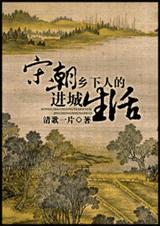�����γ�����į:�������ʷ(Ҽ+��)-��6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Ц��˵�����˴��������������Ͷ���ξ�����ʹ�����������š�����ȥ���˻����~�ݣ����Ĺõ����ã��ҳ����ڸ��˴���Ϊ���ݽڶ�ʹ�����ھ�Ȼ�����������������˶�թ����ʲô������˵�գ��������죬���������˵���������ˣ������Ĺ�����˳�������������
��������Ԫ���������֮�ԣ��Ծ���С��ת�ʸ���������ô���¡�
��������������ʩ��թ���ƣ���û����Ԫ껱��棬��ʱ����ͻȻ˵������£�һʱ����˵������ش�����δ����Щ���Ͱ͡�
��������Ԫ껲����������ģ������Ƚ�����Ѻ��ȥ��Ȼ���ø����꽫����ľ���˵�����������㽫����թ������Ԫ�������ϸ�㱨��
��������Ԫ껽��Ž��ɣ�����������ס���У�ʵ����������������Ȼ������ð����������ʹȥ�������⡣
��������������Ԥ�������ʹ��Ԫ������ģ�������������Ǹ�������ˣ��д��ø������ڣ���װģ������������Լ�������ꡢ��������Ͷ�ε�ʱ�䡣
����������ʹ��Ϊ��Щ������ģ���ȥ����ʵ����Ԫ����˻㱨��
��������Ԫ���Ϊ��������ı�����������������������ʹ���ʡ��������ʱ�����������һ������Ҳ˵������ˡ�Ԫ껼��������������¡���¶����֮ɫ��ŭ����ͷ�𣬰ν����ʣ������䣬�Ѹ�����նΪ���Ρ������������ؽ����У��Ⱥ�����
���������������֪�����걻ɱ��֪������Ѿ���Ч����æд��һƪ���ģ����˰������͵����ľ��ڡ������ż�����˵������������ֵܣ����Ȿ��������ұ䣬ʵ��������ʹ�ģ������м䣬�����˰���֮�顣
������������ʰ����ƪ���ģ�����Ԫ껡�Ԫ������˰�����Ҳɱ�ˡ�
������������Ҫ�ʣ�Ԫ���һ�����ۣ����ս�թ���ѵ��Ͳ�ʶ���˵ķ���ƣ�Ϊ��Ҫ�����ɱ�������購�أ�����˽�������飬Ԫ�ɱ���������ˣ��Ϳ��Եõ������������ˡ�
��������ԭ���������ꡢ������Ԫ껵�������ŵ��ֵܣ����������û������Ԫ껵ĵ���������ǹ�ɩ��ϵ�����������Ĺ���
��������û��������ò���绨���������֣���һ��������������Ĺ��������ر�Ԫ껡�Ԫ껱����Ժ�ɫ����û������ɫ�ɲͣ�����ռ��֮�ģ��������������ձ�Ȩ��δ����Ͷ�����֮�У�û�κΣ�ֻ�ý�һǻ��˼֮��ǿ��������������ʱ��������Ͷ��������ꡢ����Ȱ����Ͷ����͢����Ȼ���������ɵ㣬���������������ꡢ������͵Ļ��ᣬ�ٹ���˽���˻�����������
��������Ԫ�ɱ������û���Ͼн����У�һ���ƭ�����ţ��ܿ�ͷ�²��������������˵ĹѸ���Ԫ껵�����������һ�����Ԫ���Ը�Գ���§�����˹飬�������Էų�������������������Ի�ȥת�������⣬˵��Ը���ν��͡�
��������������ķ���ƣ��յ������벻����Ч����
�ڶ�ƪ���س�֮������54�ڣ��Ƴ������ܵõ��ʹ�
��������3���Ƴ������ܵõ��ʹ�
���������������֪Ԫ�����͵���ͼ�����������������˧�Ӽ���
�������������֮����ͣ��ǹ��Ҵ��£��߹ؽ�˧��Ȩ�������Ӽ�һ�潫����Ԫ���͵���ͼ�ɱ���͢��һ��������ͬ����ʹ�����ø�������̸��
���������������ʱ���Ѿ�����ս�ˣ������Ľ���������ͬ���Ĵ�ɺ���ģ��������ܲ������ĵ�����̬�ȡ���Ϊ����ʹ�����õ���������̬���൱������ֻ˵����ǰ����̸�����������γƳ�����ʵ��������ģ�������ˣ��������Ūһ��Ǯ��
�����������ڴ�֮ǰ��Ԫ���������֮ս������ʾҪͬ�ν��ͣ���ʱ������ʤ�̣�̬��ǿӲ���ܾ��������ȡ���ۺźͳƳ�����������ʹ��̸���ѡ���һ�Σ�Ԫ���Ȼ���ϳƳ���̸���ٴο����ˡ�
������������ʹ�����ü��β����ò���˵�����λʵ۵��������ȥ������㱨������������ᣬ���������������һ��������������͢Ҫ������һЩ���ͣ�ֻ�������������ܻ�ȥ���������ӻ㱨��
������������˵ֻҪ���ijƳ���������������������ǣ���������������ʿԪ�����ӊ��������������������ʹ������һͬ���У���������Ԫ�̸�С�
�������������������˵������ĺ�ͬԪ�չ���˵ڶ���̸�С�
��������Ԫ�ԭ����ͬ��Ƴ�����ʨ�Ӵڣ���Ҫ�����ԶԶ����������������ʱ���������ǵĵ��ߣ������ĸ�������������ֻ�ܱ������������ˡ�
��������Ԫ������綨���ᡢ����������Ϊʹ������͢ʹ���ٸ����������ξ��е�����̸�У���̸�γ�ÿ������ĵ�Ǯ�������������ǡ��͡���
�������������������ּۻ��ۣ�������ڴ��Э�飺����ȡ���ۺţ��β��Ԫ�Ϊ�Ĺ������Ķ����Ա��������ϳƳ�������˷���γ�ÿ�ꡰ�͡����ľ�ʮ����ƥ�������������������˫���Ľ����١��͡���������ǧ�������������������ǧƥ����һ���ؿ��߽�ȶ�����ָ����ó�����������������β���Զ���ξ���˫����ǰ������������黹��������б�������������Խ���������߾�����Ϊ�磬����ͣ���DZ���
�������������Լ��Ԫ�ռ���˱��ˣ��γ������ؽ����˸������ӡ������������������Ķ��γƳ�������˷����ʵһ�����嶼û�У�ֻ��������������õİ�ο���ˡ�Ԫ����Լ��ĵ������������Լ��Ļʵۣ����������Լ��Ĺ�Ա�������������ӡ����ɹ����������ӡ�ÿ�껹�ø���һ��ʵ�Ǯ�ơ�
����������ݺ�Լͬ�����Ƿݺ�Լ���������Ǯ���������ͬ�⣬��һ���ֲ�ͬ�������Ƿݺ�Լ�ǡ��ɡ���������ݺ�Լ�ǡ��͡������ɡ�������͢���澡ʧ�����͡��֣��ƺ���һ�����ӵ�ζ����
��������������Ǯ���˸����ӵ����ݣ�ʵ������Щ�Ҳ��̶á�
����������̸�ɹ���ǩ����ͣսЭ�飬������������һ������������Ϊ���Э����ʲô���ף��Ͼ����ij�������������ӵ����ݣ����ұ�͢��������ս�������ܻ��˲���Ǯ��������һ���߾������̣������Ǻ�ֵ�õġ�
����������ʵ��Ԫ��Ѿ����������ⷴ��Ƶ�Ȧ�ף��Լ�������ɱ�˸�����������յ�û����֮����̰��Ůɫ�����������������֮;����֮���ĵľ���״���Ѿ��൱��⣬Ԫ�Ҳ������ս�ˡ��������к����������͡��Ӽ��������ߣ�����һ��������կ���߹��ѽ���и�ɻ���Ԫ껼�ʹ��ս��Ҳռ����˿���ı��ˡ�Ԫ������ͣ����������ɹ���������������������Ҫ��Ԫ�����͢�ɹ�������ÿ�껹Ҫ��������İ�������Ͳ衣
���������γ�������ų����־���ڹ�������������֮�����ɴ˿ɼ�һ�ߡ�
�������������������ͣսЭ�顱ִ�еò����ã��Ρ���֮��϶������ִ�����ʮ�ֱ꣬�����������������¡�
���������˻����ѷ����ʲ���һ����ҩ
��������1��������ɽ
���������������꣨1043�꣩���£���������ǰ�ߵķ����͡�����ͻȻ�յ���͢�ĵ������Ҫ�����ǻؾ�ʦ�����볯͢��������ʡ����߾��»�������Ժ��ְ��
����������������������ϱ������������������ر߹أ���͢һֱ������������Ѯ���������˰����˽���������������Ը���뿪���ݣ��ؾ��Ǿ����µĹ�����
�������������͡������ؾ���ʱ���������ĵĺ�Լֻ�Dz�ǩ����û�и��Ϲ�ӡ������Լ������Ϊ������Ȳ������ؽ����Ƕ��˴�����ǰ���ٻ����أ���Ҫ�ӵ�ʱ�Ĺ���˵��
����������ʱ���Σ��Ѿ��ǻ�����ɽ��Σ���ķ������Ҳ���Ҳ������ǰ��δ�е����ѡ����ò����ԭ�����ڡ����ߡ������߱����������߷ѡ�
���������߱����δ���ȡ���������ƣ���Աһ˵����ʹ���������������ӡ�̫��ʵۿ���ʱ��������Ϊ��ʮ��̫�ڻʵ�ͳһ�й�ʱ�ﵽ��ʮ����������������䣨1041��1048�꣩�Ѵ�һ�ٶ�ʮ����
���������߹١�������������Դ���������棺һ�ǿƾ�ȡ�ˣ��ƾ��ƶȴ������꣬ÿ��ȡ��ʿ������ʮ�ˡ�̫��̫ƽ�˹����꣨977�꣩���н�ʿ����߰����ˣ����ҳ�Ϊ����ִ�У����������꣨991�꣩��ȫ���Ľ�ʿ�ۼƶ��һ����ǧ�������ˡ����ˣ���ʿӦ�ԲŸ�Ϊ����һ�Ρ���ʮ����������һ���Ӵ�����֡�������Ϯ���δ�ѡ�ι��������ƾ���С����ҷ���������Ϯ�������δ��涨����ѧʿ���Ϲپ���ʮ�꣬�ֵ�����ɳ����ٶ�ʮ�ˣ��ԽӴ����������ƶ�֮�������ﵽ�˶༰���������������ſͳ����ĵز���
�ڶ�ƪ���س�֮������55�ڣ���������
���������߱�������ʹ������������ظ����������������������Ȼ��̫�ڳ���������������״����̫��ʱ��ӯ������˲������ֵĵز�����֮����ս�£���ƣ���ñ������Ҳ����������˱����ı�Ե��
���������������ٷ����͡��������˽�������Ҫ�������Ƕ����ڵ����������ֵ������Ͳ��ǣ��齨һ���µ�����������ԡ�������ס���ˢ�³�����
���������ڷ����͡������������Ρ����������������������Ĺ����У������ֳ�����һ�α��ҡ���������ʿ�����������ݽ������ʮ�ˣ�ɱ��Ѳ��ʹ���Ҹ��췴�����鷢�����������½�������������������ȡ���ף����л������������ˡ���
���������������ң���Ұ����ŷ����Ϊ�������Ա�Ƿ��ϱ���Ҫ��͢������·����¶����֮�����������иĸ�����ȳ���Σ����
������������Ҳ��־�ĸ��Ӧŷ�����˵���������������ء�ŷ����Ϊ֪��Ժ���ྸΪ�����ԣ�����Ϊ������ة֪��Ժ�����Ĵ��ɹ��У�ŷ���ޡ��ྸ�����������ھ��v��䣬�����ļ���Ϊ��������������Ϊ�ɹ٣���Ȩ���գ����Ǵ�����ĵ����ϣ�������¶�����������Ͳţ����ҶԱ�����Ϊ���������չ�����������������͡���������������ӣ��Գ������иĸ
�������������������ɹ��ǵĽ��飬�����µ����£����θ���������ӣ������ļ�����ְ֮�����ձ����Ϊ����ʹ������ְ��������������ְ��������������ȫ��ŷ�������Թٸ��������ġ�
��������ŷ�������ǵ������������ǣ����������ս��������۽���������Ϊ����Ϊ�˼�թ���������ˣ�ʵ�ڲ��ܵ��������Ҫ��ְ��
�������������£���͢��������齨��ɣ��µ���Ϊ��������ͬƽ���¡�����Ϊ����ʹ��������Ϊ��֪���¼���������ʹ������Ϊ���ܸ�ʹ����������������������Ϊ���ܸ�ʹ��
�������������;����������Һ�塢�������������£��������ⳡ���θĸ�֮�С�
��������2����������
�������������ͻؾ��������ؿ����¸��ٷ����͡��������ڣ���������ֽ�ʣ�����ߡ���¡�ص�������Ҫ�����ǽ���͢��ǰ�ļ���д��������Ҫ�й��ǣ�Ҳ���ûرܡ�
������������һ�ֽ�����������������Ϊ����Ҳ��ӳ����������ļ��ȺͶ��������˵����Ρ�
����������������һλ�彫���ڳ�͢�͵ط���ְ���꣬����һ���ǹ�����֮�ģ�ƽʱ�Գ����������⣬��Ȼ����û����������һ��˼�����Ի������Ժ������Ĺ���ˢ�����Ρ���˥�����뷨�����������������顶����گ����ʮ�¡�����Ϊ�ĸ�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