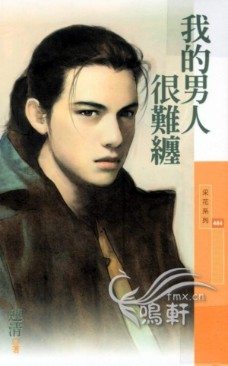我的波塞冬-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从小认识老刘,二十多岁了才认识你爸爸的。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出海之前来看我们的表演,演出结束之后找来后台看我,说了五分钟的话。
他穿着海军军装,个子那麽高,说话有一点大连口音,白脸孔,但是被海上的阳光晒得发红,是个特别棒的小伙子。因为这五分钟,我等了他半年。
那个年代谈恋爱很难,船少,每一艘巡洋的时间都很长,我一年能跟他在一起三个月就不错了。
如果我不爱他,我会嫁给他吗?”
你长了这么大,自己算没算过每年能见到你爸爸多久?也请你公道的回忆一下,妈妈有没有过一句抱怨?
我。
。。。。。。
我为什么要抱怨呢?
你爸爸那么好,有才华,有脾气,有义气,对我那么好,对你姥姥家也好,还有他把你给了我,又迷糊又好玩又漂亮的傻姑娘。我没什么可抱怨的。”
她说到这里,声音有微微的颤抖,但是她面孔冷静,神色淡然。
我们坐在榕树的下面,我仔细看着她:挽好的长发,精致的妆容,颈背修欣,有中舞蹈家特有的美丽和骄傲。
“刘叔一直都没有结婚,你也知道的,是不是?
我早跟他说过,我不领这个情——没用。
但是有些男人很固执。
后来我就当看不见;后来就平常对待;再后来,他跟你爸爸都成了好朋友了。
去年的时候他检查出这个病。
你现在看他是这样,其实过程当中特别残忍:我们去泰国的时候,他仅仅是手掌发麻,回来之后,所有的官能一点点丧失。刚开始不能走路,后来手臂都抬不起来,然后是不能张嘴说话了,医生说,视力恐怕也会。。。。。。”
我的眼睛湿润,鼻子里面堵得发疼,她却没有一丝的激动,只是说到这里突然站起来,在榕树下面快速地走了几步。
“小孩子不说谎,菲菲,刘叔不是坏人,他不应该这样。你说对不对?”
我也看言情小说,哭哭啼啼的电视剧,很多人纠结的问题是你是要你爱的那一个,还是爱你的那一个。
她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含泪的眼睛,仍然是那么平静:“我选的是最需要我的那一个。”
这是一个我等待了很久的答案,可是得到它并没有让我觉得有丝毫的释然或释怀。我步履沉重地从花园里走出来,慢慢经过住院部、门诊处、闪着蓝灯的救护车呼啸着经过,将新旧生命迎来送往,我回头看看,所以这人世上不仅有欢笑、美食、练歌房和游艺厅,还有这些等待选择的无奈。
“俺肥!”
有人喊我。
我回头四处寻找声音的来源,看见小班长从停在门诊处外面的救护车上下来,向我焦急地招手。
我听见自己的心里“轰”的一声,我飞快地奔过去。
卷纹石,我要一个答案。
chapter 38
在曾母盆地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被初步探明之后,最早降落海底地声纳仪被熄灭,然后打捞上岸。重新装箱运回大陆之前,莫凉对他们一一进行精密的检查。意外就在这时候发生。在波塞冬实验室里,那已经熄灭的二号声纳仪忽然开始高速运转。毫无保护措施的莫凉被多波束的超声贯穿身体。
此刻他躺在病床上,脸色像床单一样雪白,没有伤口,还是从前那般清爽干净。可是谁知道他的身体里承受着怎样巨大的痛苦?我想起武侠小说里的一句话:内伤严重,筋脉尽断。
这种感觉我曾经体验过。
那是在梦里,我去修理沉在海底的声纳仪,它忽然被点亮,向宁静的海域散发威力巨大的超声波,像所有在那一瞬间被袭击的生物一样,我在梦里体会到那催心裂肺,置人于死地的力量。
后来我知道,那并不是梦。
那并不是梦。那是真正发生在海底的事情。不做、不仅仅是这一台设备。也不仅仅是这一次在中国南海的勘测,多年以来,多少生命在海底为人类寻找石油献祭。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报复,这一次,在一个年轻的科学家的身上。
我隔着玻璃窗看着在里面熟睡的莫凉。
天色渐晚,病房里是幽幽暗暗的蓝色,远方的大海在沉默地翻腾。
我用手指轻轻敲着窗子说:“莫凉哥哥,醒一醒啊。尼罗河流经坦桑尼亚的那一段别名叫什么来的,你还没有告诉我呢。。。。。。”
他当然不能回答,他在默默地忍受痛苦。
我抽了抽鼻子,想要把眼泪憋回去,我不想要模糊的视线,我想要一直看得到他,看清楚他。
我在莫凉的病房外面不知不觉地睡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被哭声和叹气声唤醒,睁开眼睛,是他刚刚赶到的父母和北京大学的副校长。我想要上去安慰莫叔莫婶,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做。看着围在一起的众人,所有想要见到他的人都在这里,你莫凉最想见的人在哪里呢?
柳生兰子。
我要去找她。我要去把柳生兰子给他找回来。
我跑出医院,打了一辆出租车去科学宫,那张画着巨大抹香鲸的海报刚刚被撤换下来,我找到展览中心秘书处,我说我要找那日本学者夫妇,请马上告诉我他们在哪里。不然我不走,就赖在这里。
他们把柳生兰子在广州的联系方式写到卡片上给我的时候,被我一把夺过来,我赶到宾馆找到他们的房间,门是开着的,服务员在打扫,我抓住那广东小妹的肩膀问:“住在这里的日本客人呢?”
她用生硬的普通话回答我:“一个小时之前已经离店回国了。”
我被失望和疲惫击倒,一下子坐在地上,一秒钟之后我晃晃悠悠地扶着墙站起来,我怎麽能在这里耽搁呢?我得去机场,机场找不到就去日本,天涯海角也得把柳生兰子找回来,她得见见莫凉。她是他心里面的人。
等电梯的时候,我在走廊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倒影:头发蓬乱,形容憔悴,身上是穿了两天的衣服,很多的汗水。我有些饿,头也晕。我闭上眼睛,深呼吸,没有关系。我撑得住。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完呢。
电梯打开,我因为自己看花了眼睛,柳生兰子居然从电梯里走出来。
她看着我也是一愣:“安菲小姐”
希望 在黑暗中轻轻闪过,我的眼泪涌出来,说话却语无伦次:“柳生老师,去看看莫凉。现在。马上。他在医院里。。。。。。他还没有醒过来。
我的运气真好,柳生兰子有文件落在宾馆的保险箱里,回来取的时候被我撞上,赶往医院时,我跟她都坐在后座上,我一直看着她,有点神经质地害怕这个好不容易找回来的人突然消失掉。
我终于把柳生兰子给莫凉带回来。
可是,所有来看他的人都要被一个冰冷的玻璃隔在加护病房的外面,一窗之隔,两个世界。
柳生兰子穿着及膝的裙子,安静地站在那里,看着莫凉。我从玻璃的倒影里能看得见她美丽的脸庞,她总是让我自惭形秽,我捊一捊头发,舔一舔干燥的嘴唇,心里想:她应该美丽,因为他英俊,这样才是王子和公主,一个把沉睡中的另一个叫起来。
医生跟莫叔莫婶交代病情。
我很累,听得断断续续,他所受的危险的伤在脑血管,他那里原本就有一个血块,被超声震碎了,现在昏迷的直接原因就是颅内出血。
莫婶痛哭流涕,反复地问:“他怎麽会有血块啊?。。。。。。他怎麽会有血块啊?。。。。。。。他一直好好的啊。”
我坐在地上,把头埋在膝盖上不让自己哭出声。很多问题这样就有了答案,他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流鼻血,他为什么会跟我说“我没有时间”。
原来如此。
柳生兰子向我点点头,让我过去。我用手背擦了一把眼泪,站在她旁边。
她看着我,眼睛非常清澈:“安菲小姐执意找到我,让我来看莫凉君,一定是觉得我跟莫凉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老实说,是有很多事情在很久以前发生过,也在很久之前结束。
可是也许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安菲小姐可能不知道。”
我安静地听她说话,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在日本,研究所里有单杠,同事们在工作之余都喜欢在那里锻炼身体,轻松一下。莫凉君的单杠练得非常好,可是有一次不慎从上面摔下来,头着地。
现在想起来,也觉得那次真的危险,他甚至有成为植物人的可能。
可是莫凉君在几天之后醒过来,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我们都以为没事的时候,他开始流鼻血。
医生在他的颅内检查到肿块。
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都劝他起码要去做保守治疗,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些勇敢的人会突然丧失勇气。莫凉君就是如此。直到离开日本,他都没有接受任何治疗。”柳生兰子看着我,“安菲小姐要不要坐下来,你看上去有点虚弱。”
我摇头:“请你继续讲给我听。”
“就在那天,二位去参观展览的那一天,莫凉君告诉我,他打算在这次勘探任务结束后,接受手术。从前连保守的治疗都不愿意做,现在却宁可接受颅内手术,我问他哪里来的勇气,他说,就说因为这个妹妹。”
“就在那一天,他对我说,他没有时间来恋爱。”我喃喃的说,像是跟柳生兰子讲述,又像是提醒自己。
“开颅手术,如果顺利,就赢到一个未来;如果出现意外,他也许更愿意你在那之前离开。”她眉目低垂,再抬眼,泪盈于睫,“所以安菲小姐,如果有个人能够把莫凉君唤醒,你说说,她应该是谁呢?”
我转过身看向病房里的莫凉,泪流满面,在心里喊着:“是我,是我,不过,莫凉,求求你一定要醒过来。”
医生站起来说:“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为莫老师做开颅手术,,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力量,我建议尽快把他送到上海。”
副校长说:“请您尽快联络好国内外的专家,转院的事宜我们来安排。医生,”他握住他的手,“请尽力帮忙,医生,帮帮忙,这个年轻人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我送走柳生兰子,自己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发呆。
走廊的窗子外,海面隐没于夜色,出奇的寂静中隐隐有波涛声。
我好累好难受,低着头,打个盹,又睡著了。
我梦见爸爸。
我们在吃很丰盛的早点,都是他准备的:蛋糕牛奶,豆浆油条茶鸡蛋啊,什麽都有。我的面前是一碗大米粥。我说:“爸爸,你怪不怪妈妈?”
他说:“怪。”他在扒一个茶鸡蛋,扒完了放在我的碗里,“但是,我等她回来。”
我边吃鸡蛋边笑起来。
有人推我的肩膀。
我睁开眼睛,小班长站在我旁边,拿着两个茶鸡蛋。
东方出现鱼肚白,我在这里一睡又是一宿。
我好久没吃东西了,这个时候觉得饥肠辘辘,我接过那两个茶鸡蛋,剥掉皮,狼吞虎咽地几口吃掉。
小班长说:“俺肥,你也累得很呢?”
我摇摇头,嘴里都是鸡蛋。
“莫老师说,你潜水比赛进入了决赛,是真的吗?”
我抬起头,“今天是几号了?”
“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了。”
今天是决赛的日子啊,我把这事都忘到脑袋后面去了。我站起来,又坐下;再站起来,向电梯间走了好几步,又硬生生地回来。
小班长看着我:“你放心不下莫老师啊?”
我说:“嗯。”
“你不去参加比赛了?”
“。。。。。。嗯。”
走廊里的投币电话忽然响了起来,声音在安静的病房里分外刺耳,我赶紧走过去,把它拿起来又要挂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