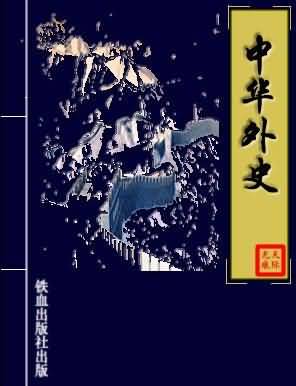中华野史-第56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方才因和你同吃晚饭,联想到那日的晚饭,不禁发出感慨来了。“
熊义听了,正触动了秦次珠撞翻秦珍的事,心想男女一般的,有了情人,便不要父母。古人说孝衰于妻子,我看于今的社会,并不必妻子,直可谓孝衰于淫欲。熊义想到这时,硬觉秦次珠这种女子,决不可娶做妻室。只是秦珍如此昏聩,总以为自己的女儿不错,婚约已经订过了,他如何肯退给我?一个人想来想去,甚是纳闷。这时正是十二月初间天气,久雨初霁,入夜霜清月朗。大冢地方,有几座小山。熊义住的房屋,有两方面靠着山麓,山坡上,一望皆是松树,高才及屋,密密丛丛,苍翠蓊郁。大风来时,立在山顶上举目下望,但见枝头起伏,如千顷绿波,奔驰足底。嘉纳治五郎创办的宏文学校,就在山背后,胸襟雅尚的学生,于黄昏月上时,每每三五成群,来这山上,徘徊绿阴丛中,啸歌咏吟,这山殊不寂寞。此时的宏文学校已经停办了,又在隆冬天气,轻容易哪得个人来领略此中佳趣?熊义既是纳闷不过,背抄着手,闲闲的向门外走。
从霜月里远望这座山时,苍茏一抹,隐隐如在淡烟轻雾中。信步向山麓走去,穿林踏月,渐渐把秦家的事忘了。
一个人立在松林中,万籁都寂,但有微风撼得松枝瑟瑟作响。立了一会,觉得没穿外套出来,身上有些寒冷。正要举步下山,忽一阵风来,带着很悠扬的尺八音韵,停步细听,那声音即从松林中穿出,愈听愈凄切动人。心想若非离得很近,听不这么清晰。这山上没有人家,这般寒冷的天气,谁也像我一般,在家纳闷,跑到这山里来吹尺八?我倒要去寻着这人,教他多吹吹给我听。一步一步寻着声音走去,好像在山坡上。
走近山坡一听,声音倒远了,又似在山底下发出来的。心里诧异了一会,忽然领悟过来,尺八是愈远愈真,正是这种霜天,微风扇动,立在高阜处吹起来,便是三五里路远近,也字字听得明晰。反是在跟前的人,听得哑喑不成音调。熊义立在山坡前,听那声音,估料在山下不远了,认定方向,走不到几步路,声音截然停止了。月下看得明白,乃是一个女子,坐在一块桌面大的白石上,手中拿着一枝尺八,听得熊义的脚步声音,停了吹弄,回头来望。熊义见是女子,不好上前,暗想她一个女子,夜间若独自出来,跑到这里吹尺八,其开放就可想而知。
我便上前和她谈话,大约不至给钉子我碰。我心中正闷苦得难过,何妨与她谈谈,舒一舒胸中郁结。想毕,竟漫步上前,朝着女子点头行礼。
不知那女子是谁,是否和熊义交谈,且等第八集书中再说。
第二十九章 美教员骤结知音友 丑下女偏有至诚心
第七集书中,正写到熊义因为和秦次珠决裂了,独自一人在山间散步,遇见一个吹尺八的女子,因为作者要歇一憩,因此停止了。此刻第八集书开场,免不得就此接续下去。
话说熊义走到那女子跟前点头行礼,那女子不慌不忙的,起身回答了一鞠躬。熊义开口说道“我独自在这山里闲步,正苦岑寂,忽听了这清扬的尺八声,使我欣然忘归,寻声而来,幸遇女士。不知女士尊居在哪里?因何有这般情兴,也是独自一个在这里吹尺八?”那女子望着熊义,笑了一笑答道“我就住在这山后。因饭后散步,发见这块又平整又光洁的白石,就坐下来,胡乱吹一会,见笑得很。听先生说话,好像是中国人,也住在这近处吗?”熊义点头。问姓名,那女于答道“我姓鸠山,名安子,在女子美术学校教音乐。学校里有两个贵国的女学生,我听她的说话的声调,和先生差不多,因此知道先生是中国人。”
熊义见鸠山安子说话声音嘹亮,没一些寻常女子见了面生男人羞羞怯怯之态;月光底下虽辨不出容颜美恶,但听声音娇媚,看体态轻盈,知道决不是个粗野女子,心里高兴,想不到无意中有这般遇合。笑着问道“尊府还有何人,与人合住吗?”鸠山安子答道“我一个人,分租了一间房子。房主人是我同乡,六十宋岁的一个老妈妈。我和她两家合雇了个下女。”
熊义更加欢喜道“女士是东京府人么?”鸠山安子摇头道“原籍是九州人,因在东京有职务,才住在东京。每年暑假回原籍一次,年假日子不多,往返不易,便懒得回去。”熊义道“女士原籍还有很多的亲族么?”安子道“亲族就只父亲,在九州学校里担任了教务,一个兄弟,在大阪实业工厂当工徒,以外没有人了。”熊义道“此去转过山嘴,便是舍下。这里太冷,想邀女士屈尊到舍下坐坐,女士不嫌唐突么?”安子笑着摇头。熊义道“舍下并没多人,就只一个朋友和一个下女。”安子仍是踌躇不肯答应,熊义道“女士既不肯赏光,我就同去女士家拜望。不知有没有不便之处?”安子连道“很好,没有不便。”说时,让熊义前走。熊义说不识路径,安子遂上前引道。一路笑谈着,不觉走到一所小小的房子跟前,安子说“到了。”伸手去栅栏门里抽去了铁闩。里面听得推门铃响,发出一种极苍老的声音问“是谁呢?”安子随口应了一句,让熊义脱了皮靴,径引到楼上。放下尺八,双手捧了个又大又厚的缩缅蒲团,送给熊义坐;从房角上搬出个紫檀壳红铜火炉来;用火箸在灰中掏出几点红炭,生了一炉火。跑到楼口叫下女,熊义忙说不要客气。安子叫了下女进房,在橱里拿出把小九谷烧茶壶,两个九谷烧茶杯,向下女说道“拿到自来水跟前洗涤干净,再用干净手巾揩擦过拿上来。这里有蒸馏水,烧开一壶拿来,我自己冲茶,不要你动手。我的开水壶,楼底下老妈妈没拿着用么?”下女道“先生的壶,我另放在一处,怎得拿给老妈妈用!”安子点头道“快拿去洗罢,仔细点,不要碰坏了。”下女两手去接茶盘,两眼望着熊义,安子生气骂道“你两只眼怎么,害了病吗?”下女被骂得红了脸,接了茶盘,低着头向外就走。安子喊道“你这东西,真像是害了神经病的,蒸馏水如何不拿去?”下女又转身从书架上取下一个七八寸高的玻璃瓶,里面贮着大半瓶冰清玉洁的蒸馏水,下女一手提着,一手托着茶盘,下楼去了。安子才挨着火炉坐下,对熊义笑道“在东京这般人物荟萃的地方,雇不着一个略如人意的下女。说起来,倒像我性情乖僻。其实我极不愿意苛派下人,只是下等人中绝少脑筋明晰的。”
熊义进门即见房中陈设虽没什么贵重物品,却极精致,不染纤尘。四壁悬着大小长短不一、无数的锦囊,大概尽是乐器。
在电光下,见安子长裾曳地,足穿白袜,如银似雪;头上绾着西式发髻,在外面被风吹散了些,覆垂在两颊上;没些儿脂粉,脸上皮肤,莹洁如玉;长眉秀目,风致天然,便知道是一个极爱好的女子。看她年龄,虽在三十左右,风韵尤在秦次珠之上。
当下听她说下等人中少头脑明晰的,也笑答道“便是上等社会中人,头脑明晰的尚少,何况他们下等人?自不易得个尽如人意的。”
安子到此时,才问熊义的姓名职务。熊义存心转安子的念头,自然夸张身世,说是中国的大员,来日本游历的。因贪着日本交通便利,起居安适,就住下来,不愿回国做官。安子看熊义的容貌举动,也不像商人,也不是学生,装模作样,倒是像个做官的,心里也未免有些欣羡。谈到身世,原来安子二十岁上,嫁了个在文部省当差姓菊池的。不到五年,菊池害痨瘵死了,遗下的产业,也有四五千块钱。安子生性奢侈,二三年工夫,花了个干净。还亏得曾在音乐学校毕了业,菊池又是个日本有名善吹尺八的,安子得了他的传授,才能在美术学校教音乐,每月得五六十元薪水,供给生活。在菊池家没有生育。
妇人守节,在日本是罕有闻见的事,因此安子对人仍是称母家的姓,不待说是存心再醮。当夜两人说得异常投合,到十二点钟,熊义才作辞回家。
次日,用过早饭,熊义怕秦家又有人来叫他去,急忙换了套时新衣服,跑到安子家来。昨夜望着熊义出神的下女,出来应门。一见熊义,笑得两眼没缝,连忙说请上楼去坐。熊义只道安子在家,喜孜孜脱了皮靴,下女在前引道,熊义跟着上楼。
只见房中空空,并不见安子在内。熊义正待问下女,你主人到哪里去了。下女见熊义已经进房,顺手即将房门推关,从书案底下拖出昨夜熊义坐的那大蒲团来,笑吟吟送到熊义面前道“请先生坐坐,我主人就要回家的。”熊义一面就座,一面说道“你主人嘱咐了你,我来了,教我坐着等的吗?”下女且不答话,拈了枝雪茄烟,递给熊义;擦着洋火,凑近身来。熊义刚伸着身子去吸,那洋火已熄了,以为下女必会再擦上一根;等了一会,下女还伸着手,拈着那半断没烧尽的洋火,动也不动。熊义心里诧异,抬头看下女,两眼和钉住了一般,望着自己的脸。熊义老在花丛的人,都被她看得不好意思起来,掉过脸见火炉里有烧燃了的炭,也不理她,自低头就炭火上吸;暗自好笑,这种嘴脸,也向人做出这个样子来,真是俗语说的“人不知自丑,马不知脸长”了。下女见熊义掉过脸去,也挨过这边来,借着拨火,双膝就火炉旁边跪下,膝盖挨紧熊义的大腿。熊义连忙避开问道“你怎知道你主人就要回的,教我坐在这里等呢?”下女涎着脸笑道“我主人照例是这么时候回来,因此教先生等。”熊义道“这么时候,是什么时候,此刻还不到十点钟,你主人到哪里去了?”下女望着熊义的脸半晌道“先生昨夜和我主人谈了那么久,还不知道她到哪里去吗?”熊义点头道“呵,上课去了。那如何就得回来?我走了,她回来的时节,你说我夜里再来。”用手按着火炉,待要立起身,下女拖住衣袖道“请再坐坐。我主人今日只有八至十两点钟的课。先生若走了,她回家又得骂我。”熊义问道“你主人因这一般的事体骂过你么?这里常有男朋友来往么?”下女摇头道“没有骂过。我主人没男朋友往来。不过,我主人脾气不好,无一日不骂我几遍。但是她有一宗好处,骂我是骂我,喜欢我的时候,仍是很喜欢我,随便吃点什么,给我吃。她最爱好,半旧的衣服,就嫌穿在身上不好看,整套的送给我穿。先生看我身上穿的这件棉衣和这件羽织,不都是很贵重的绸子吗?我煮饭扫地,穿了两个多月,还有这么新。我有个亲眷,在质店里当伙计,前日我教他估价,他说好质六块钱,若是卖掉,到万世桥,也可卖十块钱。”
熊义见下女呆头呆脑的样子,说出这些话来,忍不住好笑。
然心里倒原谅她,那种痴笨样子,倒不必一定是存了邪念。立时把讨厌她的心思减了许多,逗着她谈谈倒也开胃。笑问道“你伺候你主人几年了?还没有婆家吗?”下女道“我姓吉田,名花子,今年二十一岁了。”熊义笑道“我是问你从何时来伺候你这主人的,不是问你的姓名年岁。”花子道“我知道先生不是问姓名年岁。但是先生不问我有没有婆家吗?我婆家原是有的,丈夫也是中国人,在这里留学。我十七岁嫁了他,同住三年。去年他毕了业,回北京去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