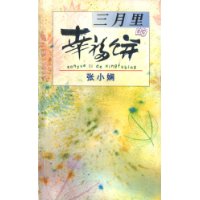阶梯教室里的爱情-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使她感到很蹊跷。
他当面不好发作,一个人静坐沉思,按头脑里妒恨和气愤的逻辑做了一个苛刻的决定:结束吧!
所谓政教主任跟她拉拉扯扯,纯粹子虚乌有。其实是:政教主任个子瘦小,跟在她的身后纠缠,单从高矮来说,象非洲草原上的胡狼跟着羚羊,怎么能跟得上呢?再从禀性来说,一支郁金香怎么会愿意混进野草丛里?他拉住她的手,她生气地甩开。
这一幕被几个人看到了,风言风语传开了。
第九章
那次聚餐以后,王丽莎感到在喝酒上有点失态,产生着懊悔,又为那个讨厌的政教主任而烦恼。但又觉得也没做出什么,以后注意就对了。她倒是觉得最近很少见到他的身影。
就在这段空隙,另外一个女人的感情象放开闸门的水猛地冲向刘之江。那个女人叫张亚萍,在头脑里爱着刘之江,心里却不顾他们在各方面的很大差异。现在趁他和王丽莎疏远了,完全地对他表白了态度。刘之江心里不太乐意,假设在与王丽莎接触的日子里,按他的性格,可以当面对张亚萍说:“我不爱你。”可是在他的妒恨和气愤里,他勉强接触起来。在《魂断蓝桥》“烛光俱乐部”式幽暗的舞会上,透着外面窗户的亮影,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贴在一起。他没有理睬王丽莎手机发来的几条短信。在教学之余,他重拿起来自己的爱好,一幅幅的油画寄到一个朋友所在的杂志社发表。她给他最后发的一条短信是:
“你怎么啦?”
他回了两个字:
“永别!”
这两个字化成的一道电磁波,象一道电流,把王丽莎击倒了。
从此,她呆呆的,发型、面色、衣饰,象被旋风吹了一样,皱巴凌乱,不能洗梳一新。别人问:“丽莎,你怎么啦?”她说:“患感冒了,一直不好。”她几乎从来没有说过谎话,这次说了,太象一个患重感冒的人。有一个晚上,她似乎沉睡着,其实闭着眼睛流泪。她只感到伤心,再想不到别的什么。用枕巾一遍遍地擦着,眼睛里发热发涩,半条枕巾擦湿了。孩子在旁边睡得很熟,胳膊扬起,放在头上面。她把女儿的小胳膊放到被子里,注视着孩子光洁的面庞,想到童贞,想到人活着的意义,越发伤心。后来不知不觉睡着了,擦湿的枕巾捏在手心里。早上起来,眼睛红红的,这个样子怎么到学校里去?她先用凉水捧在手心里冷眼睛,又用湿毛巾敷。
临出门时,她又走到镜子前,端详自己的容颜,害怕别人看出隐情来,试验了一个笑容。
“六一”儿童节,天气炎热,学校组织老师们到张掖马蹄寺去玩。
寺院虽然有名声,但人们的兴趣不是很大,感兴趣的是绿色的山。
老师们玩得都很高兴,鲜花青山,蓝天白云。她在这天,苦闷消失了许多,跟着大家笑呀,说呀。她特别喜欢上山。
山坡不是很陡,松树里夹着灌木丛,杂草野花,偶尔一块大青石。把衣服搭到胳膊上可以轻松地上山,坡陡,就扶着树干。到半山上,许多人腿脚发软,上不动了。王丽莎还在上。她的波浪发用三支别针别起来,太阳穴上面的一绺发丝仍不时垂下,背着牛仔旅行包,银灰色运动衣的拉锁醒目的两条黄,她的裤子笔直合体,适合运动,给她增加了健美。山坡上有马莲花,花枝清绿,花朵嫩白,叶瓣两三片。别人都上山了,在一块草坡上,她欣喜地采摘着马莲花,攥在手心里,用一个红线绳扎住,嗅一嗅,带青草味的药香。她想下山以后,送给他。
进入树林后,有一块苔藓,她踩上去滑倒了,身体滚了两滚,被一个树杈挡住,后面来的一个男教师把她扶起来。那束马莲花滚下去了,她看着,那束花在草丛间轻巧地向下滚着,几乎滚到山脚下,隐入一大堆灌木丛中。那个男教师也看到了,笑笑说:“我去给你拾吧?”她有心让人拾,又不能让随便一个男人拾,便说:“滚就滚下去吧!花应留到山里。”她的小腿有点扭伤。那个男教师天生不是一个性情中人,面相也憨厚,陪她上山,有时搀扶她,有时抓着她的手穿过荆棘丛。
上到最高峰,拨开树枝看,四周群峰林立。十几个人在山顶上休憩,照相,喝饮料。
天空湛蓝而清凉,收敛而又散发着蓝气似的,又好象浓郁的蓝色凝聚得这样晶莹广大。四五朵白云如卷成一卷的棉絮,边儿丝丝缕缕,娴静地飘浮着。南面的山峰低矮,丘陵一般,成绿色的大椭圆形,无边无际,融化到太阳的光辉里。她望着南方,表情沉静而微笑。眼睛被阳光照得略眨一眨,笑意荡漾,额面和鼻尖发着亮光。那种表情,好象她的初恋,在对方的注目下照第一张照片。
几个人把相照完,让王丽莎照。她脱去银灰色的运动衣,露出桃红的纯棉衬衣,把牛仔背包挎到肩上。尽管她的眼睛深处似乎有伤痕,但仍荡漾出含蓄的笑容,因为要照相,那种笑容长时间保留着。她只照了一张:背景是两座翠绿的山峰,天空是多么蔚蓝呵!
那个男教师把包里的一瓶矿泉水送给她喝,她很感激地接受了。但有人随便给他们要照一张合影时,那个男教师脸红了,躲避开,说啥也不照。
该下山了。
她一抬腿,腿面和小腿发痛,不过这种疼痛不难受,跟别人一样强迫用力气,疼痛就消失了。她在男教师的帮助下,没有容易下到山下。她忽然想起:在学校里,她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
该离开山了,坐车了。她上车时手没有抓稳扶干,身体晃了一下。
大家谁坐谁的座位。大家来的时候说说笑笑,现在好象疲惫了,有些人头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也许是疲惫吧!也许是受了寺院气息的影响吧!刘之江坐在客车的右边后面,虽然闭着眼,心思却在两个女人身上冥想,游了一天,游兴不浓。王丽莎心思忧愁单纯,不断望着窗外的风景。
第十章
她从山里回来的第二天,由于剧烈运动,腿疼得厉害,踝关节不敢用劲,脚面肿了,走路一瘸一瘸的。侧面看,她象要长途跋涉到哪里;背影看,她象一个动过手术的人。
几天后,在她慢慢地走过一条幽静小路时,忽然与他邂逅。他注视着她,她很轻地踮着走路,心里百感交集:“一个月前,这是一个亲切熟悉的女人,现在却可恨。”但又生出本能的同情性,想去搀扶,但刚有这个念头,立即又停住了。看着她乞怜而伤感的表情,他又想抬起胳膊搀扶她,手却慢慢放下了。他想起聚餐会上她的顾盼生姿,想起政教主任和她纠缠拉扯的情景,狠了狠心,没有伸出手。
他肃穆地站着,象一棵槐树,这个女人,从他身旁一踮一踮地走过。在她的身体和她平行时,他又产生了搀扶的念头,想到买一瓶红花油给她搓脚面,想到每天送她回家,但看到前面一个人从林荫道上横走过去,这个陌生人的身影也影响了他的感觉,搀扶的念头又消失了。
她走了四五步,极为伤心,头低在胸前,双手蒙住眼睛,眼泪从指头缝里渗出来。她差点晕倒,扶住路旁桃树的一根粗枝,胳膊撑在枝干上,头伏在胳膊上。
他雕塑一般站着。
她重新走路了,一踮一踮的,直到她的身影消失,他迈开脚步走路,离她渐远了。
一个星期三的下午,阶梯教室里开会,她真的迟了。她努力地不表现出腿不好看的姿势,但还有轻微的踮的姿势。大家从山里回来看习惯了,知道她脚有伤,没有产生奇异的感觉,不过也有一些人的目光因为没有事干,随便地看着她。
她表情平静,沿着这条水泥上坡路,很慢地走。她走到第六排桌位时,一个凳子横在路上。奇怪,接近于蜂拥而进的人流,这个凳子好象不存在似的,还横在走道上。她为避免接触到凳子,用手把它移开一点,才继续走路。她走到后面一个空座位上,慢慢坐下。
刘之江不很明显地看着她,感到了许多人的目光中对她有可笑的心态,因为有些人还可能在不满她的不贞洁。他产生了呵护之心,他们不应该纷纷看她,就象一盆花不准备养了,但也不想扔在瓦砾中。他恨人们。
张亚萍这种性格的女人,头脑里有一种奇怪的逻辑:我虽然有丈夫,有家庭,但别人在爱我,我却不爱他,但他可以爱我。我其实在爱另外一个人,但他不应该追求我,而我应该追求他。如果双方都有爱意,我要让别人知道我被爱着……她的逻辑在这里停止了,她再想不到别的什么。
所以,与其说是她爱着刘之江,倒不如说是她在推动着“爱”,完成头脑中的一种观念。
六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她约定他在公园里见面。
她有一个嗜好:爱手机打电话,并且还喜欢当着别人打。本来说好了午后三点在八角亭西面的柏树下见面,但她又打了三次电话,还要求他必须给她回音,尽管一切都是非常清楚。
他们见了面,都显得很高兴。他的高兴由天空、蓝色、绿树等和面前这个“女人”所构成的整体引起,而她的高兴仅仅由面前这个“情人”的概念引起。但是她推动着约会的进程。他不大喜欢公园里乱糟糟的人,不喜欢公园里小巧醒目的各种设施和刺激,但她非常喜欢,简直象喜欢手机的款式铃声和装饰得花花绿绿的手机套。
她还有一个嗜好:喜欢给“情人”花钱。
她让滩主泡了一种什么名堂的茶,茶叶象绣花针,说这种茶今年很流行。他其实对茶道很有研究,翻阅过一本厚厚的《茶经》,只因为没有条件品尝,对书上的东西影响不深。不过他嘴上说,就喝这种流行的茶吧。她说她喝饮料。
他们的谈话从天空、树木、气温,到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是几点早起的,哪一个亲戚的亲戚被提拔成副局长,学校里某老师与某老师有矛盾,互不服气,有一天做了一个梦非常奇怪,等等,随心所欲,无所不及。因为她在一个话题中会突然插进来一句,使话题随时发生变化,他跟着她应答。就如两条鱼的游动,水路难料,不过一条鱼影响另一条鱼。
在吃饭时,她说她点菜。她天生不太喜欢吃鸡肉,更不喜欢吃羊肉。这使滩主不好做一顿好饭菜。吃饭,费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她要了两瓶葡萄酒,用高脚酒杯喝。他们吃饭的情景,如果用一种诗意的眼光,那就是他们保持安静的姿势,再加上葡萄酒的深红色。但这种诗意立即又被打断,因为她喜欢猜拳喝酒。他们比划着指头,为自己多赢了他几盅而高兴。她又喜欢玩扑克,两个人便争“上游”。他对如此简单的游戏不是很感兴趣,但有时故意打错,满足她的玩心。
他们旁边走过去了一个很时髦的女人,她几乎忘记了打扑克,忘记了他,双手捧着扑克不动,眼睛乜斜着那个女人。她发现她的身材要比自己苗条,因而乳白色连衣裙的效果特别好,身材高走路舒展洒脱,裙子的下摆为英国式。但她的皮肤不如自己白嫩,脸部肌肉过于瘦,颧骨有点高,肩上挎的皮包却有点旧。这些观察又使她兴奋起来。
“该你出牌了。”他一眼也没有望那个女人,提醒她说。
“你刚才出了个啥牌?”她回过神来,问。
他把牌拿起来让她看清楚,再放下。
“哦,梅花六,我红七。”她把牌打下去,眼光透过树的缝隙,瞟了一眼那个女人的背影。
黄昏了,他们计划要再吃一顿晚饭,等着月色从树丛那边升起来,享受月色。但她的丈夫忽然打来电话,说有事,让她回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