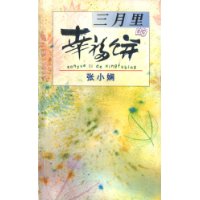阶梯教室里的爱情-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选择陌生新鲜!”
他前去,把电影《音乐之声》放DVD里,屏幕出现了画面,他选择了家庭教师玛丽亚给孩子们教“哆唻咪”的那一段播放。
她看得很入迷,羡慕地望着玛丽亚和孩子们。看完这一段,她象个高中的女生手托着腮听他讲,他呢,就象个高中的老师对一个女生讲。凭良心说,如果是真的学生在面前,不知什么原因,他老有一种急噪情绪。只有今天,心静下来,宁静、愉悦、自由地给一个人讲课。
“看过《爱弥儿》吧!没有?哦,要把自然教育演变得更丰满,在《音乐之声》中,家庭教育表现得如此完美。用教学上的行话来说,就是课堂生成,是不是?你这一堂课,三分之一用光盘,听外国人怎样对话,三分之一学生对话,甚至与学生吃东西,开玩笑,三分之一你与学生唱点什么说点什么。”
她完全依从了他。
他晚上没有回家,忙碌在阶梯教室里。到半夜三点,全都替她设想好了这节课的内容、环节、课件、用具。第二天,她不大会操作电脑,他帮她演练了好多遍。——无论什么事,只要有人看,人们总要背地里练好才放心。
课堂上,听课的老师黑压压一片。市教育局的一个主任也在听课,他可能天生不苟言笑,对课堂上的一切无动于衷,满不在乎,又好象心事重重;一个教研室的人就不象了,他虽胖乎乎的,满脸胡子,戴着高度近视镜,却在笔记本上详细地记录着课堂上的一切,也许他在评课的时候要全范围地剖析。大多数的人姿态随便,要说最特别的人是“女骨干教师”:她们姿势端庄而目光冷峻,搜寻着细微的缺点错误,上课的教师即使说话中一个汉字的读音本来是上声但是念成去声,她们也记录下来,或者,教师该有笑容的时候没有,不该有笑容的时候“为什么笑”?从而提出质疑。
下课后,由人们去评吧!总之,她的这节公开课,用教研室的那个人的话说,是:“成功了,哦,成功了”。
刘之江也在听课,他最欣赏这节公开课的一幕是:她象玛丽亚,旁若无人地活泼开朗地走入学生中,七八个学生兴奋地围拢来,有一个学生还跳起来看了被围拢的中间,看里面有什么稀奇东西,学生们哈哈地笑起来,惹得听课的老师也有了笑意——这些老师,天生不愿意自己有笑意,尤其在公开课的课堂上更是难得一笑。她转身望了那个学生一眼,笑了笑。若撇开教学,从个人的美术的角度欣赏,她很美的情态是那一瞬间回望那个跳的学生的眼神。
观摩课上完,她感到又愉快又轻松。
有一天,他感冒了,身困,发冷,疲乏无力,实在不想上课。可他又不愿央求谁去替上一节课,腋下夹了书硬狠着要去。她早知道,走过来,拿了他的书和教案本子去替她上,在拿了书转身的一瞬间,用眼神给他治病,那眼神,又柔又轻又细。他没有吱声,一直看着她的背影走出办公室的门。他坐在椅子里,闭目,喝了几口开水,润了润嘴唇,睁开眼睛望着窗外沉思。下课后,她从包里拿出一个鲜红的苹果,用餐巾纸擦得亮晶晶,放到他的办公桌上,没有说话,转身离去。这个深红色的苹果,散发醇香味,从窗户里透进的光线照着它,如静物画上的一个苹果。
他在一些老师的目光中,不敢吃,把苹果放到抽屉里。
有一段时间,她特别渴望和他在一起说话散步或者干什么,又不愿意说出口,也不愿意表现,这种念头强烈的时候,她就把头枕在作业本上一动也不动,装着困倦的样子,心里情思绵绵。后来渴望的念头淡了,看见他的身影却很生气,在心里气恼地骂他,甚至觉得生活里没有他倒更好。后来不气恼了,心情平和,依旧在一个办公室缄默着,又用最初的心情看他,产生各种感觉和幻想。如果别的女人有一句“回家吧!”她被惊醒,感觉和幻想就立即被打破了。而他,在老师们的目光中,沉默着,沉默着。等到又到了一个新的学期,他到高中上课,她仍在初中,不在一个办公室每天见面了,却都比以前更思念对方。都有点后悔:为什么不多说几句话,多做一点什么?
第三章
阶梯教室里的教学活动和其他活动是挺多的。刘之江也上了一堂观摩课,出门时匆忙,把一本书忘在教室里了。
从弹簧门进去,讲台上没有书。低头找,桌子下面的第三层板上有一本。他取上来,翻一翻,是自己的。不知谁上课,忘记了拔插销,扩音器的灯亮着。他拔掉插销,关掉电器上的一个小灯。低矮的讲台上洒落了粉笔头,黑板上写得满满的步骤公式,板书整整齐齐,一看就知道是那些循规蹈矩而忠于职守的教师上的课。他拉开弹簧门,迈出一腿,感到教室的后面好象有人。转头看,果然有人,有点象王丽莎,细看,果然是的。她在这儿干什么呢?离得这样远,大概有四五十米吧。他收回迈出去的腿,又想不说话了,要走出去。但弹簧门的柔韧使他不能很快闪出身子,他又想跟她说几句话,便又缩回身体。两扇门合齐时,砰的一声。寂静被打破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他问,声音在大厅里回荡。
“找一张光盘。”她的声音低。
他望着空荡荡的大厅,寂静无声,望着她在光线略暗的铁柜前微动着身体,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她最近好象有意避他,不说话,但更多的是看到的是她异常平静的样子。他站着,迟疑不决。
他决定走到她跟前去。开始几步,散步似的,边走边问:
“找着了吗?”
“没有。”
“找光盘干什么?”
“看呗!”
中间的水泥地面是个斜面,一米五宽,他一步一步向高处走着,两排长条形桌子慢慢地向后移动。在第七排桌椅上,有一本闲书,他仿佛就是为这一本书而来,拿过来翻看,自言自语地说是谁把书丢在这儿了。在第十一排桌椅上,有个旧圆珠笔,他仿佛专门来拣这个玩意,拿在手里,在旧书上划了一下,说还能用。在第十七排桌子上,放着个一次性塑料口杯,里面有半杯清水,他拿起来,偏着头观察似的看水,仿佛研究人员观察水里的微生物什么的。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他希望她说一句随便什么话,他将满怀相信地走上前去,但她在略暗的光线里没有说一句话。他心跳得慌,几乎想自言自语说几句什么,转身离开,又觉得这样只会使自己更加不自然。“如果她……自己这样离开合适吗?”他的脚步慢下来了,头上沁出了汗,他用手擦了一下额面,又问:
“找一张什么光盘?”
“日常用语。”
这一句话一问一答,发现自己心跳得不是很慌了,于是强迫自己问她话。
他走到离她三四米远的地方停下来。
她还在找光盘,弯着腰,紫罗兰色的风衣衬出腰肢。他又走了两步,停住,开始怀疑自己的行为和动机。看见有东西两条横着的水泥路,很想转个弯,顺墙角下的水泥路走到南面,从弹簧门走出去。这样走出去,动作是迟缓的,不豁达,甚至作为一个人的形象有点猥琐,很可能使她小看自己。然而,对她要怎么样呢?刚要向右转,一个念头飞到刘之江的脑海里:“我这样,究竟是在干什么?有点怪异吧!为什么我就不往前走呢?”他又走了两步,穿过了最后一个水泥什字路口。她直起身,手里拿着一张光盘,眼睛没有看他,望了一眼旁边的桌子算是看他。
他干咳了一声,问:
“找着了吗?”
“没有。”她弯腰继续找。
诺大的墙壁,墙壁的上面白色涂料,下面蓝色涂料,东面的窗户上挂着深红色窗帘,阳光照射显出斑驳的玫瑰红。一架大铁柜子靠着南面的大墙,她直起腰,面对着铁柜,一张一张,找她需要的光盘。
她的风衣包裹着一个身体,后背上的两道斜猾的褶痕轻轻微动。
‘他好象独自站在傍晚时候的山头上,凝望谛听着临近的夜沉思。他又瞥了一眼大厅,它们当然如果不是人的原因,是永远丝纹不动:天花板一米见方的格子拼成,东西两面的墙壁上面白色下面蓝色,延伸到南面衔接住,讲台显得那样低矮,黑板长长的一片。东面的三个窗户敞开着,窗帘没有拉住。阳光射进来,把三排桌子的桌面照得发亮。弹簧门静静的。
他放下书,突然拥抱住她。
她早有准备似的,紧缩了身体想从他的怀中滑脱,但背后风衣被他粘住,两个人的身体并没有彻底断开。于是她强烈地挣扎着,把头埋得低低的,腰也弯得很低,她的脸躲避着他。她的气力这样大,使他吃惊紧张。随着她的强烈挣扎,他不由自主地用劲搏斗,好象在制服一只梅花鹿。此刻,他几乎忘记了怀中是一个女人,是一个扭动的圆滑的清香的物件,只是劲儿越用越大,要制服。他使她的腰直起来。她的头发披散开来,遮住了她的面庞,他用嘴把披散的头发分开。她的风衣的一个纽扣挣开,“噌”的一声,纽扣飞出去,落到东面的窗跟下。她弯腰挣扎着,风衣的下摆象荷叶抖开。‘“倔强的北方女人!”他一面搏斗,一面想。她手里的光盘掉在地下了,两个人的脚在光盘上踩着,踏着,发出脆声。喯的一声,光盘踩烂了。她忽然不挣扎了,安静下来,用一种奇异的目光望着他,瞳孔里闪着亮光,脸颊绯红。
他松开手,望着她。
弹簧门响了,走进来一个人。他们停止望,急忙找光盘。
第四章
第二天,他在校园里碰见她。她的穿着焕然一新,四月下旬,浅黄色格子的棉麻连衣裙,走来走去很惹眼,裙子的最上段,也就是脖颈下,两个玫瑰色小纽扣。远处看那身材和气息,给人一种未婚姑娘的感觉。她学会了掩饰,把内心兴奋的表情表现得很平静。
一些女教师偷偷地打量她:有的在改作业时,很快地瞥一眼她的身材;有的在看一本杂志,眼光离开页面,直盯着她的背影消失;有些本来在散步喧谈,偷眼把她看得很清楚了,又装着不注意的样子,继续谈笑。有一个身体较胖说话大嗓门的女人,把两臂抱在胸前,和几个女人喧谈,看到她走过去了,拿眼睛有力地看她的身材,盯着她的臀部直到身影消失。在这表面平静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有着多么复杂的关系和惊心动魄的争斗呵!如果她们是有矛盾的妯娌两个,她一定会把她扯过来,撕碎那件连衣裙才解恨。
他们通过发短信,相约在阶梯教室里。
在这种环境里,他有一种忧虑感,想说出来,但看到她淳朴的脸,眉宇间的清秀,羞赧而极力掩饰成平静的表情,没有说,随着她笑了笑。
“你越来越美了!”他说,在心里想:“如果对她是爱情的话,现在唤醒了这个女人沉静的心。”
她摇摇头,低下,不承认,再抬起来,莞尔一笑,似乎承认了。
他们把自动屏幕放下,电脑打开,挑了几个图片,投影在屏幕上。他坐在桌子的这一边,侧着身体看屏幕,她坐在桌子的另一边。桌子的东面是投影仪,两个纸箱子。从弹簧门里进来的人会看他们的头,而看不见他们的身体和手。东面的窗户红色窗帘拉开着,窗户外面是草坪,草坪上走过去一个人的话,下层的毛玻璃上可以看清影子。南面虽然光线暗,但遥远,两个小门平常上着锁。
他们的手握在一起,互相凝视着,不说话,好象一年多了没有见过面。
弹簧门响了,他们的手松开,两个人专心地看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