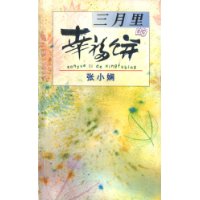阶梯教室里的爱情-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条街上,行人倒多一些。他跑得身上有了热意,也为了避免与人碰撞,改跑为走。一对青年夫妇从商场里走出来,男人白胖,衣着考究,但神态傲慢,一句话也不说,女人把雨伞撑开,给他和自己遮住雨,向北面走去。一个男人闲走路,很惊异刘之江腋窝下揣着什么,匆匆赶路,皮鞋水湿?
又到了一个什字,他折向南面跑。快冲过大街时,一块积水上雨点儿打得水面沸腾。他纵身一跳,越过积水,避开了冲过来的汽车溅起的泥水。他跑着,丝毫不觉得疲乏。再越过一个什字,拐进了小巷里。小巷没有灯,路上黑黑的,他从明亮处跑进来,看不清东西,他差点与一辆脚踏三轮车相撞,脚尖碰在三轮车轱辘上,把那个人也吓了一跳。向南转个弯,就到王丽莎家的楼底下了。
他站在楼底下车棚旁的一棵槐树下,仰头看着。雨早淋透了这棵树,树叶间的雨点不时落到他的身上。
她住的是五楼。客厅里的灯亮着,北面两间卧室的灯光也亮着。
雨不停地下着。他把药包用劲夹了夹,摇头把头上的雨水甩掉,感到头发里的雨水还在往脸面上渗。他用手抹去眼睛上的水,努力想看清她家窗户里面的暗影,视力还都有点模糊。
他原来兴奋地想着把药送给她,此刻一个人站在夜雨里,却觉得这药是多余的。她明天就要走了,要永别这个地方了,在满着收拾东西,他却送这一包药渣,有什么意义呢?他该说些什么呢?
他静默着。
不知是谁家的门哐啷地关上,一座楼都在震动。这声音使几家的灯光熄灭了。忽然从一个单元走出一个人,撑着雨伞往外面去,刘之江怕那人看到自己,隐入到树干的另一面。一会儿,进来了两个撑雨伞的人,十几分钟后,往外面出去了三个人。半个小时后,开来了一辆摩托,灯光没有射到刘之江的身上。那人把摩托推到车棚里,和看门的老汉大声说了几句话,进入到一个楼门去了。
刘之江从树下走出来,紧裹着腋窝下的药瓶,仰头看着,长时间地仰头看着,脖子有点发酸。虽然觉得自己的一切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心情却平静多了,没有那种很沮丧的纷乱思绪了。
他静默着。
忽然,王丽莎家的一间卧室的灯光亮影中,出现一个人的身影,晃动了两下,消失了。他屏声静气。十几分钟后,这个身影又出现在另一间卧室里,在玻璃跟前闪了一下。整座楼静悄悄的。一个小时后,这个亮影又出现了,比任何一次都清晰,是她的上半身,她几乎要拉开窗户往外看,可能她在窗台上找什么东西吧!等这个逼真的身影消失,他望着漆黑的夜,聆听稀落的雨声,思绪发生了变化。他原来幻想过出现一个奇迹:她拉开窗户看见他,撑着雨伞走下来,二人痛心地拥抱,溶解无尽的悔恨……现在他不幻想了,那种所谓的诗情画意或者激动人心的场景不会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因为一切都不是勉强的。
他内心塌实多了。
“她在收拾东西。”他想。
十二点了,他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
她家的灯光熄灭了。
他在暗处站了一会,想象到她睡下,盖着柔软的被子,张着眼睛望一会天花板,便会慢慢进入睡梦了,仿佛已经有所饶恕自己。就离开槐树,从小巷走出来。雨小了,蒙蒙细雨,打在脸上几乎是湿润的风。在小巷走着,雨停了,天空显出疏朗的星星,他的思绪如同天空开阔了许多。走到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偶尔一辆车驶过,街灯明亮,清凉的风吹拂着。
第十六章
第二天早上起来,他给她打了一个电话:
“我请求到兰州去送你。”她迟疑了一会,同意了。
车终于走动了,驶出这座城市。她坐在中间,右边是女儿,左边是他。车在转弯时摇晃着,他们的身体不时碰在一起。他们都有一个想法:不想故意去粘,也不想脱离开,一切顺其自然。车速加快了,人影、铺面和楼房向后飞掠。当车驶过一座加油站,路边再没有建筑了,只有稀零的树,算是彻底告别这座城市了,刘之江向后面望了一眼,恍惚觉得自己也要离开这个城市。当车驶上高速公路时,窗外开着荞麦花的田野和灰黄的土山包向后眩晕般地移动,与各种车辆擦身而过,他们两个人的脑海里被刺激出南方大城市现代气派的情景,她的内心受到了安慰,而他无奈沉重地闭上眼睛。
客车前部的电视屏幕出了图象:欧洲的山地、森林、古堡、教堂、高厦、雪峰,伴随着欧洲古典音乐。他睁开眼睛,注意力离开她,进入屏幕的意境里,魂牵梦绕,想到在这个蓝色的星球上,他,或者人类,在追寻着一个个梦,在开创一个个奇异的新境,似乎在实现着梦想,又似乎那样遥远,多象自己呵!忽然,屏幕上另换了画面,一个黄头发小伙子抽搐般唱歌,他的思绪被打断,回过神来,回到现实中来。
女儿忽然指着窗外兴奋地说:
“那是羊!”
他说:
“那是天祝草原,草原上的羊。”
王丽莎头转了一半,眼睛低望着他们之间的一块只有空气的空间,神情依恋伤感,呆呆的。他也没有直视她,在那块她望着的空间里捕捉到了她的心情,受到了一丝安慰,眼光透出玻璃窗,与她的女儿的眼光重叠在一起。
公路西面是大山上的草坡,坡上绿荫,起伏平滑缓慢,向高处延伸,绵羊三三两两地散布开吃草。牧羊人是个山里汉子,身穿白的羊皮袄,头戴无檐圆帽,筒着手。草坡延伸到很远处的两座山头上长满了松树,象一个人宽大的肩膀上披了蓑衣在静坐。
太阳从两座丘陵般的山上射过来玫瑰色的光,在前面的车窗玻璃上照了个亮影,亮影在乘客中哗地扫过去。这也是外部世界对人的刺激。他们都看了孩子那边的窗外,是一座大河滩,乱石堆积,河水浅小,颜色昏黄,河那边白杨树茂盛,掩映着几户人家,这些树丛的南面,树梢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出透明的金黄。岸那边又是灰黄的山,圆包形,绵亘的土岭形,而她,将永别这种地貌了,这是靠近河西走廊的山谷所特有的地貌。他的眼光停在玻璃上,眼光里飞速地掠过灰黄的山岭。他的胳膊随车的晃动触一下她,产生强烈的爱抚感,她的胳膊和身体这么柔软,曾经多么亲切甜蜜的一个人,那么温顺而坚韧!他却对她缺乏深刻的认识,就象在一百年以前,人们对地球的内部缺乏认识。但是将要永远也见不到她了。凭他的力量,不能对她怎么样;今后,不要说爱,就是恨也再没有机会了。他沉思着,闭上眼睛。
汽车转向另一条路,向西南方向行驶了。他被摇晃得睁开眼睛。
路两边的防护栏杆外,是油菜花金黄的一片,蝴蝶在花丛上翻飞,车窗里飘进浓郁的香味,连乘客们也来了精神。她与她的女儿望着那些油菜花,她们的脸几乎贴在一起,轻松自由地微笑着。他望着她们,醒悟到:她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没有任何的拘束压抑,舒心自由地微笑过!她仿佛回到少女时代,在黄花丛中跑着,采摘闻嗅,做着清纯甜蜜的梦。
他看着她们的背影,感到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
他今天早上起来,又决定把药送给她,就把药装进包里。此刻,他把包里的药瓶隔着皮子攥着,又松开手,苦笑了一声。这些苦味的丸药,黑色的药渣,除了让她吃“药”,再有什么意义呢?难道真能带给她些愉悦吗?难道真能增强她的免疫力吗?真能使她的身体康复吗?为什么不去运用预防医学,使她免于肺炎的侵袭呢?为什么刚开始不用良心和责任去爱,早带给她幸福快乐呢?
他原来想在临上飞机前,把药瓶送给她,求得她的一些宽恕,现在觉得,已经没有必要了。
到机场了,飞机的声音压过喧嚣声,轰隆隆响。灰黄的山岭分开,眼前一片开阔,他的心紧缩着,又被广阔天空上的太阳和四散开的山峦所感染,振作起精神。车停下,他等她们检查过后,一起到售票处买了票,与她们坐着等起飞的时刻。
广播响了:飞往深圳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
她想提前还给他买车票和机票的钱,怕他不要,又伤他的心,就等待着起飞的时刻。广播响了,她站起来,从黑皮包里掏出一叠钱,是一千八百元,放到他的手上。他吃惊地看着她,变了脸色,看到她微笑、柔顺而坚韧的目光,知道是不可挽回的了,双手呆呆的,极不情愿去接住钱。她拿起他的手,把钱放到他的手心里,他接住,低头望着一旁,沉默不语,悔恨交加。
他难过得几乎要失声痛哭,用指头胡乱地擦着眼泪。
她从她的黑得发亮的皮包里掏出来一包东西:
一束马莲花!
他惊呆了!
她象一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大方地拿起他的另一只手,让他拿着。他接花的时候,握住她的手,她没有动,让他握着,眼神清新柔顺。然而,乘客们在列队走向飞机,她要走了。
他们的手慢慢地滑开。
“永不忘怀!”她说。
她的女儿向他招手:
“叔叔,再见!”
她们离去了。
她右手提着一个皮箱,左肩挎着装马莲花的黑皮包,左手拉着女儿,乳白色的风衣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她的女儿背着大书包,装得鼓鼓囊囊。两个背影如一朵玫瑰花和一朵蒲公英渐渐远去,在很远的地方,她们与人流混成一队,慢慢向飞机舷梯走去。
她转头回望他,身体随着人流运行,不觉走出人流,成为单独的一个人,回过神来,加入到队列里才向前看。这样遥远的距离,他还在望她的眼睛。
在她踏上舷梯时,转头又望北方,他仍在望她的眼睛。
她们登上舷梯了,在她拉着女儿走进舱门时,站住,最后一次回过头来。
他扶着铁栏杆,略仰着头,象雕塑一样一动不动,眺望着王丽莎的眼睛。
她让开身体,让其他的乘客进舱门,走到舷梯的一侧,凝望着他的远影。女儿站在旁边也眺望着很远处栏杆边的人影,在她看来,那个人影同老鹰一样大。只剩她们两个乘客了,王丽莎举起手,如天鹅翅膀划动空气似的向他招手,手臂飘柔地划动蓝色的天空,给北方留存和传送去一个永恒的思绪。在飞机上工作人员的催促下,她拉着女儿慢慢退回舱门里。
舱门关上了,舷梯快速离开。
飞机发出巨大的声响,把机内外所有人的情绪统一起来了。它动了,慢慢滑动了,象一条鲸鱼转了半个方向,稳妥地驶向跑道。进入跑道后,滑动快速了,发出更响的轰鸣声,越来越快。飞机上银白色和涂着鲜红大字的“XX民航”显得比平时更加醒目。它在跑道上沉重而迅速地滑行,速度非常快的时候,忘记了重量似的,头部终于翘起来了,带动着机身脱离了地面。机尾脱离开地面的一瞬,好象显示着:一件新的事终于开始了。飞机划破空气高速向前冲击,终于飞升起来了,——这样一个巨大的东西脱离地面,运走那样多的人,叫人不可思议。它冲向南面的天空,传来均匀的轰鸣声,几秒钟后,声响象有时人们一夜没有睡好耳朵里嗡嗡嗡的那样。当它象飞鸟一样渐渐在空中越来越小时,刘之江仍雕塑般凝望着它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