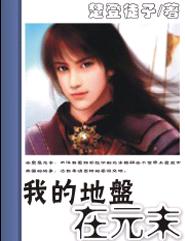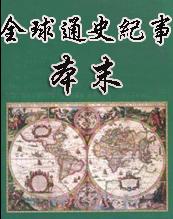濒死的地球-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声音再次传来,粗粝嘶哑。钨兰·铎尔不由得寒毛倒竖,同时发觉,伊莱的手掐进了他的胳膊。
“五千年!”那声音吼道,“都五千年了,这些家伙还在争吵?时间没有教给他们智慧吗?看来得用更加强有力的手段了。洛戈尔·多美东弗会让他们瞧瞧什么是智慧。瞧着!”
下方传来轰然巨响,上百声尖锐的爆炸声。钨兰·铎尔和伊莱赶紧奔到窗边往下看,街上是一番触目惊心的景象。
通往城下的门廊打开了。每道门里都甩出一条巨硕的黑色透明胶状触手,质地跟滑动步道很接近。
触手升向空中,发出数以百计的枝条,追逐着仓惶四散逃窜的安普理达弗人,逮住他们,剥去他们身上绿色灰色的袍子,然后把他们抛到宽阔的中心广场上。冰寒凛冽的晨风里,这些安普理达弗的居民光溜溜地混作一堆,根本分不出谁是绿族谁是灰族。
“现在的洛戈尔·多美东弗有长而有力的许多胳膊,”那个隆隆响的声音说,“跟月亮一样强,和空气一般人所共见。
“我是洛戈尔·多美东弗,安普理达弗最后的统治者。你们竟沦落到这般境地吗?住着狗窝,吃着猪食?看着——片刻之后,我就会弥补五千年来的疏忽!”
触手们生出上千条附肢——有坚硬的角形刀具,有喷出蓝火苗的喷嘴,还有巨型铲子,每条附肢上都有一只眼睛。这些附肢席卷全城,哪里有瓦砾或毁损,触手就在哪里挖掘、拆卸、爆破、焚烧,然后就地喷出新的东西。它们所过之处,留下的都是崭新锃亮的建筑物。
装备齐全的触手收起几辈人积下的垃圾,集满之后就在空中高高扬起,猛力一甩,把垃圾远远地抛进海里。有刷着灰漆或绿漆的地方,触手就抹掉那些颜色,喷上各种各样新的颜色。
每条街上都奔跑着这些巨大的根须,细须则伸进每座塔楼、每间屋子、每个公园和广场——摧毁、筑模、建造、清扫、修缮。洛戈尔·多美东弗渗透了安普理达弗,就像一棵树的根须一般,牢牢抓紧了土壤。
不过几次呼吸间,一个崭新的安普理达弗就取代了废墟瓦砾,一个熠熠生辉、闪闪发亮的城邦——骄傲、无畏,可与红日比肩。
钨兰·铎尔和伊莱看得神魂颠倒、目眩神迷。这可能是真的吗?会有这样的人物能在众人眼前将一个城市迅速推倒重建吗?黑胶巨臂刺向岛中的群山,挨个搜过冈斯吃饱后蛰伏于内的洞穴。巨臂揪住它们,拎到半空,悬在挤作一团的安普理达弗人头上——上百条触手吊着上百个冈斯,像一株长着妖果的怪树。
“看啊!”那声音隆然作响,一副得意放肆的语调,“这就是你们所畏惧的东西!看看洛戈尔·多美东弗怎么处置它们!”
触手一弹,上百个冈斯就飞了起来——四肢大张地团团转着飞过安普理达弗的高空,被远远抛进了海里。
“这家伙疯了。”钨兰·铎尔对伊莱嘀咕,“一场长梦搅昏了他的脑子。”
“瞧瞧这个新生的安普理达弗!”威严的声音继续隆隆震响,“见证它兴起,看着它毁灭。现在你们死吧!时间已经证实你们不值得——不值得膜拜新的神祗洛戈尔·多美东弗。我身旁的两人将创建新种族——”
钨兰·铎尔心中响起了警铃。什么?他得被摁在这个疯子超人的大拇指下,随他摆布,在安普理达弗讨生活?没门。
或许他再没有机会这么靠近这个脑子了。
他拔剑急掷,扎穿了那条透明胶柱一一钉中脑子,把它穿到了长剑上。
空中炸响世上最恐怖的恸嚎。男男女女在广场上乱成一锅粥。
洛戈尔·多美东弗清扫城邦的触手在剧痛中上下抽打,像受伤的虫子抽搐肢腿。高楼大厦接连坍塌,安普理达弗人尖叫着在灾变中四散奔逃。
钨兰·铎尔和伊莱奔向停着飞车的天台。他们听到身后追来嘶哑的低语——话音断断续续。
“我——没——死——没有!如果其他的一切,如果所有的梦都毁了——我会杀了你们俩……”
两人跌跌撞撞地扑进飞车。钨兰·铎尔驾着它腾空飞起。一条触手好不容易忍住抽搐,猛地挥出,想拦下他们。飞船蓦然转向,刺往蓝天。触手戳来,想扎穿车身。
钨兰·铎尔用力拉下加速杆,空气在车尾哀鸣尖啸。紧跟着的就是垂死神明的漆黑触手,竭力想打下这只伤了它的飞蚊。
“快!快!”钨兰·铎尔哀求飞车。
“高一点,”一旁的姑娘喃喃说,“高一点——快一点——”
钨兰·铎尔翘起车头,跃过迎面扑向飞车的山坡,触手紧随车后——一个直插天宇的巨怪,一道扎根在远方安普理达弗城的黑虹。
洛戈尔·多美东弗死了。那条巨臂突地变成一篷烟,悠悠沉往海面。
钨兰·铎尔让飞船全速前进,直到把小岛甩在地平线以外。他减慢速度,叹了一声,松了口气。
伊莱突然扑到他肩上放声大哭。
“别哭,姑娘,别哭。”钨兰·铎尔劝慰着她,“我们安全了,永远不会再跟那个鬼地方有什么瓜葛了。”
她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问道儿:“我们现在去哪儿?”
钨兰·铎尔的目光带着疑问扫视过飞车,盘算了一番。“车里没有能带给坎代弗的魔法。不过,我会有个好故事讲给他听,他会满意的……他肯定想要这车。可是,我得考虑一下,我想……”她小声说:“我们难道不能往东飞,一直飞一直飞,直飞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也许能在那里找到一片安静的草坪,还长着果树……”
钨兰·铎尔向南方望去,想起凯茵城宁静的夜晚和酒红色的白昼,想起他已经当成家的宽敞宫殿,想起坐在上面俯望桑瑞尔海湾的睡椅,还想起那里古老的橄榄树,节日里的滑稽表演。
他说话了:“伊莱,你会喜欢凯茵的。”
第六章斯费尔的古亚尔
斯费尔的古亚尔生来与众不同,一早就证实他正是让自己父亲大人烦心的根源。他的外表没什么特别,脑子里却有一片渴望得到营养的空旷地。他像是一出生就被施了法术,让某个专门捉弄世人的魔灵把他变成了个磨人精,所有周围发生的每一件事,不管有多么鸡毛蒜皮,他都当作奇迹一样大惊小怪。刚刚经历过一个四季轮回,他就会冒出下面这种问题了:“为什么四方形比三角形多一条边?”
“太阳黑了以后我们要怎么看东西?”
“花能长在海底吗?”
“晚上下雨时,星星会不会溅得嘶嘶滋滋响?”
他的父亲不耐烦地这样回答说:“有规定,四方形和三角形要守规矩。”
“我们得摸黑走。”
“我从没弄清过这事,只有馆长才知道。”
“绝对不会,因为星星在雨的上面,比最高的云彩还高,在永远不会凝结成云的稀薄空气里飘游。”
古亚尔长成少年时,脑子里的这片空旷没有变得苍白无力,反倒悸动着更强烈的渴望。于是,他又问了:“为什么人被杀就会死?”
“美消失后去了哪里?”
“人在地球上已经生活了多久?”
“天空之外是什么?”
面对这些问题,他的父亲忍着没说刻薄话,这么回答:“死亡是生命的延续;人的生命力就像气泡里的空气。泡泡一戳破,生命力就往外跑啊跑地散掉,就像渐渐褪色的梦。”
“美是爱用以欺骗眼睛的光泽。因此可以说,当心没有了爱意的时候,眼睛就找不到也看不见美。”
“有人说人在地球上出现就像蛆从尸体里生出,有人认为最初的人类需要一个住处,这才用法术创造了地球。这个问题太复杂,只有馆长才能给出精确答案。”
“是无尽的荒漠。”
古亚尔时而独自沉思,时而向人发问,提出各种推论然后——说明,直到某天他发现自己成了人前背后的笑料。当地风传,古亚尔的母亲生他的时候,有只格赖妖偷了他的一部分脑子,所以他现在不遗余力地想把缺失的部分找回来。
古亚尔从此离群索居,孤身一人在斯费尔苍山翠岭间徜徉。但他总是喜欢刨根问底,总是让周围的人绞尽脑汁。最后,他的父亲大人烦得不肯再听他提问,所有该知道的人们都知道了,没用的、鸡零狗碎的东西全都可以扔到一边,一个正常人只要知道剩下的那些就足够了。
这时候古亚尔刚刚成年,这位年轻人虽然瘦但很结实,有双又大又亮的眼睛,特别喜欢一流的风雅衣裳。但他仍旧是个大麻烦,这种麻烦时不时就要在他的嘴角上暴露出来。
听到父亲恼火的声明以后,古亚尔说:“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以后再也不问了。”
“好吧,”他父亲同意了,“就准你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你经常对我提起馆长;他是谁,我能在哪里找到他,从而减轻自己求知的痛苦?”
有一阵子,父亲细细观察着儿子,以为他发了疯。然后,他语调平静地回答:“馆长看护着人类博物馆,一座位于坍墙之地的古时候的传奇场馆。坍墙之地在费阿奎拉群山之后,阿斯科莱斯北部。不知道馆长或博物馆是不是还在,但如果照传说讲的,馆长什么事都知道,那么他肯定懂得长生不死的巫法。”
古亚尔说:“我要去找馆长和人类博物馆,可能我也会同样什么事都懂。”
当父亲的很有耐心地跟他讲:“我会给你那匹雪白的良马,把膨胀蛋给你带去居住,还给你可以在夜里照亮道路的火光匕首。另外,我给你一路平安的祝福,只要你不离开大道游荡,危险就不会靠近你。”
古亚尔压下涌到嘴边的上百个新问题,比如父亲从哪里学来这番施法本事,只是接受了赐予的礼物:马、魔法住处、刀柄会发光的匕首,还有保护他的祝福,使他不受阿斯科莱斯昏暗道路上危害旅行者的恶劣环境骚扰。
他给马备上鞍,磨利匕首,最后看了一眼斯费尔的老家,就此策马北上,心里的空旷因为求知的甜蜜压力而悸动不已。
古亚尔搭上一条老驳船渡过斯考姆河。上船后就离开了大路,祝福失去了效力。船主看上了他的一身富人行头,想拿棍子敲昏他。古亚尔挡开了这一击,一脚把他踢进黑乎乎的河里,让他淹死了。
沿斯考姆河北岸走时,古亚尔看到了前面的玻菲隆断崖,望见过凯茵城黑沉沉的杨树林和雪白的石柱,桑瑞尔海湾的隐约波光。
信步走过城里破落的街巷时,他朝没精打采的当地人提出一大堆洪水般的问题,害得其中一个拐弯抹角地打趣他,推荐他去问一个职业占卜师。
这个职业占卜师有个小篷子摊位,招牌上写着“奥莫克罗佩拉斯蒂尼密教”。他是个瘦瘦的男人,棕色皮肤,眼眶发红,有一把花白胡子。
“报酬怎么算?”古亚尔小心地问。
“我回答三个问题,”占卜师告诉他,“二十特斯,我会用清楚明白的话阐述解答;十特斯,我就用隐语讲,偶尔有点含糊;五特斯,我就说个寓言,你得按自己想的解释;只给一特斯,我就用听不懂的语言嘀嘀咕咕。”“首先我得问问,你的学识有多广博?”
“我了解一切,”占卜师答,“血红的秘密和漆黑的秘密,广阔摩索兰大地失落的法术,鱼的生活和鸟的语言,我无所不知。”
“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些东西?”
“靠的是纯粹的感应,”占卜师解释,“我退入店铺中,把自己关进一个没有一丝光亮的地方,如此隐世避俗之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