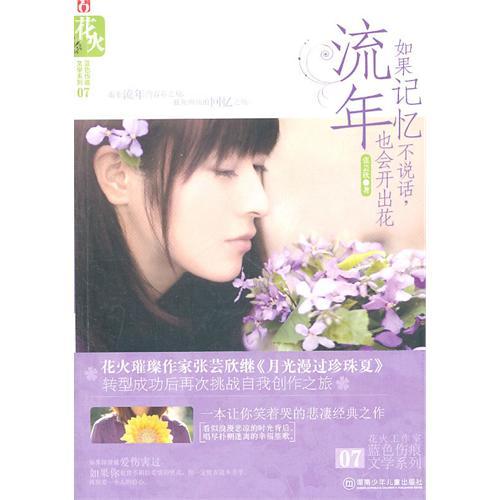写下些回忆-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原来是买春去了。当时,我没想的这么仔细,但是,大致上差不多,每一个重点都闪电般的闪过,然后在闹海里连成一条完整而清晰的主线。
我气的想哭。我感觉我这人生算是一下毁了。我还以为自己占了多大便宜,我还曾经多么依恋爱慕过她,原来是被人玩弄了。我哆哆嗦嗦往外走,好像已经哭出来了。我下了半层楼梯,正巧碰上沈芳。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很不得一拳砸过去。我狠狠的瞪了她一眼,一把推开她往楼梯下走。沈芳可能被我狰狞的面孔吓着了,一把拉住我,“景明,你怎么了。”我回过头,脚跨在台阶上,扬着脸,冲她恶狠狠的说,“回家。”我觉得我再说下去就忍不住要动手了。她却看上去很迷茫,“为什么啊?”我“嗤”地冷笑一声,眼泪不争气地溜出一滴,我一把摸去,转过头,冷笑着说,“我警告你,你以后想包二奶小白脸最好看对人,省得当冤大头。请你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我年纪轻轻,不想跟你们这帮变态公子小姐搅得感染个艾滋病,我家就我一 ……”我话没说完,就看见沈芳右肩一抬,我下意识往后一仰,但是还是被重重一个大耳光打在脸上。(看官们是不是很解气呵呵)
我整个人一下失去了重心,身子迅速地往下倒去。我心里一惊,下意识把身体想转过来,脚步能跟上身体的移动,但是,上身下降的太快了。我踉跄着趟了几步,终于整个身子扑在台阶上。再和地接触的瞬间,我下意识用手挡在胸前,这个姿势,虽然缓解了第一次的冲击,但是手被卡住,整个人顺着楼梯向下滑去,最终,脸作为第一着陆点,一头扎在地上。还好有地毯。我有点庆幸。但是,这个跤摔得我真的是眼冒金星。我长着么大,第一次用切身体会来验证,老祖宗们造词都是有根据的。我当时绝对是睁着眼,但眼前一黑,无数金色的小点出现。
我差不多摔傻了,但是,仍然下意识爬起来,往外走。眼镜在地上,我看不清,拿起来带上,发现变形了。我觉得身上再往下滴什么,嘴唇上湿湿的,嘴里有点咸,我以为是哭的眼泪,摸了一把,一手鲜红。
我听到有人叫了一声,好像很多人跑过来。我想我算是狼狈到家了。我又抹了一把鼻子,那红色不断的涌出,我忍不住眼泪涌出,但是,我坚持压抑着不让自己发出声音来。
人们围了过来。
我听到有人说,“纸,纸,急就箱……”
有人说,“眼睛,眼睛也破了……”
有人说,“你怎么样,怎么样?……”
有人上来帮我拿纸堵住鼻子,我眼里看不清他们,都是白花花的一片,也许是我的眼泪太多了。
有人问,“怎么会摔下来?……”
有人说,“是不是地毯卡住鞋底了……”
有人说,“台阶上的地毯太厚了……”
我没说话,只是掉眼泪。我觉得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丢人过,我只是哭。
我被一个男人搀住,扶着往外走。我脚步机械地跟着,去哪里无所谓,赶快带我离开就好了。
我坐进一辆车,我看到前面坐进一个人是丹尼。车开动了。我有点清醒过来。我下意识往窗外看去,门口站着一些人,脸是模糊的。我下意识想到,沈芳呢?但马上又想,你真是贱。
我在后座上哭了差不多一路。我觉得我真是倒霉,以后名声算是丑了。赶快让我回国吧。
车开了大概十来分钟,到了一家医院。
丹尼夹着我去柜台,出来一个人看看,说,登记一下。
登记完,他只给我们一个方向,“那里是来访等候区,你们去那边等着,到时候电子牌上会显示你的名字和诊室。”
等候区是一间大概20平米地屋子,放着一排排椅子或沙发。已经坐着大概十个人左右。我看到一张没人坐的沙发,坐下去,低着头。我不想看到丹尼,我谁都不想见到,最好地上开个缝,让我钻下去再把我埋起来。
我低着头坐了一会儿,丹尼好像就没跟近来。我瞄起一点眼睛,看不大清,但是他的确不在附件。似乎感觉轻松一点。我直起身,抬头看了一眼指示牌,上面显示着一个印度兄弟的名字,后面的括号里是(处理中),停了一下,名字消失,换了一行:请关闭手机。我摸出手机扣下电池,看到手上血赤呼啦的。我心想,什么时候轮到我啊?我觉得我的鼻子有点疼。我轻轻摸了一下鼻梁,还好,是直的。上大学的时候,书上讲过,要是鼻骨断了会歪掉或是塌了。摸上去似乎是没塌,不知道歪了没有。我转了转头,有没有镜子?却看门开了,走进一个人。我马上迅速又把头底下,两只胳膊架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那人走到我跟前站住。我看到她的鞋子。我看到她的小腿弯了一下,我赶紧又把头低的更深一些。人蹲在我身旁,我看到一只手伸过来,似乎是要摸向我的脸,我忍不住了,一把把那手打开。我气势汹汹坐直身子,抬头挺胸,目视前方。前方视线中有我不想见到的障碍物,无所谓,我当你是透明。其实,也看不是很清。
那人似乎接着半蹲在那里。操,卿家平身吧。她果然站起来了,真乖。那身躯似乎走进一步,又转身出去了。我长长舒了口气,挺得太直了,得活动一下腰身。她似乎挺担心我的。
我觉得我似乎好像不是很恼了。于是便想,你怎么人格那么卑微啊?刚被羞辱完就转脸忘?你妈要是知道生了你这样不自重的货色,让她脸往那儿放?哎,我妈这人正直了大半辈子,在单位里,上上下下没有一个说她坏话的,要业务有业务,要人品有人品,难得的是上不媚权贵下不欺弱小,没成想,却嫁了个道德沦丧的夫君,生了个没出息的窝囊废孩子(这厮还虚荣的要命),为了供这个窝囊废上学,忍气吞声过着有名无实的婚姻,而这个窝囊废却被人当白痴一样玩弄,却自我感觉良好并沾沾自喜炫耀。
想到这里,我心里一阵酸楚。我觉得我妈生了我真是怨大了。我就是一包袱,不但拖累她,还带给她耻辱。我眼泪又刷刷刷。我想,我就是太没志气了,人家扔过来个啃剩下的馒头,我都能上去叼着。行,我发誓,从今往后,饿死是小。我要是以后再沾你半点好处,我当你面儿,让你拿鞋塞我嘴里。
我正恶狠狠的发毒誓。门又开了,那个身影又飘过来,没有说话,只是把手伸过来,手里是一瓶水。我心想,晚来那么一步啊,可惜,可惜,我可不想品尝你鞋的味道。我一脸正气端坐着。那手在我面前悬了片刻,把水放在我脚边。我的余光看那身影飘去边上的椅子坐下,我又把腰挺直了些。飙吧。我从小就不怕有人跟我飙,一飙我就来劲。
我按着标准军资坐了大概20分钟。我就开始后背有些疼。我瞅了一眼电子牌,居然还是那个名字,拜托老大,你要是真是快死了想嘱咐几句,那您换个地儿说行不?我接着坐军资。我想到大学军训的时候,要是有谁惹恼了教官,最狠的是大太阳地里蹲军资,然后是站,最后才是坐。但是,我怎么感觉今天坐的那么不爽啊?
我看着电子表的时间一点点走,我觉得腰快断了,我心里把英国皇家医院从里到外骂了不知道多少遍,顺带着也骂了王室。我忿忿不平,您没看着我头破血流的吗?!但是,那电子牌,仍是很久才调一下,然后就顿住……
那身影倒是悠闲,喝着小水,翘着腿,靠着沙发。这脚翘完了那脚翘。真是没天理,为什么凶手可以逍遥法外?而受害者却在阿把地狱服刑?你长得比我漂亮就能乱打人?那我还比你长得高呢!操!还真以为我不会打人啊。怕的是一招上去你下半生只能“志坚”了。办公室怕是坐不了了,干脆写本儿回忆录我的上半身然后混个美女作家,倒也能养活自己那本特立。
我正恶毒的给沈芳办理工作调动,却见她起身走了。我敢快趁机活动一下腰身,左三圈右三圈,妈的,还没到我,我破这么大口子你准备让我等多久?直接上手术台输血?我知道你是免费,但是您这么“盛情”也过于破费了吧?
身影又开门进来,走回沙发坐好,似乎是对我说,“要再等一下,今晚又很严重的急诊手术,大夫不够。”我端着军资,我百炼成钢,我当你放气。
终于,差不多过了4小时,我先是听到B一声,然后,电子牌翻出我那亲爱的名字。我差点泪如雨下,罗马到了!延安到了!同志们胜利了!
我目不斜视站起身来,我几乎从腰往下没有知觉,走了几步才渐渐恢复成迈左脚伸右手的状态。我想,要是谁拍电影需要扮演僵尸的群众演员,可以来找我,要是请金城武演被僵尸QJ的男演员,我给你们打个8折。
我努力翻上手术椅,护士阿姨过来亲切的捧起我的脸,温柔的说,“亲爱的,来,我先把你结的疤揭了”
我哆哆嗦嗦问,“我是不是流很多血啊?”
阿姨笑着说,“只要动脉没有伤到,血是会自己止住的。”
我内心哭道,你们就是因为这个居然让我等那么久,真是会省钱啊,止血药都用不着了。
我又说,“我眼睛好像破了。”
阿姨说,“怎么破的?”
我说,“好像是被眼镜扎了。”
阿姨说,“那要打一针破伤风。”
我说,“会不会瞎了?”
阿姨说,“只破了一点点皮。”
我又问,“鼻子呢?断了吗?”
阿姨摸了摸,“没有,断了会塌下或歪掉。”
我心说,早知到您是这水平,我干脆自己治疗好了。
我建议,“也许裂了也说不定。”
阿姨说,“不会的。”
我:……
阿姨清理了我鼻子里的血,眼睛上巴了一小块儿半透明胶布,让我扶着床给我打了一针,然后说,“好了”。
我估计,也就是不到15分钟的样子。我觉得,皇家医院的工作效率很是诡异啊。
出了门。我看到沈芳迎过来,看了看我。我径直往外走。出了大楼,丹尼站在楼外,跟我伸出手说,“这边。”
我连扫都没扫他一眼,接着走。
我觉得有个人一直在后面跟着,从脚步和气势上,我知道是谁。
我拐出医院大门,夜深人静连半个人影都没。我也不知道该走那边,随便扬着头往前走。又走了几步,有人伸手拉我袖子,我摔开,又拉,我再甩,还拉!我一下转过身去,瞪着那双眼睛,没带眼镜,天又黑,看不是很清。那是怎样的眼神我不知道。但是,随即飘来的声音,却是一阵异常的冰冷,“有些话,我想跟你说清楚。”顿了一下,“说清楚,对你我都好。”
我有点迟疑。我没有再走。我站了一会儿,直到那辆车来过来,停下,我看到沈芳上了车,车门开着,我还是站着。我不知又站了多久,终于还是,转了身,迟疑着把右腿跨进车门。我有些怀疑自己的动机,我又想,“看看这家伙又耍什么妖蛾子也好。”
我仍是昂首挺胸跟着沈芳回到楼上,仍是那间给我一道霹雳的房间。不过,我觉得我也真是见过“世面”了,索性大咧咧一屁股做到沙发上,靠着后背,把一只脚翘在腿上,脚尖故意竖起来(据说这样表示不屑)。
我故意还晃着脚,也不说话。沈芳也站在那里不说话。我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