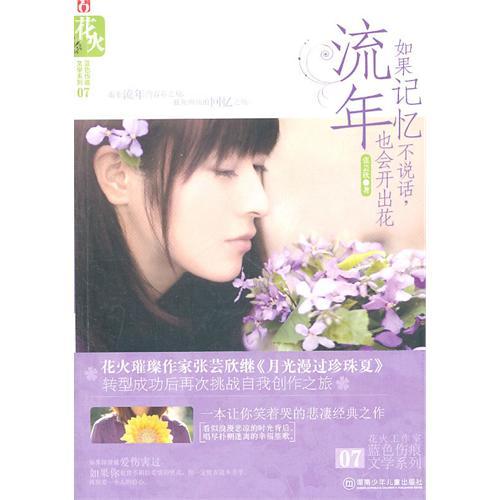写下些回忆-第1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为最早在沈芳未到之前,我总是上完课后和同学们一起出去耗时间,已经成了习惯。在沈芳来了
以后,我便假称自己水土不服拉了肚子,趁机推了那些邀约。也就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每次我和沈
芳出门,总要像地下工作者那般,神神秘秘分头行事。往往是她前我后,分别走出酒店,按照说好
的方向,走上几个街区,然后,等在某处胜利会师。
开始,我觉得很别扭,也怕沈芳因此有情绪。不过,出乎我意料的竟是她的乐此不疲。有时,她走
在前面,趁我不备还会故意躲起来。等我到了她所说的“XXX酒吧”或是“XXX路第X根路灯”的时候,
左右张望不见身影。每到这时,我便会不知为何焦急起来,急到拉住路上的行人开始操着英语打听
。也亏了这个国家人的英语普及的相当好,每个人都能听懂我想找什么,但是,往往答案总是一个“
Sorry”。等到这时,我亲爱的主子大人,便会重新现身江湖,用一副明显看得出是“表演出来”的四处
张望样子,晃在马路对面或是街角处。第一次,我哭笑不得。第二次,我索性摘了眼镜开始焦急着
装傻。
主子眼看自己被还施彼身,气忿忿地走过来,擦肩而过是,小声地还要带一句“一看就是装的。”然
后一把抢过我手里的眼镜,急步前走。
我眼睛的度数不高,只有200,不过很奇怪的裸视级差。这下可好,那种在酒店屋里的“寸步不离”被
我发扬到了该国的大马路上。本就陌生的街道,加上几乎完全不懂的路标指示,我真的就成了一个
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睁眼瞎。
我就这样像个小跟班儿似的跟在主子后面,亦步亦趋。走到街角无人处,主子猛地站住,转过身来
,在我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飞快的吻住我。当然,主子的吻对我而言,永远是甜蜜的。我就算
再迟钝也马上会反应过来。不过,仍然是,还没等我的“咸猪手”搭上主子的纤细腰身,便又被迅速
推开到一边,一起的还有低低地一句“有人来”外加一声清脆的“呵呵”。人影再飘开,我再茫然地跟上
。
如此往复,主子玩的不亦乐乎,乐到吃饭的时候,还忍不住笑出来。吃一口,“呵呵,真好玩儿。”
喝口水,还没等咽下,几乎要憋不住喷到我脸上,“。。。你表情怎么那么。哈哈。。”
看这她笑,不知为什么自己也很快忘了平日想的那些烦心事,我也笑。然后,两个人一起笑,笑着
回去,临到酒店,再次分开。
到了屋里。我说,“感情儿您这总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上的行为可是有待批判啊!”
“怎么了?不愿意啊?”她倒是歪着头,一副调皮着的笑脸,让你严肃不起来。
“哎呦喂,我哪敢不愿意您啊?!”我实在是无可奈何,只有摇头的份儿了。
“那是当然的。”——瞧见了吧,人还特骄傲自满。
我彻底妥协,“我特愿意,贼愿意,我就是爱招你虐待,我痛并快乐着!”
主子迅速掏出手机,“Wait;wait。。Wait;wait。。let me record。。。Say again! ”
得,我贱死了。
当然,每一对爱恋着的人们的生活,总不可能都是甜言蜜语的。我们也不例外。
其实,如果说是争执,也不过是一些问题上的老生常谈。
按主子的话说,我们的这些,“根本不是争执,只是,就某些问题,尚未达成共识。”
每次听到她学我的口气说话,我总会再激动,再郁闷,再张牙舞爪也甭不住地笑出来。
晚上睡觉前,我们习惯经常依偎着聊天,有时聊些有趣的事儿,有时,则是对“尚未达成共识”的问
题,“展开广泛而深入”地讨论。
我跟她讲起我认识的一位长辈。那是我从小心目中的一位英雄之一。自打我懂事起,我就常和院里
的一帮小孩子们听大人讲述他的故事和传奇,从抗战,到解放,到大跃进,到文革。记得我刚入队
那天,第一次带上红领巾,心情激动万分,中午回家吃饭。到了院子里,碰到这位老人正走下汽车
。我平时难得见到他,他不住在这里。他也难得跟我说什么话。那天,或许是我太激动了,或许是
激动到神情异常。他看到我,竟然招招手让我过来。我走过去,短短的几步,心中盘算着要跟他讲
些什么,走到跟前,大脑仍是乱的。只好学着人家的样子,敬了个军礼,然后叫了声“爷爷好”。老
人笑了,弯下腰纠正我说,“你脖子上戴的是什么啊?这个礼可不是你敬的哟。”我这时才意识到,
几乎羞红了脸,于是,马上又补上一个少先队礼。他笑了,点点头,“要好好学习,将来建设祖国。
”
这句话,曾经让我鼓舞了一段时间。当然,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很快便就忘记了。没什么奇怪,
在我青少年的时代,这样的话,几乎天天月月无数次听到。电视里听的,和广播里听的,其实,也
没有太大的差别。
很多年过去了,我一天天长大,老人一天天衰老下去。等我上了大学,老人也在戎马一生后走向了
生命的尾声。我和家里的长辈一起去探望他,那时,他还神智清晰,只是虚弱。他卧在病榻上,虚
弱地听我们送上的嘱咐和问候,偶有几句简短的回答。临到结束,他忽然抬起手指指我,“多大了,
念没念大学?”家人赶快接上,“念了。”老人点点头,“好。”
他的儿女继续说,“学习不错,等到毕业了要出国。”
他又点点头,“好。”为了逗他多说几句,他女儿接着说,“您说出国是去美国好啊,还是去英国啊?”
仍是点头,“都好。”
“去帝国主义国家也好啊?”
“好。”
大家笑了。笑那些大家都觉得显而易见的事,包括我在内,大家都觉得,他老了,而我们,还年轻
。年轻,总是聪明的。
临到走,跟他告别,都知道这一别兴许就是永别。大家问他,“有没有什么希望给下一代嘱托一下啊
?”
他看着我,那眼神早已不是若干年前的慈祥,也不是电视照片上的英武睿智。那眼神,本充满了浑
浊,但那时,似乎真的猛地亮起来。
他张口,似乎费了很大力气,指着我说,“你要留学,好。记住,不作汉奸,不作亡国奴,不当洋买
办。”
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当时,包括现在,仍然相信,那是他真实的想法,而不是作给人看
的口号。他的最后说给我的这句话,我一直在体会,尤其是出国后,直到现在。
我问沈芳,我固守的有些东西在她看来是不是过于迂腐。她曾说,是。那天,我又问他,她说,“兴
许你和我父亲哥哥一样吧。英国气候又好,生活又舒适,可是他们宁可呆在香港,那么多的人。夏
天,哪里都去不了,那么的热……”又说,“也许是,我出来太早了,又一直没有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
我曾经,时常,为了自己所谓的“家庭成分”感到非常的拘束和困惑。干的不好,怕出去了连着家人
都被人笑话。干得好了,又要听那些所谓攀附的冷言冷语。尽管,相对于很多人,比如说沈芳,我
的家庭或许也不值得一谈。不过,一些从小灌输在血液里的东西,的确一时无法轻易抹去或是转变
。我跟沈芳说,“我相信,如果,你是我这个年纪出来的,你会比我更固守那些传统。”
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早在出国前的20年里被那些“传统”包围了。出了国,哪怕是再繁华的世界,
那些固有的传统,仍然犹如1941年冬天的莫斯科,任他十万铁骑,我自巍峨。
我时常会开玩笑的跟母亲说,“要是咱是种地的,那你闺女现在混到这份儿上,怕是您早就嘴都合不
拢了吧?”母亲也总会笑着说,“话是不错,不过也别得意,你看人家……”
其实,我不觉得这是盲目的虚荣,只不过,从我母亲出生,这种永远朝前看,永远不放弃,永远检
查错误迎头赶上的价值观,就已经充斥在他们那个年代,他们的生活中了,一晃20多年后,再传给
了我们。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我们的前辈,是确实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流过热血的。所
以,到了如今,看到社会上的那些是是非非,我,包括和我一起长大的同龄人,都会有更深更强烈
的看法。而那位老人,临别对我的赠言,“不作汉奸,不作亡国奴,不当洋买办。”对我的震撼,也
自然不一般。
出国后,我为鬼子打工。签完协议的时候,我想起老人的那句话。我心里感到很无奈,又随即假惺
惺地安慰自己,还好不是当买办。
后来,在公司干的不错,认识了不少能人。这时,便有国内的朋友托我联系把国外的那些差价高的
相关器械或是配件转手卖回去。目前为止,我没有做过。因为,我觉得把那些砸了洋商标的东西倒
回去,卖出国内品牌的几倍价格,实在是……。别人可以作,我不想。因为,个人觉得,不值得。
我也想多挣钱,尤其是重新和沈芳开始以后。我也在工作之余利用自己得到的信息,搞些小动作。
不过,我反过来,从国内找货,卖到英国。谈价钱的时候,我没有压国内的价,国内竞争非常激烈
,一听有出口,都比较踊跃。我想,兴许利润已经不多了。不过,后来,倒是国内给的回扣远远超
过了鬼子。想想里面的蹊跷,我又安慰自己,虽然很不幸最终没能保住晚节,还是当了洋买办,不
过,这样的买办,总还是良心稍有安慰。当然,我也知道,我这不过又是给自己找理由,当阿Q。
所以,我当着沈芳的面,给国内的厂商写email,我说,这个供应商是XXX公司的供货者,这批货验
收后,砸上标签很可能会卖去XX,甚至是中国。我觉得,自己很像打入敌方阵营的无间道。
沈芳看到了。她说,你这样把XXX公司的名字说给他们,很不好,没有商业道德。
我说,我这是变相扶持国营企业。
她还是摇头。于是,这成了又一个我们两个值得“深入探讨和广泛研究”的话题。
一番争论后,谁也摆不平谁。沈芳大踏步,冲过去拿包,我猜她准备离家出走以此抗议!于是追着
提醒她:“要走可以,不可以穿成这个样子!也不能超出以此地为圆心,半径大于30米的范围!活动
时间不得超出20分钟!”
沈芳白我一眼,“切,你想走你走,可以穿成这个样子出去,没有半径和时间限制,去吧!”
她从包里拿出钱夹,拿出一张纸币,这张纸币似乎没见过,却有些眼熟。仔细一看,却是英国才发
行的20元纸钞。我因为出国了,错过了发行,这时才第一次亲见到。
她转过那张钞票,指着后面一个侧脸的扎鞭子老头问我,“他是谁?”
我笑,“操,英文谁不认识啊,写着呢,Adam Smith,切,怎么这么个老土名儿啊,哎,都赶上我了
,那天我也上去……”
我还没贫完,沈芳打断我,“他是谁?”
我大笑,“得了,您还是说鸟语吧。”
沈芳跟着笑了一阵,挺严肃地跟我讲了有关Adam Smith,这个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18世纪苏格兰
哲学家。以及他的著作,现代经济学奠基典著——The Wealth of Nation——这部书的出版,带动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