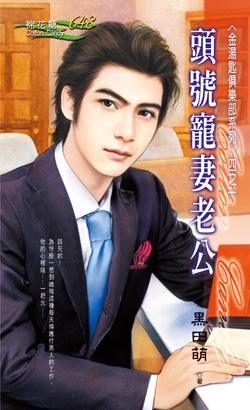木乃伊七号-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亲邢敢豢矗淼钠し舫屎稚钩ぷ挪簧倜@桌醯闷婀郑蛭谥谱髂灸艘烈话愣加昧で嗟然衔锢捶栏蚨苁窍缘煤诤诘摹5诙欤颐嵌允褰蠿光检查,结果更使我们惊奇万分。
“从手脚和胸壁看来,木乃伊六号像是个男孩或小个子女人呀,”雷利一边看X光片,一边咕哝道,“可是那颅骨,那牙齿嘛……”大家一看,只见那牙齿尖尖的,下颏和鼻骨向前突起,同狗的颅骨很相似。
“你们瞧,”他指着一串从脊柱延伸下来的小骨头,“一条尾巴!老天爷作证,布赖恩,木乃伊六号大概是一只狒狒!”
翌日清晨,我们同动物学家一起研究了这几张X光片。这具干尸果然是一只狒狒。当初古埃及人把它放在墓内,恐怕是个圈套,以引诱入墓者的注意,使他们放过了地层下的墓室。从木乃伊六号的腿骨和掌骨的X光影像看来,这是一只成年的雄狒狒。它双臂交叉合抱,两手平放胸前。这是典型的埃及风格。除了被撕开的部分以外,尸身保存得十分完好。我们再也没有把最后几层裹尸布打开。如今这具木乃伊陈列在医学院的解剖馆内,旁边展览着那几张X光片。
于是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那具身材较大的木乃伊身上了。我们分上、中、下三段拍摄了它的X光片,然后把片子凑到一起来观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人体。他脖子上套着一根细项链,右臂带着三个手镯,左臂带着两个。其他的珍宝一件都没有。既没有一般木乃伊都穿戴的大片胸甲,也没有什么指环。这使我们感到惊讶。
木乃伊的下颌还留着第三臼齿。根据这一点,再加上长骨的X射线影像,我们可以推断木乃伊七号在死时大概是四十五岁到五十岁左右。由于里层的亚麻布还裹的很厚,它的长度将近6英尺。其实它的骨骼比较小,测量起来,不过5英尺4英寸长。
从骨盆的外形看来,这是一具男人的骨骼。两腿之间有一个软组织阴影,大概是阴茎。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在开罗检查一具木乃伊时发现,阴茎和阴囊都已残缺。到底是防腐处理时作了阉割,还是在它生前受过宫刑,谁也说不出上来。
左侧大腿骨有一个螺旋型骨折,毫无愈合的迹象。左侧太阳穴上有一条细如发丝的裂纹骨折。此外还有两个肋骨也折断了。
把这几处骨折凑到一起来考虑,我们断定木乃伊七号当年不是死在战场,就是活活摔死的。几处骨折都发生在左边,更支持摔死的看法。他想必是左侧着地,摔裂了颅骨,同时摔断了左腿和左边的肋骨,造成了颅内出血或脏器出血,因而死于非命。
雷利十分高兴,因为从X光片看来,骨质结构保存得十分完整,比他预期的要好得多,而且胸腔和腹腔有些阴影,似乎体内还有一些内脏,只是不知它们保存得是否完好。我们过去在解剖木乃伊时往往发现胸腔和腹腔里填着不少沙子和乱七八糟的草药。
于是雷利决定尽早解开裹尸布,由另外三名大学毕业生担任助手。这件工作是在一天晚饭后进行的。那间附有看台的解剖室里一片肃静。尸体躺在一张狭长的解剖桌上。一排强光灯高悬在屋顶,把那里照得通明。雷利及其小心地割开裹尸布。结果如何,我们谁也无法预料,因而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有些木乃伊一旦接触外界空气,就会立刻崩解,成为一堆尘土;还有一些木乃伊只要轻轻用手一碰,就一层层地剥落下来。
教授是从尸体的下半截身子开始的。他手执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在木乃伊的两腿之间轻轻划了一下,一层层裹尸布便迎刃而开。他的动作十分缓慢:始终在腿缝中下刀。两条大腿间的亚麻布完全切断了。他由此向下,把裹缠两条小腿和双脚的亚麻布也切开了。教授先从两踝开始,小心地揭开亚麻布。有些地方的防腐胶粘的很紧;他只好一片片地把它撬开。这个步骤与其说是解开裹尸布;还不如说是去除那固定双足的“石膏”。一小时后,两只脚已经完全裸露出来了。
好奇怪呀!这两只脚保存之完好,竟超出我们的一切想象。趾甲十分完整。腿肚上还留着细毛。皮下的静脉依稀可辨。脚趾还可以随意屈伸,竟跟活人的肢体肌肤相似。这真是出乎意料。其余部分(臂、胸和头部)会怎样呢?真是难以预料了。
雷利轻轻地把刀子伸进各层裹尸布之间,沿着中线将布切开。首先跃入眼帘的是双臂。我们把横置胸前的双肘裸露出来,然后沿着前臂层层剥开,直至双腕。到了这一步,我们又转向腹部。一小束紫色的小花放在脐部。它的芬芳突然向我们袭来,人人都闻到了。
这束花只有人的拇指大小。雷利想把它拈起来,但他刚碰到花束,它就变成了粉末。
时间,似乎已经化为乌有之物了。人的躯壳居然能保存的如此完美,花卉居然能保持它们的馨香直到今天,而这皮囊里的生命却早在五千年左右以前就已终结。这一切使人不由得浮想联翩,思绪万千。
但雷利教授却无动于衷。他只是略为停了停手下的操作,碰了碰花束,就接着工作起来。手腕上的亚麻布被揭开了,几只手镯露了出来。在千年尘封的裹尸布中,突然现出碧绿和湛蓝的美色,把我们的眼睛都看花了。这样的手镯,我在开罗博物馆也曾见过,但上面的宝石哪里及得上我们眼前这样晶莹透亮,光华夺目。有三个手镯镂刻成荷赖斯神目的形状。另外两只金手镯,雕刻着精细的花纹,镶嵌着罕见的宝石。
两只手也保存得极其完美。指甲完整无缺,一道道皱纹和一根根静脉十分清晰。十个手指都能被弯成个“O”形,又能被随意扳直。看来,我们目前一点一点地打开的,恐怕是一个上上下下都完好无损的躯体。
可是现在还有一部分身体没有裸露出来。这时教授不禁犹豫了片刻。我们大家都明白他为什么犹豫。整个躯体保存得实在太好了,可是脑袋是个什么样呢?如果脸上已经朽烂,或者面目狰狞可怕,大家必将大失所望了。其实,对我们的研究来说,这脑袋并不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可是我们实在很难把这完好的身子看作是死尸啊。它的两只眼睛会不会还睁着呢?两片嘴唇会不会因死前的愤怒喊叫而张着呢?一切答案都包裹在这最后几层亚麻布之下。
脖子上的裹布解开了。我们在X光片上看到的项链露了出来。这是一根很细的金链,坠着好些蓝色宝石。雷利教授不去解项链,继续往上揭开下巴上的裹布。
快到嘴巴的地方,他的动作慢了下来。嘴唇露了出来。然后是鼻子、颧骨、眼睛。他一下揭去了最后几层亚麻布,整个脸部都露了出来。
下巴的轮廓很好看,显得坚强刚毅。双唇紧闭。鼻梁笔直而略宽,下端扩张成两个纤细的鼻孔。两只耳朵又长又大,似乎跟脑袋不大相称。头发不长,有波纹,微微缠结在一起。双眼闭合着,仿佛这人打算睡觉,而且果真睡着了。
“真是完美无缺呀!”教授气喘吁吁地说。我们默默地盯着这具躯体。古埃及人居然发明了这样杰出的尸体防腐法,至少在我们眼前这一例中,它硬是顶住了时间之牙的啃咬。
第二章
将近午夜时,我们已把所有的裹尸布全去掉了,还照了许多相片,并把这具木乃伊放进一个湿度自动调节的房间。雷利起先想接下去做尸体解剖,以研究内脏的状况,但他又改变了注意,打算先做一些实验以后再说。
他先用一台电子计算机扫描仪来进行研究。这种仪器有点儿像雷达,不过用的是X射线。操作起来,身体各部的截面图像,就将出现在彩色荧光屏上。木乃伊七号被放在一张检查桌上,慢慢地穿过一架很像巨大的炸面饼圈那样的扫描器。检查从胸部开始,逐渐移向腹部。
“至少心脏还在。”雷利咕哝到。可是腹部的截面图像进一步表明:肝、胰和胃也都处于正常的位置。
雷利又仔细看了看荧光屏上的彩色图像。“真奇怪啊,太奇怪了,”他低声道,“我还以为大部分内脏已经肯定拿走,以利于保存哩。原来什么都在呀。”
他聚精会神地坐在那里,一时忘掉了其余的一切。最后他往椅背上一靠。“取些深部组织标本吧,”他说道,“也许还有什么东西会生长哩。”
我知道,医学文献上曾提过有些哺乳动物的细胞在长期保存以后还有复活的可能,不过那是冷冻的组织呀。如今要从一具干尸身上取下组织细胞,希望它能生长,这不啻水中捞月呵。可是雷利这个人做事一向十分精细,认为这个实验可能有些意义。对他来说,否定的结果就像肯定的结果一样地有意义。“不要有成见。有些事情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你也得亲自动手来证实,不要随便推想。”他嘱咐我说。
那天下午,我在那埃及人身上取了几块皮肤的标本。我先用一把薄刃的刀子在左腿上轻轻刮下了一块组织,并把这层上皮细胞放进皮特里氏碟,碟内事先放好一种有利于细胞生长的营养胶。在雷利的指导下,我还取了一些深部组织的标本。在双侧小腿和大腿,在下腹部,我用一根纤细的探针插进皮下二三英寸处,弄下一点组织,放进盛有琼脂培养基的碟子,让这些组织同各种细菌接触。
一星期后,我们走进组织培养室去看结果。同我们一起去的是马卡姆教授,他是一位跛足老人,在上一年代中,他曾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阿诺德,这种事情我可从没有见过,”他的嗓音有些嘶哑,“我们在标本碟内放进各种各样的菌株,可是什么细菌都不生长,似乎被这个埃及人的细胞所抑制了。”
他拿起一只盛有橙色琼脂的碟子来。细菌长得很旺盛,但靠近组织标本的地方却一点不长。每个标本周围都有一圈明显的抑菌区。
“肯定是什么抗菌素的作用,”雷利议论道,“那具尸体保存得这样完好,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尸体的分解主要依靠两个因素。一个是死亡细胞释出的蛋白水解酶;一个是细菌的作用。如果保存那具埃及人尸体的防腐剂具有强烈的抗菌作用,它就可能防止细菌破坏那死亡的细胞。可是,任何一种抗菌素都不是百分之百地有效的。对一部分细菌有效的抗菌素,对其余的细菌就完全无效。何况除细菌外,还有酵菌和病毒也参与尸体的分解。由此看来,这肯定不是抗菌素,而是别的什么东西。
“用探针取的深部组织标本呢?”我问道。
马卡姆示意我们跟着他穿过实验室,来到后屋。这里放着一台巨型电子显微镜,有十几个旋钮与一个显示屏相连。屏幕旁是一个真空管,管壁很厚,管内放着标本。它的影像如果显示在屏幕上,足足可以放大10万倍。
马卡姆取了一块标本,然后操作起来。一个针尖大小的标本,突然变得很大,把整个屏幕都占满了。它的形状很像月球的表明,坑坑洼洼的。影像在移动着,现在显示出来的组织轮廓犹如一条很长的山脊,然后是一个山峰,越过峰顶,便是一道山谷。三个红细胞,像一个个巨大的盘子,两面都朝里凹陷,在屏幕上移了过去。在山谷底部有一个类似变形虫的白色结构,略呈椭圆型,伸着好几条又长又细的伪足。
“这是一个白细胞,”马卡姆道,“是机体防御系统的一部分。”他把影像调得更近一些,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