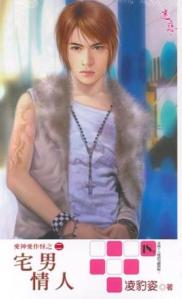园青坊老宅-第3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四斤儿不知道怎么回答好,说自己是被鬼拍的,没有人相信。说是被人拍的,半天也说不清。最后,只好把老宅里闹狐仙的事,说了一通。
听的人大部分都不相信。有人半真半假地说:“狐仙不是鬼。《聊斋》里的狐仙故事多迷人啦,你索性晚上去找找,也许能找个漂亮的狐仙做情人。”说完,大家哈哈大笑。
有一个人没笑,就是那个大学生小高。小高喜欢琢磨事,他发表了一个高见:“哪有鬼,鬼都是人造的,这些日子总听你说你们家那老宅里出怪事,是人装的鬼吧?!”
四斤儿一听,对呀,那天晚上自己分明看清楚是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人,而且那样真切地记得女人的裙裾扫过自己脸的感觉。绝不会是鬼,根本没有鬼!
当年自己在牢房里,和就要枪决的政治犯肩膀挨着肩膀睡了几个月,他们后来死了,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眼前出现过。记得执行枪决的头一天傍晚,看守给监仓里送来一碗红烧肉,大家立即围了上来。
看守大声喝斥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坐到自己的铺位上去,这是给你们吃的吗?想吃还早了点。”原来这碗肉是送给那两个政治犯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这是他们最后的晚餐。
监仓里其他的人明白了这碗肉的含意以后,都乖乖地回到自己的铺位上,背靠墙壁坐在那儿,眼睛望着天花板,不敢看那碗肉,空气中虽充满着肉香,却有了点杀人的味道。
四斤儿是第一个跑到肉碗前来的,他太想吃肉了。此时他想,吃了肉,去替那个政治犯死,他也干,反正死也痛痛快快地吃了顿肉。
那两个政治犯都是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个是老师,他们明白了,互相对视了一会儿,老师把大家吃饭的空碗,一字排开放在地铺上,端起那碗肉,往四斤儿的碗里先拨了两块,说:“孩子,你正在长身体,多吃两块,长高一点。”
四斤儿不知说什么好:“不不不,还是你们吃吧。”
老师说:“我们吃就浪费了,大家都吃点吧。”往每个人的碗里分了一块。
这是四斤儿一生中,吃得最没有味道的肉,却又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肉。
四斤儿夜里睡不着,感到和他挨着的老师也没睡着。想到老师明天就是死人了,四斤儿有点害怕。下半夜,他好像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朦胧中不知道旁边睡的是活人还是死人。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牢房的门突然打开了。看守站在门口大声地喊着两个政治犯的名字,叫他们出来。
两个政治犯知道自己最后的时间到了。他们慢慢地把衣服穿好,那位老师伸手摸了摸四斤儿的头,意思是告别了。
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但四斤儿总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四斤儿以为他们会出现在他的面前,哪怕是在梦里,但他们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在监仓里的那几个月,那位老师一直在教四斤儿学文化,没有课本,就教四斤儿背古诗,其中有一首是:
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
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
无论去与往,俱是梦中人。
四斤儿直到今天还记得这首诗,却不知道是谁写的。有一次他问成虎,成虎告诉他是唐朝大诗人王勃写的。他恍惚大悟似的“哦——”了一声,过了几天却又忘了。
这事对四斤儿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不再相信有鬼。包括他把母亲的骨灰盒放在家,也是基于这个信念。
没有鬼,那么是谁拍的我?小高的一句话开了四斤儿的窍,没有鬼,有鬼也是人装的,可人为什么要装鬼?
他想了一天也没想明白。下班的时候,看到市报上登了一条消息,几个农民把郊区的一个古墓盗了。这突然让他联想到:是不是老宅里藏着什么秘密,这装鬼的人就是在寻找这个秘密?!
不为三分利,谁会起五更。何况是个女人,深更半夜跑到小跨院里来干什么?四斤儿脑子中突然一亮:这是不是和老宅要拆有关?虽然四斤儿不了解齐府的历史,但他知道齐家曾经是显赫人家,还知道齐家后人有的在国外,有的在台湾。如果不是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包括四斤儿家在内的所有的穷人都搬不进这齐府大院。解放前夕,宅子的主人会不会把来不及拿走的财宝埋在院子里?
思路一打开,想像的空间就无限宽广了。四斤儿越想越觉得,那天晚上的人影像是谢庆芳。
谢庆芳是不是想寻找齐家埋在老宅里的财宝?
四斤儿受教育的年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看过听过太多的地主资本家偷偷埋浮财的故事。这时,他脑子中又一亮,那天夜里他被拍倒以后,第一个出现在他面前的就是谢庆芳,这难道是偶然?
是她,肯定是她。
四斤儿觉得自己的脑子被那一拍拍明白了。不行,不能被白拍,我要有所行动。
夜里,等七妹睡熟了,四斤儿悄悄地起了床。从曹老三说的故事中得知,武侠夜间为了更好地隐避自己都穿夜行服,四斤儿没有夜行服,但有黑衣服。他穿上黑衣,拿了一把铁扳手,轻手轻脚地朝三进那个小跨院摸去。
老宅被夜幕笼罩着,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家家都关门睡觉了,这段时间怪事太多,人们都将房门紧紧顶上,生怕下一个意外会落到自家头上。此时的老宅里,除了隐隐约约地传来人的呼噜声,一片静悄悄的。
夜里已经很有些凉意了,四斤儿打了一个寒噤,前后左右看看,没看到什么可疑的东西。他想,得找个地方把自己藏起来,左看看右看看,寻找藏身的地方。要守着跨院,最好的角度就是雨廊的尽头,如今那儿放着一张破旧的竹床,竹床上堆着一些柴草。
老宅里所有的空地方都满满地堆放着东西,一堆旧木头,几件破家具,几个旧麻袋,麻袋虽然鼓鼓的,但里面装的可能却是从旧枕头里换下来的陈年砻糠,或者是冬天烤火的木锯末,甚至是一捆旧稻草。这些东西一放可能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在物质不丰富的年代里,所有可能还有一点利用价值的东西,人们都舍不得扔,万一什么时候重新派上用场,就能节省一点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用这些东西告诉大家,这块地方是我们家的。这张旧竹床就是谢庆芳放的,表明这一块地方都是齐家的了。自打谢庆芳放了东西,再也没有别人往这儿放东西了。
四斤儿就钻进了旧竹床下面,视角很好,既可看到小跨院的门,又可以直视三进的厅堂。厅堂的西边就是谢庆芳家的房门,她要是夜里出来,这里一眼就可以看到。还可以看到厨房旁那个一人小巷,也就是说,从任何方向来的人,都要经过这个地方。
只是人躺在竹床下面很不舒服,竹床很矮,下面是石板地,石板湿漉漉的,湿气透过衣服贴近皮肤,凉透了。
一股有可能发现秘密的自信心,支撑着四斤儿咬牙忍受着。
果然,第一天晚上就发现了秘密。
大约守了一个多小时,四斤儿就听到一人巷那儿传来动静。有人背着一个大包袱走了过来。由于背上的包袱很大,包袱皮一路擦着一人巷的墙壁,动静很大。但这人又小心翼翼的,好像害怕惊动别人,走到竹床旁边停了下来。
四斤儿脑子里闪过第一个念头,小偷!
但这人是把包袱搁在竹床上面,压得竹床吱吱响。竹床下的四斤儿看到一双男人的脚,穿了一双白色的皮鞋,一只袜子口还破了。
这人站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怎么还不来?”然后就转身朝着竹床上的那堆柴草小便起来。也许是憋久了,尿了很长时间,热乎乎的尿液顺着柴草流到竹床上,然后又淋到四斤儿的脸上。
操!四斤儿在心里骂了一句,任由尿液从脸上流到脖子里。这时,又听到一个人的脚步声,从三进厅堂方向传来的。他悄悄地侧过脸,看到一双绣花拖鞋从三进厅堂的那道门跨过来了。
男人的声音:“你再不来,这尿都憋死我了。”
女人的声音:“操侬,没正经的。”原来是杜媛媛。
男人的声音:“这是我在一车旧西装中给你挑的最好的,一共二十套,全给你背来了。”
杜媛媛说:“最近也不好卖了,工商局查得严,查到就罚款,罚的挺多的。”
哦,原来是后院的赵大成帮助杜媛媛倒日本“大阪西服”。
“喏,给你,一条牡丹烟,托人从上海带来的。够你抽的了,抽完了告诉我。”
赵大成说:“我这么辛苦帮你带货,就一条烟谢我?”话里不怀好意。
杜媛媛冷冷地说:“大成,别把我当成你满街骗骗的小姑娘。”说完,就背起包袱转身走了。
赵大成也走了。四斤儿赶紧从竹床下爬出来,赵大成好像喝了不少啤酒,那尿里有一股啤酒的味道。
第二天晚上,四斤儿心焦地等待着七妹睡着。七妹无论有多少烦心的事,只要是头一沾枕头就睡着了,而且睡得沉。听到七妹轻轻的呼噜声后,四斤儿就悄悄下了床,穿上他那一身行头,又钻进了竹床下面。
这次,他看到谢庆芳夜里起来,在三进厅堂里站了好久,然后又回房间了。
四斤儿刚要松弛一下僵直的脖子,忽然听到一人小巷那边有动静,扭头一看,头皮一麻:真的有鬼!只见一个影子一点声响都没有地从后院那边飘过来,一飘一飘地飘进了共用厨房里。盘腿坐在厨房中央,嘴巴发出像婴儿一样的声音:“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妈的,吓我一跳!四斤儿在心里骂了一句,原来是张奶奶家的二傻子。这个二傻子一直半人半鬼的,清楚时,比正常人还神,糊涂时,连张奶奶都不认识。他深更半夜跑到厨房里来干什么?突然,四斤儿头皮又一麻,他想起七妹跟他说过,二傻子就是生在厨房里,他母亲生完他也是死在厨房里。这二傻子半夜里跑到厨房里喊妈妈干什么?她妈妈已经死了几十年了。
这时,张奶奶披着衣服从后院过来了,她拉着二傻子的手,把他牵回家了。
一会儿,四斤儿又看见一个人溜进了厨房,还是张奶奶。她悄悄地将别人家灶台上的菜油、酱油、盐等一家一点地倒进自家的油瓶盐罐里。张奶奶好像不是第一次干这事了,每家油瓶都只倒一点点,为的是不让别人第二天发现。临了,还顺手拿了人家的几块引火点煤炉的柴火。
第三天,一夜无事。
第四天出事了。出事的不是别人,还是四斤儿本人。
那天夜里他在竹床下藏了好久,耳朵竖起来听着附近的动静,但什么也没有听到。谢庆芳家那个老式的座钟敲了一点以后,起风了,躺在竹床下的四斤儿已经深深地感到地上的寒气袭人。虽然已经把那件冬天穿的工作服棉袄套在身上,仍然感到一阵比一阵凉。
四斤儿坚持不住了,想早点“收工”。正准备从竹床下爬出来时,忽然听到有人从前门那儿走来,走到谢庆芳家门口,敲了敲门,是齐医生。四斤儿平常见到齐社娟都喊齐医生。
齐社娟是从医院下夜班回来,顺便看看她二哥齐社鼎的病情。好像是谢庆芳开的门,看完二哥,齐社娟没有马上回到楼上,姑嫂二人站在三进的厅堂里,嘀嘀咕咕地说了好久。齐医生是一个平时说话很少的人,这深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