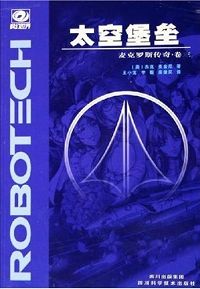太空烽火-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需要你证实我的所见。““你搞得就像是我们在等待飞碟似的。”他的脖子扭了扭,看见黑暗中贝斯洛眼镜片上闪烁的光泽。“哎呀,这里可真够热的,不行,我得离开,要不,非得变成驼背不可。”
“住口!你不能不说话吗?如果外面有人,非得让你吓跑了不可。”
“此刻人人都躺在床上睡觉,只有我们在这里犯傻。你干吗不安一个探测仪或者是感应开关以及别的什么东西呢?如果有人去厨房,它就给你报警,你还可以用你的微型全能东芝照相机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拍下来。”
“呀呵,我怕拍到你和库拉克趁我睡觉的功夫偷偷地溜到厨房,从冰箱里往外拿食品的镜头。”
“这件事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托勒问,“也许那个人只是喜欢隐秘的生活。
可那又有什么呢?看来我还算是幸运。”
“不自然,这就是理由。还有,我很好奇——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充分的理由。”
“是这样,可我并不好奇,我真不明白我怎么会接受你这可笑的建议c如果我还跟你于下去才真是傻到家呢。”托勒的身子动了动,头碰到了架子上。“哦!可怕——我得出去了。”
说完,他不顾一切地爬了出去。‘你也出来吗?“贝斯洛看了看表,说:“时间到了,说不定那人就要来了。”他用双手和膝盖撑着爬了出来,“如果那人今天晚上来的话,现在该到了。”
托勒向自己的舱室走去,贝斯洛在后面紧紧地跟随着他。走到那个人住的地方,他们都停下来,将耳朵贴在门上。托勒失望地向他看了一眼,贝斯洛耸了耸肩,拖着疲惫的步子向自己的房间走去。“晚安,托勒。”
托勒站在自己舱室的门口,门仍然打开着。听见贝斯洛的门关上,他才蹑手蹑脚地回到了那个人的舱室门口,听着里面的动静。可是他却什么也没有听到,于是将耳朵贴在门上。正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门却出乎意料地打开了,首先映人他眼帘的是一双亮亮的黑眼睛,镶嵌在一张精美的闪着青铜色光泽的脸上,脸的周围是瀑布般油亮的黑发。此刻,这张脸冷冷地看着他,他的第一个想法便是不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脸。
“杨丹·塔拉滋小姐!”他终于镇定下来,“要不是你的头发,我还真认不出你来了。”
“托勒先生,”她的话中有几分俏皮,“这是你的一个坏习惯吧——我指的是在别人的门外偷听。”
“不是的,”托勒从她那里接受到的最明白的信息是她希望他呆在这里。“我只是——是的,是好奇c我们都觉得你——我的意思是说——里面的那个人很奇怪。
都好几天了,我们一次也没有看见过你,我们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
“你更应该关心你自己。你都看见了,我很好,如果你能够体谅我的话。”她从他的身边走了过去,托勒为她闪开了路。
“请原谅,如果我打扰了你。”他说,他的心里似乎有很多话想说,但更多的还是遗憾。她转过身来,面对着他,用目光与他交流着,可她的脸上却毫无表情。
托勒感到有点奇怪,好像自己正在浅水的泥沼中挣扎一样。他想躲开她的目光,可她的眼睛却在向他诉说着什么,他唯一可做的就是迎接她的目光。“对不起。”他嘟哝了一句,算是打破了他们之间短暂的沉默。
她一句话也没有说便离开了他,沿着过道向厨房走去。托勒目送着她修长的身体渐渐远去,觉得自己脸热心跳,连手心里都满是汗水了。
五个星期来,他一直没有再看见她。她在舱室里干些什么,她是怎样躲开其他人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都在困扰着他,使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耗费心机。她为什么要如此蛰居?她为什么要避开所有的人?当然,不会是因为她害怕他们——在一条满是男人的船上,惟一的女人会惧怕男人?简直是无稽之谈。不,不会的,即使她有一千条理由,惧怕也绝对不是她远离他们的理由。凭着男人的直觉,托勒觉得杨丹·塔拉滋小姐来这里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作为男人的配偶而出现的。
他并没有把那天晚上的奇遇告诉贝斯洛,他甚至觉得杨丹也是不愿意让他提及此事的。不过他又觉得携带如此重大的秘密简直是一件十分愚蠢的事情,尤其是在贝斯洛喋喋不休地劝他重新参与侦破行动的时候。他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他知道她是不会再被他撞上了。毫无疑问,他想,她是再也不会被人撞上了。尽管她只有一个人,但那是她自己的选择。
可为什么呢?为什么是她?又为什么是以这种方式?托勒一有时间,便沉人到这些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中。他试图在他的心中把她的面貌勾勒出来,但他却失败了。每当他努力回忆她长得什么样子的时候,他的大脑便一片空白,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描绘出她到底长得什么样子,留存在脑海中的只是一张美丽的人类面孔——他只朦朦胧陇地觉得她长的是一张亚洲人面孔,也许是玻利维亚人的,没有什么突出的特征,只是一个很美的轮廓而已。这既让他困惑,也让他感到沮丧,他怎么就想不起她长得是什么样子来了呢?他在心中安慰自己,毕竟,他们只见过两次面,而且是一闪而过。可是,他却能够毫不费力地想起与他匆匆相遇的其他人的面孔:他从麻醉剂中清醒后照料他的护士、电梯驾驶员。六轮车的司机——所有这些人都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仿佛就站在他的面前似的。
可是,杨丹……留给他的全部印象就是光洁、蜂蜜色的皮肤,乌黑的眼睛或者是头发,苗条、匀称的身材以及走起路来飘一般的感觉。就是这些。
试图回忆起她的面貌成为一件让托勒着迷的事。只要那些徒劳无益的对那个幽灵一般的女人的各种画面的连接的企图不至于折磨他的大脑,他就努力回忆那天夜里他和她相遇时说过的每一句话以及他们的每一个细节,并试图破解隐藏在其中的微言大义。但这样的努力同样也是徒劳无功的。尽管他付出了无数的艰辛和长时间的冥思苦想,但仍然没有找出话语背后的意思并对他们之间的相遇做出新的解释。
看来只是一次纯粹偶然的相遇,他想,可他又有些不甘心。难道真是这样吗?托勒有理由确信在这个神秘的杨丹·塔拉滋小姐备受关注的地方,发生偶然事件的比率是少而又少的。
在他的心中与塔拉滋小姐占有同样分量也同样神秘的便是蠕虫洞之旅了。他是在飞行开始后的第二个星期得到贝斯洛的书并开始读起来的。刚开始的时候,他读的并不用心。这本书是从第七章开始的——贝斯洛并没有把它全部印出来,而且还有许多令人感到费解的天体物理学术语。显然,贝尔汉森的《星际旅行理论》是一部学术著作。托勒觉得即使在世界范围内,读过这本书并且真正理解贝尔汉森观点的人也许还超不过一百个。
不过贝斯洛竟然是他们中的一个倒着实令他吃惊不小。
不过除了吃饭、睡觉以及和矮个子贝斯洛玩以外,他总得干点什么,于是,他把读书看成一种宗教般的职责——他在那些由整页的长句子组成的冗长的段落间跋涉着。有时候,一些词所代表的意义不但要从上下文中猜测,而且要到第二段或者第三段中去琢磨,才能领悟一二。
贝尔汉森不是威廉·莎士比亚,但他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这本书给托勒的一个主要的感受,就是这个人洞悉了整个世界的万事万物中所业已存在而未被人们所意识到的全部可能性和可行性。在这本并不容易读懂的书中,他态度鲜明地向人阐述这么一个观点——至少另一个作者的职业慧眼是这么看的,那就是新鲜的观点和概念产生于作者的艰深的思索和创造力,而这一切的诞生是值得作者为他们付出代价的。他可能从来没有当过诗人,但他也绝不是愚莽的屠夫。
由于对作者日渐增加的敬佩,托勒在这本书中步履艰难地跋涉,使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赤脚的士兵走在崎岖不平的田间路上,尽管他并不理解指挥员的命令,却愿意为他冲锋陷阵。从这本书中,他也了解到了有关蠕虫洞的问题——那是和其他的问题混杂在一起提到的。
从书中所得到的一切给了托勒以无法言说的喜悦和震惊。
托勒把贝尔汉森的书放在枕边,两腿交叉,靠在沙发上,打开他在自己的卫生间发现的那个装润肤液的小盒子,将里面那粘稠的绿色液体抹到自己的皮肤上。尽管这种润肤液擦在身体上并不合适,但想到此刻即使离那个和这里距离最近的矿泉水疗养地都已经几千万公里了,这种润肤液便成为了他目前的最佳选择。
于是,他边把这种粘稠的液体擦到自己的脸、胸膛以及胳膊上,边读着那本书。
那段与蠕虫洞有关的时间变异的文字他读了四五遍了,不知为什么,那段文字总是令他感到烦躁不安,头皮有一种被刺痛般的感觉。他干脆放下书本,努力回忆起他从前曾经有过的类似的感觉。回忆让他吃了一惊:杨丹!几乎与此同时,他抬起头来,看见她如镶嵌般地站在了他的门口,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打开了。他跳起来,张大嘴巴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一个人该对一个幽灵说些什么呢?“托勒先生,”她的口气与其说是问候,倒不如说是在陈述一件事实,“我可以进来吗?”
托勒呆呆地看了她几秒钟,才意识到自己应该以主人的身份回答她的问题。
“哦,可以!请进,我没想到会有人来,我——你愿意坐坐吗?”他的目光在屋子里四处搜寻着,搬来书桌边的那张泡沫椅。
“不,谢谢。我坐的时间已经太长,我想我们全都如此。”
“是的,”他打量着她,心想这回可得把她的面容原原本本地记在心上。
“托勒先生,我不想打扰你读书,我只耽误你一小会儿。”她的眼睛在他的舱室里扫了一遍。六个星期来,托勒已经把这里弄成了罪犯收容所的休息室。
她站在那里,托勒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房间是多么凌乱不堪。“我正准备收拾一下的。”
“没关系。我有话给你说。”
他等待着。她满脸好奇,打量着他。她觉得在自己说出下面的话之前他应该作出相应的反应。
“好!”他终于开口了。
“你有感应吗,托勒先生?这个问题并不复杂,“感应”一词他从前也听说过,知道它的含义,可是他却无法明白她用这个词做何解释,其中又包含了什么意义。
“感应?”
“遥控智能接收器。是的,你很熟悉——”
“哦,是的!是的,我知道。可我没想到你会问起这个。”他做了个笨拙的手势,才意识到自己的手中仍然举着那把泡沫椅子。他把椅子放了下来,说:“我没有感应,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也没有这方面的爱好。你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
她仍然用热情、鼓励的目光打量着他,终于她说话了:“有的人具有天然的接受能力,虽然他们对之一无所知,托勒先生,你就是其中的一员。”她终于把话说完了,他分不清她的口气像是挑战还是像命令。
“看来我明白了,不是吗?”他笑了,试图冲淡这个年轻女子脸上的过度严肃,但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是在退出去的时候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哦,你别走,”他赶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