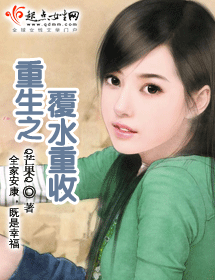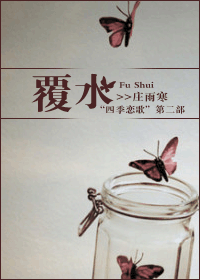覆水可收-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奴婢在王爷府里姿色平平。若走了一个还算标致的侍女,府里再有了事,就会来更标致的侍女。且奴婢专心伺候王爷,并无他想……”
“府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家务事?”不待我说完,莫将军不耐烦地打断,直直地问我。
我立刻缄口不言,这才意识到以自己的身份是不该答话的。可话已说出去了,想必是有些得罪他了。
“莫将军不用和府里的侍女计较吧?”嗅出气氛不对,他的眸里闪出危险的光芒,看着莫将军:“战事要紧,我们先进去谈战事。”
莫将军因我被尹暮轩暗抬一杠,众多誓死保卫疆土的将士自然对我印象不佳,一个个斜睨着我,轻蔑地走入了帐篷。
长途跋涉,只为了看这么多蔑视的神色?这又是何苦?
不只是迷茫,还有些委屈,来看他,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冬日的严寒褪去不少,眼看着嫩绿的草芽扎破土壤,远远望去新绿无涯,走到近前却仍是冻土枯色,“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意境在此处被诠释的分外传神。
今日一早起来,收拾妥当后,我忙进帐篷“服侍”尹暮轩梳洗。
“这是织锦袖衣。”放下衣服,我正准备去拿盔甲,却被他制止了。
“今日不用穿戴这些。”说罢,他轻快着上墨青穗缎外褂,牵着我向外行去。
“这是去哪?”怕人看见,急急甩掉他的手,侧首问道。
“你不是要学骑马么?今日教你。”似是理所当然地回答,全然不顾我有多惊讶。
“可若是有兵来犯……我不是罪孽深重了?”那些将领对我的敌意,我如此迟钝尚能感受的到,他不会全然无知的。
“有敕王爷在,还用我担心?”
“别赌气啊。你若是带我出去,此时又正好敌方发兵,归来后,我不被那帮将军踩碎揉烂才怪。”想起他们看我凶狠的眼神,我至今仍有些战栗。
“你怕他们?”似是有些意外地打量着我,浅笑道:“你敢忤逆皇上,私来边疆,还与敕王爷同车而行,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怕呢!”
这话倒似别有一番用意,我虽领悟,却也不好点破,只得装傻:“呵,那咱们晚上去吧?”
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冬春交际,边塞风光不如画,却另有风趣。潮湿的沙尘再飘散不起,沉沉地伏在大地,绵延千里,仿佛蓄势待发的猛兽,一但伸爪则置人世于水深火热,不胜不休。
共着大漠落日,昏黄的光晕像雾气笼罩着沉寂的战场,我有些怯懦地甜甜笑着:“你真要教我骑术?这方面我有些笨拙,不好教的。”
“这匹禄螭骢是玉骢种的,习性温顺,只要你不伤它,它是不会伤你的。”仿若未闻我的胆怯,他牵过一匹青白相间的马,隔着些距离,再加上黄昏天欲晚,那毛色看上去竟有些像兰色。如此静雅的颜色,我心里生出一股喜欢,可是还是免不了的有些残存的害怕。
“绝影,你可不要耍脾气啊。”小心抚摩着它柔软的皮毛,我嘱咐道。
“绝影?”感叹于我的起名水平,他设问道。我知道我取的不好,所以“借鉴”人家取的马名了啊。
“我的马叫惊帆。”看着我的惊讶,他挑眉道:“是不是很巧?”
“呵……呵……是好巧啊。”我有些尴尬的回答着,猛然想起绝影与惊帆同侍一家,渊源颇深,同为名马却各有所长。
“握紧细鞭,不要挥。抓住缰绳,不要拉。”在我以一个极度难看的姿势爬上马后,尹暮轩坐在他的马上,在一旁悠闲地指导我。
“可是这样它不走。”我完全按他说的做,马却一点也不给面子,呆在原地无所事事地吃着根本不存在的草。根本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嘛!
“用腿蹭马肚子。”
我依言去做,马却毫无反应。
“再蹭。”看马无动于衷,他继续教导。
不知这马在留恋什么,我“再蹭”“再蹭”了近十次,它都一点反应也没有,真是自以为是的不像话。我心里一急,猛的一踢马肚,大喝一声:“快跑。不跑吃了你”这马倒真是欺软怕硬,我话还未说完,它就通了人性似的狂奔起来。
周围的景物疾速闪过,明晰的昏黄此刻已全然模糊,天地都只剩下一种色彩,心里也只存在一种感觉。
晕眩。强烈的晕眩。颠簸的马极复节奏感的跳跃,速度却依然不慢,不愧是好马,即使要把马背上的人扔下来,也让被扔的人心甘情愿。
哪怕被扔下来哪怕摔的满身是泥,骨断筋折,我也骑不下去了。巨大的颠簸使我坐不稳不说,腹部的不适更为强烈,五脏六腑都搅和到了一块。猛的抽着马鞭,希望剧烈的疼痛感能让它停下,它却拼了命似的以更快速度奔驰。
“不要抽了!快住手!”没了控制的手还在猛抽着,耳畔已依稀传来尹暮轩的声音,从飘渺到清晰,伴着马蹄阵阵,似乎越来越近。猛的一拉,我坐在了墨黑的惊帆背上。
“你很勇敢。初次习马者,除了不想活的,很少有敢踹马的。”虽是赞扬,但他说的咬牙切齿,里面的意味我再清楚不过。
“你不用讽刺我,我知道错了。”错本就在我,也没什么好辩驳的,只能由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没有讽刺,是……真心……话。”说的有些吃力,咬紧牙根的挣扎让我体会到他此言非虚,可是他说话的声音为什么……
“你受伤了!还流血?”这是怎么回事?绝影即使要踹,也踹不到这个高度啊。
“拜你的皮鞭所赐,刚才拉你的时候又牵动旧伤。”声音已微弱了不少,我急的不知如何是好。
“回去,我们马上回去,你再坚持一会。”似是通灵的马也许感受到了情况的紧急,向着营帐狂奔而去。
坐在马上,心里不是悔恨或是焦急几个简单的词语所能形容的,只觉得一团火焰在心里熊熊燃烧,烧的精疲力竭,烧的心慌意乱。
帐篷里,火烛滋啦作响,燃烧的火苗不复往日旺盛。人言油尽灯枯,生怕出现不详预兆的我坐在蜡烛旁,专心地剪着烛花。
“你这个混蛋!若是我们元帅出了什么闪失,你就不用活了!”贺漠竟不顾礼仪尊卑,第一个冲进帐来,待太医诊治之时对着我破口大骂。
“若是他有事,我生不如死。”这是真心话,两国交战,我却牵扯主帅再度受伤。若他有不慎,我无颜以尹殷人自居。
“少拿这些谎话来装可怜!我们元帅一时不慎中了你的计,你以为我们还会吃你这套?”
“我……”
“贺漠,不要为难她。”勉强睁眼看了我们一眼,暮轩嘱咐道。
“元帅!伤在左胸,本就命悬旦夕,好不容易病情有了专机,却被她引得伤口再度开裂,你还有心袒护她!”贺漠满是不敢相信的痛心,仿佛我就是那祸国殃民的败类一般。
他闭上眼不再作答,苍白的脸色滚下细密的汗珠,却洗不去痛苦的神色。半晌才又开口:“不怪她,是我不好,逾越了……不属于自己的,就不该去奢望……”
贺漠一脸愕然,我也无法解释,刚被马惊,惊魂未定间又遇上了这样的事,脑里乱的已毫无思考能力,只能呆呆坐着,时不时剪掉烛花,以求渐渐平复自己的心跳。
“郭太医,王爷如何了?”一看太医起身,贺漠连赶上去询问,听言我也连忙起身,急切地凝视着他。
千万,不要有事。
“冲脉阳虚,气弱无力。新伤尚浅,旧伤未愈,虽可保性命无虞,但近期内不适征战。”大约是军营中的人都习惯于打断太医们对于脉象的分析,郭太医略谈脉象后便直接转入伤病的程度,言简意赅,极富经验。
“太医请这边来。”贺漠侧身伸手示意,请太医开方取药,向帐篷外走去,经过我时还不忘狠狠瞪了一眼。
“又拖累你了。”内疚地坐在床边,我拿出白绡帕轻轻为他拭去额上细细的一层汗。
“反正也连累不了一辈子。”似是自嘲一笑,他偏过头去,我只得收回了手。气氛一时有些尴尬,如此情景,留在这里也无益,不如让他一个人静一静。
“既然王爷不愿见到如儿,那如儿先告退了。”微一福身,我缓步走出。
“蓝玉……”
“恩?”
“我要你记住一点,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相信你。”
心里猛的一凉,那个人,也曾信誓旦旦地说他相信我,可他却那样绝情地对待姐姐。世间的许多事,不是相信一词可以阻挡的。
他决不会平白无故说出这样的话,应该是预见了什么事,可究竟是什么事,他是不会愿意告诉我的。即使如此,他的一句相信,还是让我寒冷的心又温暖了起来。冬日的风,划过身边,也飘逸着春日里的芬芳。春若来,冬寒又能残存几日?
心情明朗,做事也轻松起来。近几日,在郭太医的照料下,暮轩好得很快。只是在他病重时,尹疏霭却不来探视,实在有些匪夷所思。纵使不关心暮轩的病,他也该做做样子啊,这样不闻不问岂不落人话柄。
疑惑了不少日子,暮轩已能下床活动,未免士兵无首,军心涣散,他迫不及待地投入了军务中。不得不说,他实在是一位优秀的将领,尹殷朝能有这样的将军镇守边关,一定不会让外侵占得半点便宜。
“皇弟,多日不见,憔悴不少啊。”军帐里,自从尹疏霭进来后就气氛紧张,他却仿佛毫无所觉。
“略受小伤,并无大碍。”微一颔首,尹暮轩淡笑回答道。
“若无大碍,脸色怎么有些苍白呢?”仿若抓住蛛丝马迹,尹疏霭闻言立刻佯装关心地驳道。
“若有大碍,皇兄怎么不来看我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尹暮轩面无改色地反问。
空气为之一窒,安静的空间里涌动着不平静的波涛。
“呵,是皇兄疏忽了。这几日外敌进犯,皇兄上阵驱敌,却忽略了皇弟的感受,真是抱歉。”在他语里,尹暮轩俨然变成了一个受了伤后急待安慰的可怜兮兮的孩子。
“是么?那皇兄真是辛苦了,一阵劳顿,想必已精疲力竭,喝点百合毛尖安安神。”警厉的语气骤然温和,仿佛在和远道而来的兄长谈心般,尹暮轩吩咐我去砌茶。这才发现,满篷将领都干候着,我竟然一杯茶都没送来。
慌忙退下,行至帐外,才听到里面隐约飘出几句:“皇兄此去十分辛劳,杀敌如何?”
“两万零三十四名,将领一名。”略一停顿,尹疏霭若无其事地回答。
“那我军损失如何?”丝毫没有被血淋淋的数字影响,尹暮轩声音依旧温和地问着。
“四万零五十二名,将领牺牲一名。”这次回答的声音似乎是贺漠的,明显显露出一些不快和蔑视的意味。
四万五十二名?
几天前还活生生的面孔,会喜会怒的年轻生命,就这样化为云烟!
战争二字,又岂是一个残酷能够形容的!
意识到不能再听下去,我忙去茶蓬领茶。错任将领,竟会枉送这么多无辜生命,这是我没有料想到的。原先我以为我害的尹暮轩不能征战沙场,只是伤了他一个人,现在看来,我扼杀的也许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