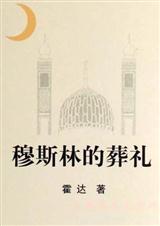宁小林的官司-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果真是,梁拉柱脸上露出了羞愧之色,他接受了一万元的赔偿额,并答应在三天内交付。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呀!只剩下原告方了,我把贾尤玲叫进来。贾尤玲听了我的解释,也痛快地说,行,剩下的我们自己承担。当我问起宁德贝的父母时,贾尤玲仍吞吞吐吐不肯说。我说你不说,我也知道他爸妈是谁。贾尤玲瞪大眼睛问,他爸妈是谁?我说,宁晓林贾晓庆。贾尤玲呆了似的,盯着我的眼睛,好久没说话。我说,按照规定,起诉书上、调解书上,都应写上宁德贝爸妈的名字,他们是宁德贝的监护人,这是程序问题。贾尤玲哦哦地点着头,说那我写上那我写上。我把起诉书交给她,她把他们的名字写了上去。我让她补一份儿特别授权委托书,她显出积极的态度,极快地说,明儿上午我就给你送来。
镇中赔偿的三千元,也答应在三天内交来。诉讼费按承担责任的比例负担。调解书制作好后,我没让他们领走,因为卷宗里还缺少原告的委托书,万一中间有变故,事情就麻烦了。我向他们说明了情况,最后强调,明天贾尤玲将特别授权委托书交来,后天梁拉柱和镇中交款时,将调解书领走。
成功让人喜悦。当事人走后,我跑到王庭长办公室,把这件喜事告诉给他。王庭长听后,很平静地笑了笑。
宁德贝的事解决了,宁晓林执行案子所涉及的费用也会随之解决。我问,梁拉柱和镇中交了赔偿款,是不是先把宁晓林欠的诉讼费、执行费、罚款从这里扣除?温玉山也在那里,温玉山激动地说,当然要给他扣下,剩下的钱也不能让他们领走,等宁晓林把那起案子执行了再说。王庭长摇了摇头,作出与温玉山意见相反的决定。他说,让他们领走,梁拉柱和镇中交了款,就让他们领走。我看到温玉山一脸惊讶,我也为他的这一决定捏了把汗,如果让他们把款领走,如果宁晓林一直不予执行,可就抓了瞎!王庭长不再谈这个问题,把话题一转,问,周少安的离婚案,安排什么时间开庭?温玉山说,九号上午开庭。王庭长听了,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九号,还有五天时间。
贾尤玲按时将特别授权委托书交给了我。又一天上午九点,镇中把赔偿款和诉讼费交到了我手里。吕校长没有来,派了一个女出纳。女出纳代领了调解书后,把一个很简单的调解书看了好几遍。贾尤玲也早早来了,脸上现出一副很腼腆很不好意思的样子,后来又变得一脸的期盼,因为梁拉柱到中午还没来。贾尤玲等到中午,见我们下班去吃饭,她便犹豫着走出了法庭大门。吃饭回来,我发现贾尤玲还在法庭大门口徘徊。
下午,梁拉柱姗姗来迟。他满头大汗,手里提着一个尼龙小兜,兜里装着一把票子,兜提带在右手腕上缠着。梁拉柱怕我责怪他,见了面就说,信用站没钱,又跑到皇寺,刚取出来。
贾尤玲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梁拉柱从右手腕上解下小兜,并不急着掏钱,说,我把调解书领了吧!我让他和贾尤玲在送达证上签了名,把调解书交给他俩,梁拉柱才慢腾腾地往外掏钱。我点钱时,发现梁拉柱和贾尤玲都盯着票子发楞,脸上的表情却很复杂。
梁拉柱恋恋不舍地走了。贾尤玲坐在我对面的长椅上,望着桌上的票子,小心翼翼地问,我把钱领走吧?我把镇中交来的赔偿款也放到桌上,让她核对一下数目。她悬着的一颗心,落下来似的,脸上堆起了笑,并欢快地应一声,然后很笨拙地捏起一沓票子点了起来,一万多元的纸币,足足点了一刻钟。她给我打了一张收条,连一声谢都没来及说,急匆匆地笑着走了,仿佛走晚了,我要变卦似的。
周少安的离婚案如期开庭了。
周少安只一个人来了。他见到我,目光婆娑迷离,大概是因我去镇中那晚,从他身边走过时,他认出了我。他不愧是一位国家干部,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周少安媳妇是和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相跟来的,看长相陪她来的女人,像是她的妹妹。开庭前,书记员核对当事人到庭情况时,我才得知周少安媳妇叫黄梅茜。
黄梅茜胖胖的身材,圆圆的脸,脸上显得异常平静。她长得并不难看,只是嘴里一颗假牙有些煞眼。穿得有着农村人的朴素。
王庭长只道了开场白,后边大都由主办人温玉山主持。
周少安提出离婚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感情破裂,已无法继续生活下去,要求离婚,儿子周前进随他生活,女儿周彦倩随对方生活,家庭财产共同分割。黄梅茜则不同意离婚,认为双方感情没有破裂。
周少安和黄梅茜同在一所中学毕业,同届不同班。上高二时,学校举办校庆二十周年文艺联欢会,排练节目时,他俩相识了。当时黄梅茜长得苗条。她演唱《红灯记》里李铁梅听罢奶奶讲红灯的唱段,一下唱得出了名。周少安与人合作,在台上说了一段天津快板,演完就完了,不像黄梅茜那样引起轰动。联欢会过后,黄梅茜从宿舍到教室的路上,不断有人指着她铁梅铁梅地叫,叫得周少安心里发痒。周少安开始追求黄梅茜。高中毕业时,周少安考上了中专,上了地区财贸学校,黄梅茜回到村里,但两个人仍你来我往。周少安中专毕业后,分到了工商所工作。黄梅茜通过亲戚,到一个养路站当了一名养路工。一年后,他们结了婚,很快有了孩子,黄梅茜生下儿子后,辞去养路工,在老家专心带孩子,把儿子带到五岁,又生下一个女儿。黄梅茜在老家一边带孩子一边种地,孩子一天天长大,黄梅茜又替周少安尽孝,把婆婆公公养老送终。
黄梅茜说,我替他尽孝的时候,他咋不说感情破裂?他当了副所长,喜新厌旧了,跟一个下岗工人贾晓庆相好,这是思想问题,道德问题,希望周少安能悔过自新。黄梅茜像一个领导批评部下一样,大人不计小人过,弄得周少安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煞是难堪。按照程序,当事人陈述完最后意见后,进入调解阶段,两个人达不成一致意见,温玉山宣布休庭。
合议庭人员和书记员,都凑到王庭长办公室,对该案进行合议。这是近两年来养成的习惯,百分之八十的案子,当庭宣判。周少安的离婚案比较简单,属于这类案子。
我们刚坐稳,周少安后脚就跟了进来。他弯着腰,一脸惶恐,说,王庭长、王法官、温法官,你们让我离婚吧!有一句话我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现在我和黄梅茜在一块儿,家伙儿愣是硬不起来,在庭上我没好意思说,你说这样我们在一块儿还有啥意思?温玉山问,你生理没毛病吧?周少安晃晃脑袋说,没有,绝对没毛病。王庭长说,周副所长,你说的情况我们知道了,我们合议合议再对你说。周少安走了出去,出去时,没忘了把门带上。
温玉山先发了言,他说,从开庭的情况看,被告不同意离婚,原告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个家庭,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所以我主张驳回原告的离婚请求,诉讼费由原告负担。我认为,还不能把这个家庭拆开,原告的思想意识存有问题,需要纠正。王庭长说,一年庭里受理两百多起案子,离婚案几乎占一半,这种现象应引起社会重视,更应引起我们法官的重视,为了社会的安定,达不到离婚条件的,决不可调离或判离,这起离婚案,构不成离婚要件,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五分钟后,继续开庭,王庭长宣读了判决结果。
宣布闭庭后,周少安在笔录上签了字,一句话也没说,低着头走了。黄梅茜还和原先一样平静,倒是她妹妹兴奋地望着我们,眼里全是感激的目光。
过了一个星期,那天下午,我在办公室整理几本卷宗,臭蛋跑来了。我问他有什么事,臭蛋说,我去小良舍村了,打这里过,顺便拐进来看看法官大人干啥哩!我笑笑没吭声,心里却嘀咕他闲着没事干。
哎!法庭可给宁晓林帮了大忙啦!臭蛋故意把话说得一惊一炸的。
我说,帮什么大忙啦?不就是他儿子的事吗?那是我们应该做的。
臭蛋神神秘秘地说,他儿子的事是其一,主要是法庭没让周少安离婚,成全了宁晓林。你没听说?贾晓庆和周少安闹翻了,贾晓庆说后悔跟了周少安那么多年,犯了一个大错。从前家里的事贾晓庆从不挂在心里,现在也关心起家了,这几天宁晓林也有了笑脸。哎!宁晓林和贾晓庆离过婚,可后来宁晓林往红星小学调工作时,复婚是其中的一个条件,有人在中间调和,他俩才又复了婚,我刚听说的。这几年,贾晓庆一直和周少安在一块儿不清楚,可宁晓林心眼死,偏偏就喜欢贾晓庆,这下好啦,法庭给他清去了障碍。
我故意逗他,说,你就哄我吧!跟真的似的。
臭蛋把脸一绷,认真地说,真的,我不哄你,哄你是小狗!
又过了几天。上午,一起赡养纠纷案开庭,十点半就开完了。闭庭后,我第一个走出审判庭。我见宁晓林在审判庭门外站着,不由得警惕起来。宁晓林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那个掂着菜刀气急败坏的样子,那个闭着双眼装病装死的无赖,一时间不能从我脑海里抹去。可我弄不明白,为什么后来王庭长没再执行他,一直搁着好像忘了似的。对待这样拿着自己的头,往墙上撞的主,不能太心软了。
我后退了两步,到自己认为的安全距离。我说,宁晓林,你干什么来啦?我故意提高声音,意在震慑一下他,并且给王庭长提个醒,好让他们在思想上有个准备。王庭长若无其事地走了过来,到宁晓林身边停下脚步,问,有事吗?宁晓林笑着说,我已经按判决书执行完啦!
执行完啦?我瞪大了眼睛,猛一下转不过弯来。你把房基朝后挪了?宁晓林说,已经按判决书上的尺寸挪了,一会儿你们可以跟我去现场检查一下,我来是告诉你们一声,再把诉讼费、执行费、罚款交了。
王庭长自始至终都很平静。宁晓林,你把应该交的款项交到金平那里。之后扭过头吩咐我,收了钱开完票,我们去现场。
到现在,我仍满腹疑虑,宁晓林是不是在耍花招?为了防备他耍赖,我让宁晓林到王庭长办公室等我。我的顾虑是多余的,我拿来单据后,宁晓林如数交了款。
我们乘车来到现场,见宁晓林的房基的确已经朝南挪了。把申执人王东晨也找来,一测量,正好与王东晨的房子相距一米——同判决的结果一致。我作了记录,王东晨和宁晓林在笔录上签了字。一切办妥,我们打道回府。临上车前,宁晓林交给王庭长一份材料。半路上,王庭长把材料交给我看,并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宁晓林会这样做的。
原来那份材料,是宁晓林写的悔过书。看过之后,我的疑问从这份整整五页的悔过书上,找到了答案。
悔过书上有几句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与邻居的官司,家庭不和,当时我痛苦至极,真的到了不想活的地步,经过儿子的官司和周少安离婚案,我才从内心里真正相信,法庭是公正的,是法庭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