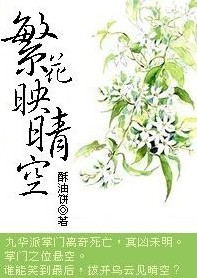繁花落定-第7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直在旁服侍的桃夭忙去找顿珠,白玛却不在,不知到哪里去了。问桃夭里,说是出去走走。
我想想甚是愧疚。我这一向不大出去走动,连带白玛这个豪爽如男子般的人物也天天陪我窝在房中,料也闷得厉害了。当下也不去理会,叫了桃夭帮我梳发。
一时顿珠来了,我叫桃夭出去帮我弄几样茶点,把她支开,自己梳着长长的发问顿珠:“苏勖那里,联系得怎样?”
顿珠道:“苏公子说,纥干承基那里现在看着的眼睛比当日的东方公子还多,明着去探望十分不方便。”
我轻笑道:“明着探望不方便,暗中探望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顿珠微笑道:“小姐聪明。苏公子说了,晚上狱卒交替班时应该有机会偷梁换柱,把小姐塞进去。只是要委屈小姐换上狱卒的服色了!”
我怔了怔,玉篦轻转,已将头发挽起,用根长长的银簪束了一个男子的发髻。
那铜镜之中,便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清俊男子了,只是太过清瘦,亦太过苍白了。
顿珠在身后轻轻叹息,似有种说不出的惋惜。
我回头看向顿珠,顿珠却不说什么,只是疾速低下了头,不让我发现他眼底的难过和同情。
我怔了怔,同情?我应该被同情么?
我站起了身,雪白的袍子曳在地上,流淌着婉转优美的线条,无风而动。
“放心,顿珠,我以后,会过得很开心的。”我慢慢说,不知是对顿珠,还是对我自己。
顿珠弯腰向我行了一礼,低声道:“顿珠相信。顿珠这就去准备晚上的事。”
顿珠回身出了屋子,身影在门口顿了一顿,一句如梦呓般的声音飘散在空中,几不可闻:“我们的小姐,生来便该是被人宠爱,被人照顾的啊!……这么着寻不着归宿,太苦了……”
我笑了一笑,轻淡得如阳光照耀下晃动的蛛丝,微微的一抹,不知道是坚韧,还是柔弱。
戌时,刑部大牢左近的一条小弄里,我穿着狱卒服色,从轿中走了下来。
苏勖正带了几个穿着同样服色的狱卒等侯在那里,略有焦躁之色,见我来了,忙迎上来,开口第一句话便道:“书儿,你若此时后悔,还来得及。”
我镇静笑道:“怎么了?你不是已经安排妥当了?”
苏勖皱眉道:“是,我本来已经安排好了。可今儿牢里气氛有些异常,我怀疑太子知道真情后很震惊,开始在牢中安插高手,多半这一两日便会采取行动了。”
我也是一阵紧张,但我紧握住拳头,挺直自己的肩背,不让别人看到我的颤抖和惊惧,竭力平淡道:“不必怕。我会小心的。”
顿珠、白玛等却更紧张,白玛拉住我道:“小姐,不然我代小姐进去一次好了,一定把小姐的心意转告给纥干公子,让他自求出路!”
我忆及当日在落雁楼最后见到纥干承基时他绝望伤痛的面容,凄楚一笑,道:“你以为他会听信你的话?”
苏勖皱眉道:“书儿,他也未必会听信你的话。也怪我,趁了你拖住他时擒了他,他一直以为你和我在联手用计对付他。”
白玛更是着急,道:“不然,苏公子你让我也换上狱卒服色一起去吧。小姐一人犯险,我……我实在不放心!”
顿珠等纷纷上前,叫道:“我也去!”“我也去!”
苏勖喝道:“胡闹,夹带一个人进去就不容易了,这么多人去,只怕立刻会给了看破了!”
我深吸一口气,道:“你们都不用去。如果真有事,便是你们全去了,又能在几百上千的官兵之中救出我来么奇Qisuu書网?我一个人进去,给发现的机率还少些呢!”
顿珠、贡布、仁次等面面相觑,而白玛已经泪光盈然。
第四十二章 探监
我抬起头,天际的星星颗颗明亮,镶在无边的黑绒上,竟有种慑人心魄的愧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花香,不知是牡丹,还是兰花,幽淡缥缈,似远似近,飘忽在这暗夜的冷风中。
风很冷,可我的心不能冷。》
如果我的心都冷了,谁又去温暖狱中那颗绝望冰冷的心?
苏勖向侯在一旁的狱卒们招了招手,等他们近前来,才道:“你们知道该怎么做,是不是?”
为首那位看来是牢头,有些谄媚笑道:“苏大人放心,我们一定好好把这姑娘带进去,再好好带出来。”
苏勖点了点头,我便杂着这些狱卒之中,一步步迈向靠近纥干承基的地方。
而顿珠等,依旧伫立在弄堂之中,凝成了座座雕塑。
快到大牢门口时,牢头便和同行的狱卒大声说笑着,看来极是自在模样,守牢兵卒笑道:“张大哥?换班来了?”
张牢头大刺刺应了一声,道:“兄弟们辛苦啦,怎么还不走?你们接班的也该来了吧!”
守牢兵卒“嗨”了一声,道:“林侍郎有了命令下来,说齐王之事才出了,叫我们安份些,一定要等下班人来全了才许走哩!”
张牢头摇了摇头,道:“那就没办法了,咱们想图个安稳混饭吃,只得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啦!”
他一厢说着,一厢已带了一众狱卒大摇大摆走了进去,丝毫不露破绽。
一时到了一间休息房中,地上堆了好些木枷,墙壁上亦挂着许多铁链,隐见有斑驳污渍,淡淡的血腥味和潮湿的霉臭味直熏鼻孔,让我阵阵恶心。
几名狱卒正或躺或坐在几张榻上,见人来了,都跳了起来,道:“你们可来了!却来得晚了,该罚,该罚!”
张牢头哈哈一笑,掷出一锭银子,道:“今儿可巧了,我和众位兄弟赌了一把,进帐不少呢!这锭银子,就算是我给大家的彩头啦!刚从彩云坊过来,那里的姑娘还有不少闲着呢,你们不去喝几口花酒!”
那几名狱卒立刻鼓噪起来,叫道:“快走,快走,这回可要玩个够,不玩白不玩呢!”
几人一哄出了门,只最后走的那位一瞥眼看到我,“咦”了一声,道:“这位小哥有点面生哦。”
张牢头笑道:“就你会管闲事!小赵家里有事,和这才来的弟兄换的班,使不得么?”
那狱卒连连道:“使得,使得!”
外面又有人在催快走,那狱卒答应着,飞快跑了出去。
我松了口气,低低问那张牢头道:“现在我可以去见纥干承基了吧。”
张牢头迟疑一下,唤了另一人来附耳说了几句,那人便道:“姑娘,我们这便去吧。”
随了那领路的狱卒,我们一路往大牢深处而去。
此时入夜已深,便虽是隔几步便有哨岗,却大多垂着头在打瞌睡。而张牢头所带的这队狱卒显然是巡牢的官兵,因此我们在昏黄的壁上油灯摇曳中一路走过,竟不曾引起过半点注意。
大牢的最深处,曾经关过东方清遥的那间牢房,又被这狱卒打开了。纥干承基和东方清遥竟然住到了一间牢房,这种巧合,实在有点可怕,似清晰地提醒着我,是我,用纥干承基的被困,换来了东方清遥的被释。
那狱卒低声道:“姑娘,你且进去。我们两人一齐出巡的,现在我一人离去,并不合适,所以我会在东面那间空牢房里暂避,等你们说完话,我再来带你一起走。”
我忙低声道了谢,狱卒向我手里塞了两样东西,将我轻轻推和牢房,小心下了锁。
隐约的油灯光芒被关到了门外,我的身子,已全然被黑暗吞噬,一时竟有片刻的茫然和恐惧。
“你来做什么?”黑暗中,有人冷冷喝道。
我从明处来,看不到纥干承基,他却看得到我,居然还一眼认出了我。
我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心中反而安妥了些,捏了捏手中之物,才觉出那人给我的,原来是火折子和一截蜡烛。
我不敢乱走,小心吹燃火折子,将蜡烛点着,慢慢举高。
纥干承基盘坐在墙角的干草上,正冷冷盯着我,漆黑如玉的眸子里看不见任何内容。他的衣衫,依旧是那日在落雁楼穿过的黑袍,质地虽好,但却和他的躯体一般受尽折磨,破成一片一片,凌乱地被血渍胶粘着,狼狈地贴在身上;只有他端正有力盘坐的姿势,悄无声息地昭示着:眼前的这人,虽已遍体鳞伤,落拓不堪,依旧是个倔强不屈的剑客。
可这不屈的剑客,肢体却很僵硬,分明保持某种警戒的姿势。
那是针对我的吗?
我心一酸,又要掉下泪来,慢慢走近他。
纥干承基喝道:“站住!”
我顿了一顿,然后继续往前走着,一直走到他的面前,才将蜡烛放到地上,倚着墙靠在他身畔坐下。
纥干承基有些愤怒地一直盯着我,但终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沉默地又将头扭向前方,不来看我。
离他近了,那血腥味更浓了,这个少年,这些日子以来,到底受过多少折磨,流了多少血?
我颤抖的手慢慢伸过去,欲去抚摸那曾如钢铁一般将我牢牢箍在手中的臂膀。
手指才要触到他的衣物,只闻咣当一声,纥干承基带着镣铐的手猛地挥来,拂开我的手。他本是绝顶高手,这一拂虽不曾用上多大力道,可余力依旧把我推到一边,扑倒在地上。
我伏于冰冷潮湿的地面,丝丝凉意从每处与地面接触的肌肤传到身上,冰得一阵颤抖,禁不住心头愧疚伤痛,哽咽着轻轻道:“对不起。”
“我不想再见到你,容书儿。”纥干承基终于回应我的话了,声音空空落落:“我很快就会死,不会再吵你烦你,你也放过我吧!”
那声“放过”,却说得好生疲倦好生伤感,那种被伤透心的悲怆,叫我忍不住委屈,委屈地握住他的手,含泪道:“纥干承基,你真的以为,我那日是联手苏勖有意害你的么?”
“你弄痛我了!”纥干承基盯着被我握住的手,吸着冷气,咬牙道。
我一低头,才见我双手握住的,正是纥干承基当日给苏勖刺过一剑的那只手,时隔那么久,那伤口居然还在流血,向外翻卷着新鲜的肌肉。
我屏住了呼吸,道:“他们折磨你,不断割裂你的旧伤?”
纥干承基低声道:“哦,他们倒已经半个月没提审我了,没人弄伤我。”
“那……那这个伤口……”
“我自己弄伤的。每次伤快结疤时,我就设法把它撕裂,让自己痛。”纥干承基的声音冰凉平淡:“这种痛可以让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曾经那么喜欢的女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只要想到这个,我心里就不会那么痛了。”
“我是一个坏女人!”我哽咽道,从怀里抽出条帕子来,小心地替他裹上伤口。我早就发觉了,心上的疼痛,远要比身上的疼痛更让人难以忍受。
纥干承基默默看我裹好,才道:“你是不是打算一直在这里呆下去,陪着我?如果你呆会走了,我还会把这伤口撕得更大。”这话明显有些嘲讽挑衅之意了。
我微微一滞。一直在这里陪他?直到他死了,我呢?也陪着他去死?
我忽然有种解脱的轻松,不去理会他嘲弄的眼神,安然笑了一笑,道:“好主意!”
纥干承基挑着眉,冷冷道:“你喜欢我把因你而起的伤口越撕越大,恨不得我把自己的手腕给剁了,是不是?”
我微笑道:“没有,我想,我一直留在这里陪你,一直到你死了,我也死了,也是种解脱。便是还有再欠你的,我到黄泉之下做你的妻子去。”
我悄悄伏下身子,伏在纥干承基盘坐的膝上,心里居然有丝欢喜之意。
而纥干承基的背去僵直起来。他几乎是在痛苦地低吼道:“容书儿,你究竟要把我耍到怎样的程度?”
“承基!”我安静地抱住他,温柔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