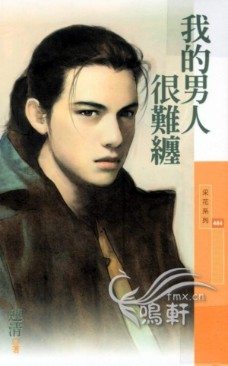我的夫君谭画眉-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成个什么样子,你在这里怎么没个体统,大喊大叫的?”何雁慈的娘埋怨何雁慈忘了从前学的礼法,愤然推开何雁慈,要自己走。
“娘~~”何雁慈看她娘脚步踉跄,心里有些急,也没管她娘的训斥,又喊道:“夫君,夫君,你帮我扶娘一下啊。”
“别喊了。”何雁慈的娘看草屋里没人出来,就在何雁慈手臂上拍了下:“我能行,他可能出去打鱼了吧。幸亏不在家,要是听到你这么大声喊他,他不责怪你才是。”
“娘,不会的。”何雁慈笑笑,眼底都是明媚。她想起谭渊告诉过自己,该喊的时候就要喊,该大声说话也要大声说话,高兴的话,即使是女子也可以大步流星地走,也可以像男子一般跑跳……
“雁慈,他们是谁啊?”何雁慈正想着,她娘拽了拽她的衣袖,指了指几个站在草屋前的人。那几个人都是家丁打扮,但衣料上好,腰间还带着刀。他们本来是对着湖眺望什么,可听到何雁慈跟她娘的脚步声就都转过身来,其中一个年长的给旁边的人使了眼色,其中两个便过来把何雁慈跟她娘架了过去。
第十一章
“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雁慈,他们是谁?”何雁慈的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看到那些来路不明人物腰中的刀,脚便开始发软。
“娘,女儿也没见过他们。”何雁慈本来也很怕这样的人,可自从在湖上见过谭渊跟雪公子切磋武艺,便觉得眼前的人倒也没什么了。
“你们……”家丁中年长的人刚要发话,却看到草屋的帘子一挑,从里面出来一个面色阴沉的公子。那公子相貌英俊,但脸却似结了千年的寒冰,看不见一丝笑容。他见这几个人架了何雁慈跟她娘,便低声斥责道:“不得无礼。”
“是,大少爷。”那年长家丁慌忙命人放开何雁慈跟她娘。
“你就是何雁慈?”那公子盯着何雁慈看了半天,才问了这么一句。
“请问公子尊姓大名,为何在我夫君不在时屈尊寒舍?”何雁慈没回答这公子的话,反而反问了一句,话间带了强入民宅的讽刺。吓得她娘拉了下女儿的袖子,心说怎么这么不知道轻重,这人目光带着不满和鄙视,万一对两人不利可如何是好。
“看来是了。那这位就是你娘。你和他没圆房对吧?”那公子也没有回答何雁慈的问题,反而说了这么一句,吓得何雁慈捂住了嘴巴无言以对。
“公子在说什么啊?”何雁慈的娘看女儿吓了一跳,心里也觉得事情不对。
“你到底是谁?”何雁慈觉得自己的手脚有些凉,她用眼睛四处看着,心里有不好的预感。
“你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那公子上前一步,一把拽过了何雁慈的手给何雁慈把脉。
“你要干什么?怎么可以随意碰别人的手?”何雁慈用力挣脱,在那公子放手的一瞬间跌倒在地,她咬牙迅速爬起来,跑到水缸旁边,捡起那砍柴刀,却没有向自己的手腕砍去,而是拿起刀,跑到公子身边,要砍那公子的手腕。
“哼,这也是他教你的?你们果然没有圆房。”那公子根本不把何雁慈的举动放在眼里,抬手夺过那刀,顺势丢到草屋的土坯墙上,让那刀死死嵌进墙中。
“我们圆房与否干你屁……干你什么事?”何雁慈涨红了脸,想学谭渊的样子跟那公子吼叫,但那粗鲁的字眼还是让她羞愧难当,说了一个字便说不下去。她瞅瞅墙上的刀,想起谭渊跟自己说过女子不可以那么软弱,纵使被别人不怀好意碰了手也应该是奋起反抗,而不是自惭形秽地归罪于自己。
“很简单的道理。你没和他圆房就不算是他的娘子。”那公子冷笑着。
“我怎么不算他的娘子,我……”何雁慈分辨着,忽然又想到了什么,她上前一步瞪着那公子问:“你和我夫君是什么关系。”
“哼。”公子并不回答,只是鼻孔出气。
“你……”何雁慈瞧着那公子的态度,心里竟然莫名慌张起来,她想到自己回来后,还没有见到谭渊,而刚才一心只讨厌面前公子的种种无礼。
那公子看着何雁慈慌张地四处寻觅,便冷冷开口道:“你不用找他了,他不会回来了。既然你们没有圆房,说明他也并不喜欢你。我打听过了,你是被你爹和大娘以收聘礼的名义嫁出来的。当然,就和把你卖掉差不多,看你这模样也是一般,想必他花了银子娶你是因为你可怜吧。所以这些银子你收着,好好跟你娘一起过日子,而且日后也能再嫁找个好婆家。”说罢一摆手,让手下那年长的家丁拿了一包银子过来,重重摔在何雁慈脚下。
何雁慈的娘被公子的一席话弄得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拉着何雁慈的手,瞧了瞧何雁慈打扮,又回想这些天何雁慈跟谭渊之间的那种气氛,虽然像是新婚,可两人之间的羞涩种种,却好像是还没挑开那层窗户纸的迹象。
“雁慈,你和他……”何雁慈的娘不知道问什么好,她咬着嘴唇,心说这算怎么一回事,这可如何是好啊?
“娘,您先别问了。”何雁慈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解释,她推开面前阻挡的家丁,房前屋后地找寻谭渊的身影,可是她见到的只是冷冰冰的四壁。她又冲出屋子,到船上看,可船上也只有尚未被日头晒干的渔网。
没有谭渊,哪里也没有谭渊了。何雁慈倒退几步,觉得不可思议。她跑到小草房那里,看到水缸里面都是新鲜的鱼,再回到灶旁瞧瞧,里面的点了一半的木柴也还有余温。
“你把我夫君带到哪里去了?”何雁慈从灶里把手抽出,在裙子上拍打着,眼睛狠狠瞪向那公子,全然没有了平日的温柔模样。
“雁慈……”何雁慈的娘吓得赶紧拽住何雁慈,不让她往公子那边走,生怕那公子一声令下,带刀的那些家丁就把自己母女两人结果了。
“你说啊!”何雁慈把自己的娘护在身后,但质问的声音却更大:“我和我娘回来的时候差不多是该吃饭了。水缸里面有鱼,灶里的火点了一半。这表示我的夫君要做饭给我和娘吃,所以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消失。而平地钻出来的你却不表明任何身份,就让我离开我的夫君……是你带走我的夫君对吧?他在哪里?”
“雁慈~”何雁慈的娘看那公子眯起了眼睛,慌忙又挡在女儿面前,想要祈求那公子原谅何雁慈的无礼。
“娘,你不要对他示弱。夫君说我在他面前示弱是好事,可在外人面前示弱会给他丢面子。”何雁慈紧紧拽着她的娘,瞪着那英俊但冷酷的公子。
“没想到众人口中贤惠羞涩的何家大小姐竟然也有如此泼辣的一面,不过倒还聪明。我也明白为何他可怜你了。”那公子捡起地上的银两,走过来轻轻放在灶台上,对何雁慈的娘说道:“这位大娘,你也听到你的女儿承认没有圆房,既然如此,这桩亲事便不算数。这里是一千两银子,足够你们母女买自己的房屋田地,好好过下半生。当然,在这村野之地,你女儿再嫁也是容易的。”
“这位公子。你……”何雁慈的娘听说这包里是一千两银子,眼睛立刻有些圆,她瞧了瞧那些银子,又看了看自己的女儿,却发现何雁慈对这包银子漠不关心,反而是上前一步,仰头狠狠瞪着那公子追问谭渊究竟去了何处。
“你无需知道我是谁,也无需知道他去了何处。你留下这银两,和你娘好生过活吧。”那公子看到何雁慈苦苦追问,板着的脸倒也有了些表情。他把何雁慈推回给他的银两抛到了屋里,然后挥手,带着那几个家丁便去草屋后面牵自己的马。
何雁慈虽然没有打听到谭渊的消息,但看那公子的态度,也明白谭渊的失踪和这公子脱不了干系,便追着公子的脚步,让那公子说出谭渊的下落。那公子也不理会,让两个家丁架住何雁慈,自己上马先带人走了。待那公子走远,那两个家丁也上马飞驰而去。
何雁慈的娘被这变故搞得糊涂,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只好跑到屋子里把那包着银子的包裹拿出来,解开后对着还亮的天色查看成色。而何雁慈则是追着那公子一行的马跑了很久,直到那公子的身影消失在路上,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往回走。何雁慈一步一挪,眉头紧缩走回了草屋,却看到自己的娘没有四处找谭渊,脸上也是一片茫然,没有丝毫忧伤的表情,反而好像还带了些喜色。
为什么,难道那银子比自己的夫君还要重要吗?何雁慈靠着灶台,无力地坐到地上,刚才质问那公子的勇气和力量一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莫名的伤悲。她从灶里拿出一根燃到一半便熄灭的木柴,想着谭渊,不知道谭渊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被人带走的,是不是会像上次在湖里看到的,跟人经过生死般的恶战,才从自己的身边消失。
“夫君……你到底在哪里?”何雁慈抱住那块木柴,想着谭渊是在给自己做饭的时候被人带走的,更是悲从中来,“夫君,你让雁慈怎么办?雁慈追不上那些人,雁慈究竟怎么才能找到你?那些人到底是谁,你去了哪里啊?夫君……”
“雁慈……”何雁慈的娘听到女儿哭泣,才醒悟过来,她慌忙把手中的银子放下,心疼地搂住何雁慈,给她抹眼泪。
“娘,我的夫君不见了。”何雁慈看到娘一脸忧心地瞅着自己,心里就像开了个闸门一样,所有的难过倾泄而出。她抱住她娘,把头靠在她娘的肩膀上哭泣着,让泪水肆无忌惮地打湿了她娘的衣襟。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她只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谭渊不见了。
夫君不见了,自己甚至都没有看过他的模样,他便不见了。何雁慈想起谭渊的种种,醒悟过来谭渊知道自己的一切,可自己却对谭渊一无所知。
“雁慈,要不……咱们报官吧。”何雁慈的娘见女儿哭得如此凄惨,心下也不忍,她把装银子的包裹系好,递给何雁慈道:“咱们去报官,跟县太爷说你的夫君被人绑走了。”
“娘,不行。”何雁慈摇摇头,擦着眼泪道:“我们无凭无据,怎么能说夫君肯定就是被那些人带走的?何况如果夫君真被人绑走,也应该是朝我们要钱才是,怎么会给我们钱。何况,夫君跟我说过,咱们这边这县太爷为官不清廉,怕是把银子提上给他当证物,他倒还会诬陷咱们娘俩为了钱财谋害夫君……所以,娘,不能报官啊。”
“那、那怎么办才好?”何雁慈的娘没想到女儿能说出这么多道理,可仔细想想,好像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娘,夫君说过,遇事不能慌张,要仔细考虑,再作定夺。娘,我先煮饭给你吃,吃完饭,我先清点一下家中的物事,再到村里打听一下,看村里和夫君熟识的人知道什么。”何雁慈说罢揉了揉自己哭得通红的鼻子,觉得自己的嘴唇也哭肿了,眼睛也变成了桃子,可这样又如何,于事无补,夫君也不会回来,与其在这里哭泣,倒不如照顾好娘,然后四处打听一下,看能不能寻到些线索。
“雁慈,你……你比在家的时候更有个小姐架势了。唉,嫁人就是这点好,知道柴米油盐的难处,从姑娘家磨练成了别人的娘,这才能懂得些事情。”何雁慈的娘点点头,觉得只有这样了。
何雁慈做了决定,便没再犹豫,把柴火重新点燃,炖了鱼、煮好饭,和娘一起吃过,然后就开始整理草屋内外的每一处,看看有没有和从前不同的地方。她手里还拿了平日记帐的簿子和笔,把自己觉得奇怪的地方都记录下来。
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唯一古怪的地方是放水缸的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