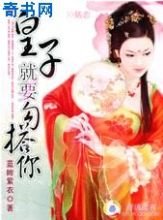这辈子就想谈恋爱-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扇子姐姐只好说:他工作忙。
严振宇倒杯茶给扇子姐,劝君婶说:“妈!君苇得挣钱哪!没钱哪儿娶的上媳妇?您不想他早点成家?”
君婶着急的道:“想呀!人家扇子一直等着呢。”
扇子姐正愣神,一听扯到自己身上,有点着慌。
“谁动我烟碟了?”严振宇夹着烟卷,望着五斗橱,突然冷冷的问。
没人答茬。严振宇有点起火,审人的口气问:“林天雯!”
我啃着指甲,从容道:“我没动!把手按在圣经上发誓!”悄悄扯下扇子姐姐的袖子,她还看我,我努嘴挤眼,她才明白过来,忙把手边的烟碟儿,递向严振宇。
严振宇盯着扇子姐,不接,只冷冷说:“以后记着,哪拿的,还放哪儿去。”扇子姐姐嘴唇都白了,我都看出她心里很不是滋味。
君婶笑道:“振宇就是死心眼!你别理他。以后他还得叫你声嫂子呢。”
严振宇对君婶的口气,和缓多了“妈。晚饭咱吃嘛?”
君婶无可不可的说:“咱有嘛是嘛呗。”想起什么来:“对了,扇子。你爱吃嘛?让他给你做。”
扇子姐姐仓皇掠着严振宇,急忙表态,说一定要回家吃饭。君婶极力挽留,最后变成软磨硬泡。严振宇一直冷眼看着,终于发话:“房老师,一快吃吧。给咱妈个面子。”扇子姐慌乱的看着他,又看看君婶,终于委屈的点点头。
严振宇问:“你吃什么?”
“什么都行。”扇子姐姐怯生生的说。
严振宇转身,喝令:“林天雯。打瓶儿酒。”我追着他问小费给多少。他说踢你两脚!
扇子姐紧赶几步,问:“有什么叫我帮忙的吗?”
严振宇回身,瞟她一眼,道:“有。”
扇子姐很积极,忙问:“做什么?”
“杀鸡。”
扇子姐一愣,恐慌的瞟了下厨房,却步了。
我买酒回来,作为小费,就跟严振宇这儿蹭顿饭。饭桌上,快吃完了。扇子姐姐忽然问:“怎么还不熟?”
君婶问:“什么不熟?”
“鸡呀?”她看着严振宇,不紧不慢的问:“刚才你杀的鸡呢?”
君婶纳闷的问:“振宇,你什么时候买鸡了?老贵的!”
问的严振宇脸都红了,捧着碗,咬着嘴唇,翻眼看天花板。
扇子姐道:“去厨房看看,会不会忘了。”好心提醒的样子。
严振宇干脆筷子一摔,盯着扇子姐姐。
扇子姐姐,不理会他,向窗外瞟了瞟,自言自语说:“也许,那只鸡会飞呢。也说不准。”
我憋住,不笑出声来,心想,扇子姐也够厉害,原来表面上的胆小怯阵,只是麻痹敌人的假象。
吃完饭,扇子姐姐立刻就要走,一刻也等不及。君婶留不住,只好让严振宇送她出门,眼巴巴的望着扇子走了,还不死心的喊了句:“扇子!你可常来呀!”过道没有灯,屋门一关,仅有的亮也没了,我走在最前边,扇子姐扶着我肩膀,还有点跌跌撞撞。
好不容易摸到楼梯,扇子姐却站在暗沉沉的楼梯上,底气不足的说:“那烟碟……我拿走好吗?”
严振宇跟在她身后说:“那是君苇……”
扇子姐姐温和的截断他:“我送给他的。”
等了片刻严振宇没有回音,扇子姐和我都仰头看着他,虽然什么也看不清。他做了个深呼吸问:“我岳母知道吗?”
“不知道。”扇子说。
“你随便。”他侧身靠着栏杆,让路。
扇子姐低头寻思了会儿,说:“我这样回去,伯母会疑心的。等以后再找个合适的时机吧。”转身,手搭在我肩上,我带她到楼下。严振宇并没送她,是我跟扇子姐到胡同口。照例互道:拜拜,她走了,我去玩。
(本文章首发起点文学,希望喜欢我的网友帮我多投票)
(十一)车 祸
(十一)车祸
(本文章首发起点文学,希望喜欢我的网友帮我多投票)
走在这条街上,时不时会有清淡的花香飘来,如果你象狗一样,提鼻子仔细闻,又嗅不见了。那就是海棠花香。海棠花都开了。天暖和了。
放学路上,有时碰上严振宇买菜回来。就跳到在他自行车后架上,让他驮我回家。有一回我央求说:“振宇哥哥,你教我骑车吧,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他说:行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晚饭吃完,等严振宇收拾好屋子,安顿好君婶,我们就推上他的车,段城他妈截住严振宇,热心的问:“唉呦!这不是振宇吗?找着单位了吗?”严振宇摇摇头。
段城他妈问:“没上街道问问?”严振宇笑了笑说:“问了。没有单位要人。”
“哦!”她眼珠滴溜溜乱转,忽然一笑,:“这社会,得有熟人,找路子,要不谁理你去。”刺探的问:“你没烦烦小房?她们家,我一眼就看出不一般来!”紧盯着严振宇看。
振宇道:“人家认识我是谁?”
段城他妈,眉飞色舞的说:“唉?你是女婿,她是儿媳妇儿。一家子,还有嘛外道的!”
振宇提着口气,又艰难的咽回去,斜着眼看着她问:“是吗?一家子?那我老婆呢?她男人呢?”段城他妈被问得一呆。
严振宇撂下她就走了。我推着车,追着他一路冲到马路上。车把与我齐胸高,我不禁看着严振宇发呆。以前也摸过车,学单腿滑,(双手扶把,别着腿,一脚踏脚蹬子,一脚滑步)倒的挺快,滑的挺远,可始终也没骑上去过。他看我滑了几圈,点点头。
把我抱到车座上,腿还够的着脚蹬子,就是有点费劲。他命令:蹬!使劲蹬!我回头看他说:不敢。
他寒着脸喝道:别看我!看前边!
我回过脸看着前边,心里没底。严振宇直指远方的天,“天雯,冲!”他声音不高,可底气十足!我深吸口气,撅屁股离座,弓起背,紧攥车把,狠命的蹬起车来,开始车把稳不住,左右打晃,我觉得我控制不了了,横了心的要摔倒,没料到,严振宇硬生生扳住后架,车竟然的没倒。
严振宇在我耳后,指着前方说:“天雯,你往前看,那是什么?”
“马路。”
“马路尽头呢?”
“楼房。”
“楼房后边?”
“天空。”
“你什么也别想,照直往前冲!你就会飞上天。有我给你扶着!”我笑了,因为闻见他嘴里的酒气。
“我哥就这么说,他说这世上没有死胡同,因为路走到尽头,还有天空。”他凝视着前方的天,提到他那个已死哥哥,传说中的严振寰,他有点动情。
他扳正我的脸,端正我的方向,手轻轻托起我的下颌,他把车把正过来,指着前方,说:“别慌。手放松,把扶稳,想你就要飞起来了。有我扶着你,你不会摔倒。”他的语气,反常的温和,就好象他能轻易的主宰一切,让人不得不信他无所不能。
那时候的街上,没有这么多车来车往,在树下往来的人,头发上,衣服上,沾了花瓣,这整条街,两边都种着海棠树。飘来一阵清香,风一过,吹落的海棠,花飞漫天,真的很美。
我手虚拢着车把,向前稍微探着身,脚下发力,车蹬起来了!我心头一喜,猛蹬几下,骑快点,风钻进我的衣服里,我好象被风托着,落花漫卷,迷了眼,打着脸,痒簌簌的,我好想笑!有点找到飞的感觉。
我回头瞟了眼,想告诉严振宇:我原来真的能飞!可竟不见人,心就慌了,车把也我不听使,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我害怕,又不知怎么停车,终于跟另一辆自行车撞上了,人仰马翻!
我一个鲤鱼打挺,蹦起来,红着眼,先找严振宇!靠!那个被撞的好不识相,揪住我的后衣领儿,大声吼:“别走!撞了人连……”
懒得听他废话,回手攥住他的胳膊,腰上一叫劲,一个背口袋,把他摔在地上。他叫唤一声,蜷着身,抱着头,要死要活。可怎么看他有点眼熟?
我蹲下,说:“死不了人!他妈忍着点行吗!”
“算你狠!”说着,那个人扭过脸,瞪着我咬牙切齿。
我傻愣着,喊道:“贱男!!!!?”春游以后,在学校偶尔碰见,可没再过话。因为大多在办公室,我罚站挨批,他则给老师帮忙,登分儿、抄评语。
“萧剑男!”贱男急皮怪脸的纠正道。
我赶忙弄出一脸的悔恨,道:“大队长!靠!不知道是你呀。我要知道!撞墙,他妈的,我也能不撞你!”
贱男眼神有点怪,他目光掠过我的脸,越过我头顶。我忽然察觉一片巨大的乌云罩下来,回头仰望,就见严振宇极具压迫力的站在我身后。
我被他揪着领子,刚站稳,一巴掌甩来,那骨突筋露的手打在脸上,火辣辣的,好疼!我急忙捂住,忍了半天,才把眼泪逼回去。不能哭,太丢脸!瞟一眼贱男,我以为他还不得幸灾乐祸,不想他毅然拨开振宇伸去搀他的手,自己挣扎着站起来,横身挡在我身前,义正词严的道:“你可是成年人!怎么欺负小孩儿!”
严振宇和我都望着贱男愕然,振宇还颇有意味的瞟了瞟我,然后说:“小伙子。你那伤流血了,不上药,可要感染的。”
我才注意到,贱男的衣服破了。胳膊肘搓破皮,露着红肉,看上去挺惨。一经提醒,他觉出疼来,抱着胳膊,直叫唉呦。
严振宇领我们到他丈母娘家,拿出医药箱,用剪子钳出酒精棉球,不擦伤口,先擦剪子,然后在夹出一个来,才是擦伤口的。
贱男的胳膊被严振宇反拧着,棉球一沾上他,他就要死了似的,弄得振宇都有点不耐烦。我很看不上那个娇气样儿,还觉得丢脸,就把胳膊肘架在他肩上,说:“我说哥们,忍着点,好不好!人家关云长刮骨疗毒,还能跟下棋!不比你疼?好歹咱也算个爷们!别给我栽面行吗?”
贱男就跟通了电似的,说:“你还熟读三国?没看出来!”他也不疼了,笑道:“头一回听你说一句话,不带脏字耶。”我挥拳要揍,被严振宇狠厉的眼色,制止了。
我跑去找毛毛玩,从大衣柜的镜子前闪过,我急忙缩身,在镜前站住,被打的那边脸都肿了。
我一怒冲到严振宇面前,指着红肿的脸,给他看说:“不对称了!”
严振宇已经给贱男包扎好,瞥了我一眼,说:“是吗?那边再来一巴掌,就对称了。”
我拧着眉头,看着他。他正收拾完药箱,也拧着眉头问:“不服气?”我揍他不可能,被他揍却很有把握,不敢不服,就低眉顺目,认罪服软的态度。
严振宇指着我鼻子尖说:“别躲!在叫我听见你满嘴冒炉灰渣滓,看了吗?”他把手边的水杯,往桌上重重一撂,贱男都一惊。端起我下颌,直视着我,嘴横着一扯,狠狠的说:“冲两杯胰子粉,给你漱漱嘴。”我浑身一紧,磕膝盖打颤,是真的害怕,他不是说笑的。
他起身放医药箱,贱男冲我吐舌头,我冲他扮个鬼脸。“林天雯。”
严振宇叫我,我问:“什么事?”
他扫一眼贱男:“他住哪?”我看贱男。贱男说:“成都道。”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