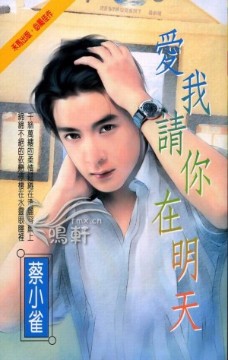谁让你在深夜里微笑? 师生恋2005最火的小说-第3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唉,这年头,当英雄难,当无名英雄更难。好,我们就按你的意思办!刘老师,安心养伤,班上的事情,我会安排好的!”校长激动地说。他肯定对自己思想政治工作的成功感到自豪。
校长和主席总算走了,我和老刘都常常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就发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过了好半天,他才自嘲地说:“活了四十多岁,×子无情戏子无义的道理也早懂了,怎么还吃这个亏?让你们兄弟多担心了,我这个大哥没有当好啊!”
我帮他点燃一枝烟,递了过去,说:“大哥,你就别说这个话了,这只能说明你是一个讲感情的人,对那个什么什么阿莲动了感情哪!”
他一听见“阿莲”两个字,眼睛里就放出了绿光:“不瞒兄弟说,我以前离婚的念头都有,为什么呢?她把我当个男人哪!”
贱,贱,真是贱!我心里说。
“现在有没有啊?”我笑问。
“不知道。”老刘狠狠吸了一口烟,“我TMD是怎么了?饱暖就思淫欲了?”
这可是我听过他说的最严肃的一句话。
也许是吧,我心里说。
元旦刚过,王记发死了。这也好,在墓碑上雕刻他的生卒年的时候,可以多写一年。
他的死,也是有预兆的,那就是他的脸越来越黄,呼吸越来越艰难,上课才讲10分钟,就要坐下来休息―――肺坏了。到医院检查,肺癌晚期。
尽管电视上报纸上整天吹嘘中国医学有多大多大的进步,但我们都知道,王记发可以做的只有一件事: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
他在医院的日子里,我没有去看他,因为我怕看见他。我总觉得,去看望一个濒临死亡的人,是一件很残酷的事,仿佛是在炫耀:你看,我多幸运,还活着,而你,马上就要死了。事实也是这样的,大家在看望王记发之后,最大的感受不是王记发多可怜,而是说自己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有的说,该享受就享受,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玩就玩,该乐就乐,该嫖就嫖。呜呼,这就是王记发的死给大家带来的收获!
说实话,我对他这个人也没有多大的好感,他是那种委琐而可怜的人,有点自私,但又不是心肠特别坏的人,但是缺少一中男人的气概。当班主任,还被学生打了一顿。可怜他,怕丢脸,不敢声张,只是在事情过了半个月后,才偷偷的告诉我。我当时很想叫在街上混的前学生收拾一下打他的几个畜生,他制止了,怕校长开除他。
“我丢了工作,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他说。
我也只好罢了。
现在,他委琐地走了,他一家老小还是喝西北风去了,我不知道政府对待这种家庭有什么帮助没有,好像是每个月给几个钱吧!
我希望他到了另一个世界,不要再这样畏畏缩缩的,要好好做一回男人。
代表市教育局出席王记发追悼会的是潘科长――胖阿翠。她在会上念了很动人的悼文:“。。。。。。王记发同志二十年如一日地奋斗在教育战线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合格人才。他的去世,是我们B市一中的损失,也是B市教育界的巨大损失。。。。。。”
记发大哥,你当含笑九泉了吧!
自从那次在罗马假日见过一面之后,我有半年没有看见这位潘科长了,没想到她的长进还蛮大的,官腔打的也蛮是那回事,就相信了“机关是培养干部的好地方”这句话。瞧,她宣读完毕,还亲切地和王记发的遗孀握手,并叮嘱她们要保重身体,培养好孩子,让记发在九泉之下安心。然后,她提高了声调:
“王记发老师是为了B市的教育事业而死的,死得光荣,死得其所。我们要继承王记发老师得伟大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当时很想立个遗嘱:有一天我死了,坚决不允许胖阿翠参加我的追悼会!
更可恶的事,追悼会结束后,校长还请她“指导工作”。其实我知道,就是校长想当“特级教师”,想我们的潘科长向局长要指标。
我靠,不教书的,不是高级,就是特级,我们这些在第一线的,评个高级,不知有多难。王记发死了,高级还没有评上!
胖阿翠拿班做势的在学校里转了转。还好,她没有发表什么高论,只是说要尽力为老领导“争取”一下。校长高兴得眉开眼笑。
TMD,王记发的死,倒成了校长评“特级”的理由。
第三十九节 最难忘的新年
朝烟放寒假了。她的父母都在C市,不回B市过年了,所以她也得去C市。离校前,她给父母打个电话,说还要过5天放假,却偷偷溜回了B市。
回来时,她穿着一件眼颜色很土的棉袄。我问:“怎么穿这个?我不是给钱让你买寒衣了吗?”
她笑着说:“这件就是呀!80块钱,剩下的钱,都买英语书了。”
我很难受。
她笑着说:“没什么,保暖就行。以后条件好了,再补给我!”
我只好默默地抱着她。
那几天,B市一中还没有放假,我忙着监考,阅卷,填写成绩单,也没有多少时间陪她。她就在家里当主妇,做饭,打扫卫生,居然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多余的时间,她就看英语。因为,她上的是全英班,这个学期,英语学习任务最重。
只有晚上,我们才可以不受打扰地在一起,看书,听英文歌曲:
“。。。。。。wherever you go;wherever you do;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wherever it takes or my heart breaks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这个春节,我又没有回去,我对父母说,我到朝烟家过年去了。他们虽然有些凄凉,却也很欣慰。唉,愿老天原谅我这个不肖之子。
朝烟到C市去以后,我就开始复习司法考试了。上次复习不够扎实,模拟试题做的太少,有些知识点都生疏了,所以趁寒假不上。
当然,我们每天都打电话。我知道她在C市也不快乐,因为在那里,她除了父母和姑姑一家,她也不认识别人,所以整天在家里看肥皂剧。
“无聊,无聊,我真想飞到你身边。”她在电话里说。
“那你快点来呀,我都想死你了!”
“还没有到初九啊,今天才初二,烦哪!亲我吧!”
我就对着手机狂亲起来。
“唉,只有声音!”她哀叹道。
我们就都盼望快点到初九。
好不容易到了初九,她又打电话说不能来了,因为她母亲不放心她这么早到学校去。郁闷哪!
到了正月十二,她终于启程了。为了蒙蔽她可怜的母亲,她先从C市坐车到武汉,来到D大,等她母亲打寝室的电话。她在空荡荡的寝室坐到六点,腿都咚麻了,她母亲才打电话来。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就打电话她,说,明天再回来吧,今天太不安全了。
“有二十多天没有见到你,想你想得厉害。就是步行也要回去。今天非见到你不可!”她坚决地说。
我只好答应了,心却悬了起来。
七点钟,她从车站打来电话,说马上上车了。我的心放下了一半。
七点半,我就带上为她买的寒衣到车站接她,然后一起到她机械厂的家去。
不知她的母亲是粗心还是实在拮据,朝烟竟没有一件象样的羊毛衫羊毛裤,她穿的几件线衣不是膨体纱的就是晴纶的,根本不保暖;那条线裤,线纹都磨平了;纱也荒了,可以透过来看灯光。寒假里,我去上车给她买了一件红白相间的羊毛衫和一条加厚了的羊毛裤。不过那天很狼狈,像作贼一样,偷偷的买,生怕熟人看见了。
我带着寒衣到B市长途汽车站的时候,她还没有回来。候车大厅的铁门紧锁着,站前广场上也冷冷清清。我走来走去,边走边跺脚。看着街上偶尔走过的行人,估算着她也该快到了。
到了8点半,还不见她的影子,我又紧张起来:会不会出车祸?会不会被绑架?唉,真不该让她回来!
这时,那个开旅社的女人过来了:“老板,住不住旅社?”
“不住!”我没好气地说。
“很便宜的,”她又走近了一步,神秘地说,“还可以帮你叫小姐。”
“滚远点!”我吼道。
“不住就不住,狠什么狠?”那女人讪讪地滚了。
9点钟还没有回来,我就租车去武汉。我对自己说。
9点钟,两道强光射向广场,一辆长途汽车缓缓驶进了广场,停了下来。我奔了过去,紧紧盯着下车的每个人。
第九个,朝烟!
“咳,这儿!”我喊道。
她跑了过来,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过去的一个多小时,真是太漫长了。
“我好想你,天天想你。”她把头贴在我的胸前,喃喃地说。
“我也是。”我轻轻抚着她沾满风尘的头发。
“这不是做梦吧?”她摸着我的脸说,“这是元无雨吗?”
“难道还会有别人?”我打趣道。
“不许笑我。你不知道,这二十多天有多难熬,我都快疯了。如果我妈还不让我走,我就偷偷地跑出来。”
“你敢吗?”我笑。
“当然敢。为了你,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大笑,挽着她进了路边唯一一家还亮着灯光的小餐馆,为她点了一份真正的羊肉火锅,一份青椒肉丝,一份小白菜。
火锅一上来,她就狼吞虎咽起来。我负责给她找肉,剔骨头,她只负责往嘴里放。
“我一整天没有吃饭。”她抽空解释道。
“为什么不吃?”
“没有见到你,没有心情吃。”
我心疼地揩了揩她额上被辣出来的汗珠,说:“吃慢点,吃慢点,这些都是你的。”
“好好。”她点头。
她真是饿坏了,一边吃,一边盯着铁锅,用眼神指挥我,该夹哪块肉,该吃哪块胡萝卜。
战斗了半个小时,羊肉全部消灭了,米饭也吃了两碗。她一抹嘴:“饱了!”
我宽慰地笑了。
出了餐馆,她冷得一惊,我慌忙用风衣裹住她。
站在风里等了半天,好不容易拦了一辆出租车。
“好想B市。”坐在温暖得车厢里,看着街上的灯火,她动情地说。
“就想B市啊?”我问。
“更想你。”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
终于走进了她那温馨的闺房。我迫不及待地拿出羊毛衫羊毛裤,说:“快来试试。”
她一脸幸福:“给我买的?”
我不言语,帮她脱下外套和旧线衣,穿上这套新衣服。
“好暖和好暖和。”她喜滋滋地说。
这些衣服有点紧,将她的曲线都绷出来了。我忍不住抱住了她。
“急什么!出去,我要铺床了!”她打落了我的手。
我只好坐在客厅里等待那消魂的时刻。
“进来吧!”女王终于发出了召唤。
我一进去,感到浑身的血都要喷出来了。她换了一条粉红色床单和大红色被套,自己穿着一套洁白的贴身内衣;身体与纺织品都沐浴着红色的灯光,热烈而圣洁。她白皙的皮肤,像罩着灯泡的纸,白里透红。她的眼里,纯清荡漾。
“你真美。”我喃喃地说。
“你今天才发现吗?过来呀,傻瓜。”
我不敢碰她,仿佛她是女神。
“你怎么了?”她问。
我慢慢地走过去,轻轻地搂住了她。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们在两处房子里,尽情地欢乐着,仿佛世界都是我们的。
“这个学期,我可能要回来的稀一些。”有一天,我们刚欢乐完毕,躺在我家大床上休息的时候,她不经意地说了一句。
“哦。”我应了一声,略微有些吃惊。
“我不知是准备考研好,还是修双学位好,反正得多花时间去学习。”
“嗯,应该那样。那就三个星期回来一次吧?”我小心地说。
“你没有意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