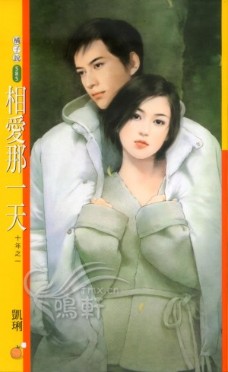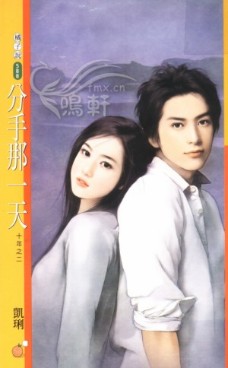那一年花正开-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房间里就好。
君柯站在师姐梅玲的身后,戏台上他那骄傲的神情已不在。他的眼睛里仅存有一些的荒凉。当他看到若由时,眼底却闪过一种,那似乎是惊喜一般的光亮。也许若由,只是在方君柯死寂的心中荡起一波浅浅的涟漪。也许,君柯仰慕的是若由那现实中真正的骄傲与阳光。而他自己却是生活在阴霾中的一个小小影子。只有在戏台上,他才有那样的绝世风华。然而他却不知道,若杉对他的迷恋,远远超过了任何可以取代的情感。若杉不顾林阿姨的反对,坚持了与君柯学戏的愿望。她每日站在园子的槐树下,等待方君柯的到来。每当见到她盼望的那抹白色的身影转过回廊,欢喜便堆在她的眉间。
“学戏是很苦的。”君柯淡淡的说。
“我懂……”若杉微微仰着的脸显着她坚定的信念。
那神情我似乎从来没有过,我站在窗前,看着他们那年轻的脸,我想,他们虽各自的心都不同,但那份同样坚定的情感,多少年后,回想起来,仍使我深深的感怀。
若杉望着满院尽谢的茶花,说:君柯说,徽剧要强调唱念做打舞翻的基本功和表演技巧。那是一种形式美。手,眼,身,步,法。君柯说,山膀,看着可能没有什么,但是要达到形式美。欲左先右,从腰部启,然后看手、眼随、上步、拉开、眼向前看、踏步、静心、亮相、睁眼、吸气、闭嘴、吸肚和挺腰这一连串动作。动作中领神,协调,浑然一体。也就是说,从这样一个小的动作,也要体现出一位巾帼英雄的气魄和矫健。君柯说……
我笑看着她。君柯还说什么?
她有些羞涩的低下头,“很多呢……”
“你都记得?”
若杉点点头,我哑然,对廊柱后面偷听的若由莞尔。他微微笑着冲我眨眨眼。却被若杉突然的回首撞见,她忙扯着裙子跑开,引来身后若由得意的大笑……
方君柯每日教完若杉,会跑来见若由,或谈人生,或谈戏剧,而或是闲来聊聊,都会听到他愉快的笑声。只有这一刻,他有些苍白的俊美的脸,才扬起真实的清澈的笑。方君柯说,他唱武旦,也唱花旦,然而武生他只在随唐演义里,演着罗成。在他的心里,只有罗成,才是一个英雄,他愿意自己永远是那个少年,那个飞扬着青春的英雄少年。他说,在乱世里面,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以杀止杀,只能牺牲一部分人来成全大部分人。而在现实中的生活里,他,就是被杀的那一个,所以在戏里面,他更喜欢演绎着这样的角色。他说,没有人能伤害到罗成,若是有,那就是挫骨扬灰的伤害。而他的伤害,正是自己给的。方君柯的一席话似乎也是在说着他自己,在此后的半年里,便真的验证了。
若由说,他在方君柯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似乎远离尘世的悲伤,这使他想起了我。我不禁感叹,这是一个怎样的少年,他的身上,有着我与若由不同的影子……
第三章 君柯(4)
也许,那段有着方君柯的日子,是我们真正快乐着的日子。
他与梅玲,给李家大院里添了些许新的气息。君柯教戏时,梅玲便安静的同我坐在回廊里。她象一位母亲,又似乎是一个爱人。梅玲常笑着说最大的愿望便是能与我学习英文。她对李家大院里的每一个人都谦和的笑,只有在我这里,她往往才能如一个小女孩一般,哪怕是片刻的迷茫与宁静。也让她觉得安然。
方君柯没有说什么时候离开,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归来。只是当我答应梅玲教给她英文的时候,云英突然准备离开了。因为戏班子永远都是漂泊的。临走之时,梅玲告诉我,人生是要选择的,就象她选择了与爱的人共同漂泊。而我选择什么,就是我以后走的路,无论有多艰辛,都会一路的走下去。自己走过的,除了自己,别人都不会记得。
八月十八,云英班结束了最后一场。
若杉紧紧扭着裙袂的手。我看到了她眼里的不舍。
锣鼓响起,方君柯踩着细碎的步伐。举首抬足,他的眼睛却不经意的飘过我与若由的身边,眼底竟是沉着的笑意。“春色撩人自消遣,深闺喜得片闲……”方君柯将“消遣”两个字的声音压低,深深的唱出了他独特的,阴柔的美。若杉说,这一段,他教给了她三次,然而她总是学不好。其实方君柯明白,她的心思从来没有在学戏上,就象他的心思也从来没有在教戏上……
梅玲与君柯走了。阳光很好的照耀着满园残去的山茶,若由的白衬衫映衬着他温暖的笑,他给了方君柯一个拥抱。君柯轻轻靠在若由的肩膀“如果我走了,你是否还会记得我?”若由说,会的。但他的眼却在望着窗子里的我。他知道我明白,他正在安慰一个寂寞的生命。君柯的离开,让若由为之感怀,因为我们从方君柯的身上,看到了彼此的颜色。
云英班离开的那一天,若杉站在五槐门的钟树下好久。似乎那绝尘的烟一并将她带走了似的。直到傍晚,她才姗姗走回。一进门,泪便落了下来。
第二天清晨,若杉打开房门。手中却多了包裹,我知道她终究是要去寻方君柯的。那就象她少女时代心里深深扎根的一颗种子,如今日、它长成了树,从她小小的心里生长出来,方君柯的离去,使她仿佛消失了阳光一样的几乎枯萎。她是要去寻找她生命的源头的。
林姨的哭劝,父亲的沉默,若景与予芝极力的挽留,都没能阻止若杉坚定的心,她决然的离开了。这是父亲失去第二个子女,他看若杉的背影时候的眼睛,仿佛一下空了一般。他扬起手,始终没有说什么。任她离开了。我记起父亲曾问过我,做女子象若杉那样不好吗。然而若杉的离开,似乎又一次让他看清楚他身边的每一个人,最终都会选择离开一般。使他的心深深感到痛,以至于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从不选择挽留,他害怕失去,象失去若离与若杉那样。
留住人,却永远也留不住心。父亲企图说服自己,将那份痛深埋在心底。如今若杉那踏出李家大门的那一刻,伴随着父亲空空的眼睛与扬起的手,她那青色的绣花鞋扣打青砖时的脆响,仍时常浮现在我的耳边。似是梦中的清脆响声,响彻在五槐门的深深巷子里。
然而半年后,我们才知道,云英在离开五槐门后的一个月里,方君柯便投江了。因为一名盐商强迫他唱武家坡,方君柯却回答说他唱旦,武生也唱,但只唱罗成……
后来他被割伤了脸。
方君柯说再也没有懂他的人与他想懂的人了。他也不能唱戏。
梅玲说她要岁他一起去了的,可是那一捧骨灰总是要个归处的。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坚定的诀别。她捧着那瓦色的骨灰罐子,一步一步走出了李家的大门。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离开李家大院的时候,留给我的记忆,只有那越来越模糊的背影。若离如此,若杉如此,梅玲如此。。。。
方君柯去了,而若杉却没再回来。
因戏而痴,因戏而死,戏就是方君柯的梦,戏就是他的人生。他更象是历史的驿车后面扬起的烟尘,一阵迷漫,便被车子抛弃、散尽。然则,即使是做影子,做烟尘,他也是那么投入,那么忘我,以至辨不清何者为戏,何者为真。然而现实总是无情地击碎了每一个人的梦想和信念,使芸芸众生如过客般活过,又如尘埃般消逝。
我们站在他每日练戏的树下。生如夏花,死如秋叶。若由沉痛的说。除了若离死去的那一天。第一次,看他哭泣。
“他唱旦,武生也唱,但只唱罗成……”还有若杉那赞许的微笑。
那个灵魂深处有着骄傲与冷峻的男子,他的英灵,是不是还在继续握着他的长枪,在自己的戏台上飞扬着他桀骜的笑容。
他的死,倒了两个女人的山川日月。
终于没有了,那冷彻骨髓深处的枪尖,随着灰飞烟灭。永远再不能够一见。
这是幸,或者不幸?
但他的爱,不会被忘却,那便足够。若由轻轻擦去泪,挽着我的手:走吧,起风了。
第四章 惘然(1)
又是一个风雨夜。狂风摇曳着桑枝,分不清楚喧嚣的是风,还是人。春晓掌灯坐到我的身边,“怎么,又睡不下了?外面闹得很,把窗子关了吧,或许能好一些。”她言罢便去关那窗子,我拉住她,“算了,我本也不想睡。”
“不知道大少奶奶生得是男还是女呢。”春晓轻声说。
“好久了,怎么还没见生?”我问她,“你去看看,莫要人说我们不关心。”
“我不去。”春晓放下灯,“生的什么,和我们又有什么干系。关心了,在奶奶那更捞不着好。有人关心便好了,多一个少一个我们,没什么干系。小姐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别平白的给自己添麻烦,等你嫁了出去,和这个家就没什么牵连了,还指望他们怎么的你?”
等我嫁了出去?我重复了她的话,却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
“前天在后园,听奶奶和老爷说,要给小姐找婆家呢。找的哪一家还不知道,可这等大事情,也不和小姐你商量,虽说婚姻大事父母做主,但奶奶可不是小姐的亲母亲,怎么说还是要问问你的意思的。况且若由少爷他……”
“春晓!”我抬眼见那门外,却只有喧闹夹杂着风吹响木门的吱呀声。
“小姐,现在全家上下哪有人有闲功夫听我们说话。”春晓看看门外,道,“小姐,我们家两位少爷对你的心咱们都从小看到大的。这么多年过去了,若景少爷有了自己的家,可他的心还在你这你也比谁都清楚。至于若由少爷,那徐家小姐他也认识半年了,你可曾见他们提过成亲的事?就小姐你一个人只字不提。老爷奶奶理所当然的认为小姐是在等嫁……”
“我在等嫁?”她这话却突然似乎是给我指引了道路一般的,或许,只有我有了归宿,若景,若由,予芝,还有和我们相关的人,便都有了自己的方向。也许,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解脱.我不禁有些惨淡的愉悦,一脸惊喜的看着春晓,她不解的望着我。
“夜深了,睡吧。”我轻笑。
听得春晓熄灭了灯,听见她幽幽的叹气声。我却突然睡得比任何时候,都安心起来。
第四章 惘然(2)
清晨秋文来,她一脸光彩得告诉春晓关于予芝生产的事情,她说予芝现在睡了,大少爷一直陪着。春晓问她生的什么,秋文说生的是一位千金,大少爷欢喜得不得了,且老爷今一早便在门外看了数回才回房里的。春晓关了门走到我床前,我极力的屏住呼吸。她坐在我的床边,半晌突然道,“你都听到了吧。”
我仍不做回答的闭着眼睛,她轻轻的推了推我,说小姐你可都听到了吧。她又问了两次,我终于慢慢坐起来,看着她说我听到了。她反而不知道说什么了,只是怔怔的看着我,然后便起身开始收拾东西,边收拾边说那一会就去看看吧。我点头,开始梳妆,我想还是打扮些,因为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与父亲说,所以今天别的什么都不想了。予芝那边也是要看看的。
转过回廊,我便停下来,回头对一直跟在我后面的若由瞪瞪眼睛,他马上开心的笑了,象个孩子一样笑。我也不禁扬扬嘴角,“你跟着我做什么?”我问他。
“我不做什么。”他有些无辜的回答,“我想你是去看大嫂,我和你一起去行不行?”
“不行。”我看着他有些窘迫的样子忍不住笑出声来,他马上明媚起来,又有些担心的样子缓缓说,“我还有件事情要和你说,你不会不高兴吧?”我摇摇头,他马上说“我们学堂要招收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