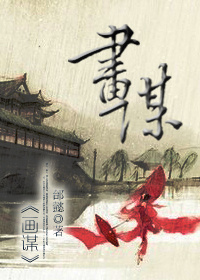与天谋-第10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虽快而且狠,可在他的眼中,以那样的刀法来对付他,就算是三五七个,也算不上中看。
可他还是应付得有一些微的讶然。
他做事向来谨慎小心,而且从脚步声响起时,就一直戒惫着。可是现在,却还是不免有一点应措不及。
只因为那人手里边的刀,并不是向着他落下,而是向着持刀人自己。
本没有表情的脸,在这片刻间慢慢的浮起个怪异的笑容来。木然得带点刻薄的笑意,仿佛是其他人的表情透过了这张脸,对着他得意而挑衅的一笑。一个木然的人,冷冷狠狠地对着自己行凶,却用着别人的表情笑着,满是诡异和恶毒地看他——能待如何!
分明是通过这人来警告他担心些孩子,而且在他面前公然的控制着来人做出自戮的事情来,是比语言还有有用的警告他——对方随时可以把水滴如何如何。
他能待如何,他只有出手。
本也是多事之秋。就算来人不是同对手有过接触,会知道些迹向。光来人是静池的下属,这一点,也断不能让这人在这样特殊的时间,以这样特殊的方式,死在这里。只会徒添事端。而且能救能做的一些事,他终是不愿意做到无动于衷。
虽然来人的举动不在意料之中,讶异之余,他却是也在片刻之间把其中利害关系想过,同时出手也并未因为那一丝讶异而慢上分毫。
火苗一腾起的同时,他着的还是女装。顺势一袖带着劲风,已经向桌上燃起来的纸张扫去,另一手中已经扬起一点寒光,架向了那一柄正在不知不觉间会把来人自己砍死的刀子架住。
书卷被袖风一带扫落,他那一袖力道不弱,那火势却怪异,莹莹微微的,却没有被卷灭,落在地上尤自烈烈燃着,腾起淡淡的青烟。他已来不及去扑灭——那一刀被架住,那人却不停手。反手一刀向着自己颈上横去。脸上还是那份古怪笑意,眼睛里却是木木地毫无神彩可言。
书郑燃烧的片刻间,火光摇曳里来人落下了五刀,他也架住了五刀。一刀比一刀更快更狠烈,显见得平日里下得的苦功。倒不愧静池的任用。只是这时刻,反而添了倒乱。
接了第五刀之后,他陡然腕一翻,手中收了刀,却是一指向着那人眉间指去。
失了他的招架那刀,依然不死不休的向着那人自己身上扎去。刀势快,他更快。终是抢在前头,一指点上了那人眉心。
那一指很轻很轻地,却如同耗了他极大的气力般。虽是他神色不动,眉宇间仍有一抹淡淡倦色闪过。
那只是一般的摄心术,这突如其来的疲惫,也不全是因为他耗了那一指去解开的缘故。
然而也幸得这一指,那人到底停了下来,如大梦初醒般的茫茫然张眼看他。
“谁让你送过来的?”他抻手扶了桌沿,对着一边燃尽的纸灰看也不看,盯着来人仍是问这一句。
那人怔然半天,并不记得到底方才发生什么事情,只对自己在他面前持着刀微微有些不解,又被他清利的眼眸一看,不由有些惶惑,想不明白自己究竟为何会在他面前拨出刀来,有所冒犯。可见他问来,却不责备,似没有看到般,提也不提自己手中执着的刀。这才定一定神,把刀收入鞘中。
静池已交代过对他一同从令,这人到底记得自己的本份,还是忍住了询问的念头。努力回想了一下,来之前的事倒还记得,当下恭敬答他。“御大夫浔蜎令在下有请浅草姑娘。”
“她说了什么?”站了片刻,待那些微的眩晕惑过去。他方才平静地问,似乎对他的回答交不感到惊奇。一边问,一边抻手去,把桌上的几个小点心收了起来。对于来人送来,已经在地上烧成一堆的灰烬始终不去细看一眼。
那人被他这一问,脸上却是浮出些迷茫来。他见这人答上不来,却也不再多问一句。随了那人就出了门来。只是来不及留下线索告知静池善袖。
可是那人引的方向,却是渐行向府外来。
他容色淡定,默默地跟着,也不开口多问一声。
随着那人行到府门前,门口处正有一人倾城倾国风情万种的笑着候着。不正是此时本应该在府里边作客,他还着意支使了狐狸去陪着的浔蜎?
是否善袖不解其意,睁只眼闭只眼的任浔蜎溜了出来。可就算狐狸坏事有余,还有静池一道作陪。若有什么变故,静池无论如何也会密令急告于他。现在浔蜎在这里,静池那一边又如何了?
可是门口分明停着两辆马车,丙辆一般装饰一般华丽的马车。可是这两辆马车的到来去有时间上的先后。他看的仔细——就算是冷天里,一辆车轨上的泥痕,已经略略干了些,算来停在这儿的时间正是方才浔蜎到来之时。而另一辆,沾上的还是湿湿的新迹。分明是刚刚到来的。
如果是浔蜎寻机离开,静池不会不告知他。而且从善袖端茶回来到被他打发出去的时间,离这人的到来不过片刻工夫。这么段的时间,不够浔蜎从府中到门口,再着人去‘请‘他。
若是浔蜎没有走,府内已经有一个浔蜎,此刻门前又来一个浔蜎,这门前府里的待卫也全然不觉得有丝毫怪异,难道都是瞎子呆子不成!
这个浔蜎是谁?府里边的浔蜎是谁?
这一两步间,不等他开口。浔蜎见了他,早也甜甜的唤着浅草妹妹,笑得花枝招展地迎了过来,亲亲热热的上前来携住了他的手。
门口有几个守卫,面对着浔蜎的丽色都有些手足无措般的呆呆怔怔。就连去先前带路那人见了浔蜎,都有些阁痴迷神色。浔蜎自然也乐于享受这种被人看的乐趣,看看同来的那人安然无事,只不过若无其事的冲那人笑笑。可看他的眼神中却分明有丝恶毒的示威和得意。
她的笑,从来都是霸道的美丽。这一笑,更是弄得几人神不守舍。可是这几人倒也不像方才那人那般的仿佛着了魔一般失魂落魄,倒还知道对他行礼问候。可是对于这个似乎是‘多’出来的浔蜎,却似乎半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
他从门口几人面上扫过一眼,终是一言不发。就连浔蜎唤他,也不曾应了一声,可是对着浔蜎拉手过来拉他,却是半点也不曾反抗。随着她一道上了马车。
“浅草妹妹真是玲珑剔透的识趣人。”两人同上了马车,浔蜎一手拉起缰绳新自驾车,另一手还是拉着他,只不过已经变挽为摛,牢牢的扣紧了他手腕血脉。翻手将他袖中的短刃收去,细细看看,才似放了心的笑起来。毕竟见过他那日的飞出的一刀,小心提防些总不见得是坏事。“放着明明大好的机会也不示警呼救,总不会是连开口的气力都没有了吧?”
他沉默着不答,也顺从的凭由浔蜎作为,不曾提力抵抗——似乎也真如浔蜎所说,无力抵抗。可是精疏精致的容色是平静淡定的,没有丝毫的惧意。
“你不求救,倒也是救了他们。”浔蜎妩媚的斜睨他一眼,另一手伸在她自己修长的颈上轻轻一抹,妩媚的做出个手势来。很美很美的抹颈的手势——只不过,浔蜎到时所要抹的断然不会是她自己的脖子。面上还是微微笑着,甚至连眼里也有了一抹笑意——猎物到手的满意。其中也微微有些好奇。“你甚至还救得了那个人?只不过你救了那人,却就救不了你自己了。”
见他还是平静的不答话,也不见得如何惊慌,冷清的精致着,又从精致中透出冷来。却别是一番不容侵犯的韵致。可是看在浔蜎眼里边却有些不舒服起来,有如冰针雪刺,眼中的钉肉中的刺。再如何精致清逸,总是要叫人不怎么受用的了。
浔蜎此时看着他,正有这种不怎么受用的感觉。明明浅草人已经落在自己手中,探她的脉息也确实是无基抵抗。浅草甚至连开口说话都做不到——至少从方才到现在就没有听她开口说过话。
可是为什么浅草的神色还能够如此安详,镇静得让分明是掌控了局面的自己有一丝微微的不安,仿佛有什么东西正脱出控制。甚至仿佛落入看不见的网中的人,不是浅草而是自己一般,一种本能的觉得危险潜在。可是却找不出来。危机有时会激起人的斗志,也不全是坏事。可是至少浔蜎便不喜欢现在这种感觉。
“我也没有想到,这么轻易就能让浅草妹妹上勾。我知道浅草妹妹聪明,又通于药理。一般的迷药只怕是难于近得了你的身。”见他还是安静的不答,浔蜎笑得越加的婉转,扣着脉门的手却暗暗加力。满意的看着他终于不能保持正坐的姿态,软软靠在车内的软垫上,本就苍白的脸色更是失了些血色。方才又接口,口气当中端的是得意。“只是你又偏要顾念着别人的死活,这才着了道是不是?”
他虽戒备着并不曾去碰过书卷,可书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真正的迷药,是从书卷点燃开始。无色无味的混和在烟里,而那时来人却已经做出惊人的举动来。
任何人被如此用人质来要挟,就算能够镇定以对,心理上都不免会有些失措。更何况书本以面前突然鬼火般的烧起来,而来人同时在面前举刀自决——只要有一瞬的失措,就足够了。可是他却立即就应对了。
火光一现,他便一袖袭去灭火,再见那人出刀,另一边出手救阻那人神志不清的举动。
可惜他那一视虽然将书卷纸张扫落,那火却不曾完全扑灭。他虽然架住那人的第一刀,却不防之后还有第二刀第三刀,让他无暇再去顾及地上烈烈燃烧的物事。
烟葛袅娜。
他在架住第二刀时,已觉不妥,在阻住第五刀时,便作出决断。就算是会泄露身手底子,也只能出手解开了此人所受的禁制——简单的术法,他也从善袖处学得皮毛。任是善袖教得乱七八糟,到底仗着他的聪颖,也算用得透脱。只不过如此一来,未免让对方根加提防。可是再拖延下去,他自知必将力有未甫。
听着浔蜎泣泣洒洒的道来。他干脆不去看她,转眼看去看车窗隙间掠过的街景。
“你就算是不救他,他也未必杀得了他自己。只要扎上一刀,痛上一痛,自然就解了。”浔蜎得意之余,却又带些好奇的笑看他。
扎上一刀,那人或许会清醒过来,可是也许扎上一刀,就算那人醒得过来,或许也就是个死人了。而且就算是人清醒过来,那一道青烟,已经着实呛了他一口,对方的目的已经达成。
即已经如此,那么能不流血的时候,还是不要流血的好,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而且那人也算是盟友,他若能救则救,对静池也算有个交代。
他干脆的合上眼去,任由浔蜎细说。
“那个孩子——”见浅草不恼不惧,浔蜎笑得更加明媚,扣着他脉门的手下劲力暗吐,欣赏着面前精致的容色又惨淡二分,却睁开眼睛,清冷的向她扫来一眼。“倒没有这般的运气。是要打要剐,还是要惊要吓,可全得由着我!“
“你想要怎样?”开口也有些吃力般的,他慢慢的一字一字的问。却在这不应该笑的时候,淡淡的微笑了一下。
微笑,欢笑,苦笑,冷笑,狞笑……笑可以有很多种,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含义,有时候甚至可以比语言更好的表达一个人心里的所想。
但他只是笑了一下,很快,一现而消,仿佛他并没有笑过。即不是高兴,也不是生气,甚至没有任何情绪,没有任何的意义。
可他到底是笑了一下,那一笑清澈而明朗,如同明月夜下清风过野,可望不可及。
然后静静地任由浔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