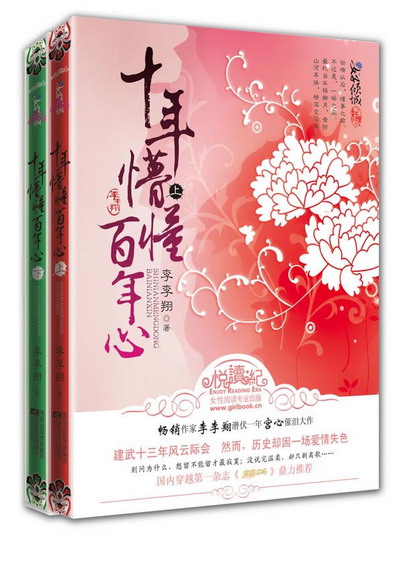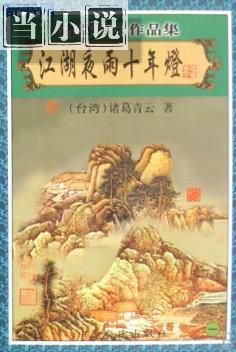暗访十年-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名字,叫做特战队。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特战队一共有多少人,都分布在什么地方。
后来,洪哥一辈子都在寻找这支神秘特战队里的战友,可是一个也没有找到,书籍上也没有关于这支队伍的记载。仿佛这支神秘的队伍根本就不存在一样,仿佛一夜之间他们就突然蒸发了一样,仿佛洪哥就没有参加过这些训练。洪哥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曾经无数次向人提起过自己在这支特战队里生活过,但是没有人相信。
但是我相信,洪哥第一次给我提起的时候,我就相信。
因为我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个夏天,遇到了一个曾经在特战队里生活过的人。
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纯净的年代,那时候的人们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的歌声,投入了如火如荼的四化建设中。那时候我在上初中专,每个假期都要进行社会调查,背着一个黄挎包,带着牙刷牙膏,开始浪迹天涯。那时候的人都很单纯,我只要拿出学生证和学校提供的社会调查证明,就常常能够免费乘车,免费住宿,甚至连吃饭也能够免费。
有一次,在皖南小镇的一家旅社里,我见到了一个身材高大,满面风霜的中年人。我们坐在旅社的小院子里,摇着蒲扇,和一同住店的天南海北的人谈天说地。那时候很少有酒店和宾馆,也没有一些洗脚按摩之类的特殊服务。人们出门都是住旅社和招待所。吃完晚饭后,大家就都走出房间,坐在院子里的树下,就像在一起生活了很久的大家庭一样无所顾忌地聊天。这些年,骗子像蝗虫一样四处飞溅无孔不入,每个人都像防贼一样防备着每个陌生人,小旅社被拔地而起的价格高昂的酒店宾馆取代,这种其乐融融的情景再也见不到了。
第一节:特战队的秘密(8)
那天晚上,在夜阑更深,困意袭来,别人陆续离开的时候,院子里只剩下了我和那个中年人。我递给了他一根香烟,短暂的沉默后,他向我说起了自己在特战队的经历。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让我将信将疑。他同样不知道自己的部队番号,不知道自己的上级是谁,不知道自己将会执行什么任务。一直到他离开了那支队伍,他都蒙在鼓里。他说,他以前是吃商品粮的,后来就变成了吃农业粮。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把山东的苹果拉到安徽出售,他是一名货车司机。
多年以后,这位货车司机的话,我终于在洪哥嘴中得到了印证。原来真的存在这么一支神秘的特战队。
但是,这位皖南小镇上的中年人,他当初的训练基地是在河边,而不是在山中。那么就是说,当时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特战队都在训练,等待着改变他们自身命运的机会。
而最后,他们等到的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农村来,再回到农村。
洪哥说,他们在那排教室里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填鸭式的教育。这种教育一直遗传到了今天,老师在讲台上喋喋不休,像布道的神父一样,学生坐在台下默默不语,只能被动地接受,像接受洗礼的少女一样。在少女的眼中,神父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是凛然不可侵犯的,是无比正确的。在神父的眼中,少女是一张白纸,可以画出随心所欲的图画,可以塑造出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
洪哥后来一直怀疑那个讲课的老师是不是有巫术,他的话语有一种催眠的作用,用缓慢的一成不变的腔调,说着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故事都是围绕着古代的刺客:要离、聂政、专诸、曹沫、侯赢、朱亥、豫让……老师一再告诫他们:士为知己者死,一诺重千金。这些古代的侠义刺客就是他们的榜样。老师的话像吸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的思维,老师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他们像被种了蛊一样身不由己。
有一天,一群荷枪实弹的民兵开进了那座大院,预想中的剑拔弩张并没有出现,淳朴的洪哥们相信只要是民兵就都是一家,一家人怎么能自相残杀,洪哥他们束手就擒。
接着是漫长的审查,事无巨细都要交代清楚,每一时每一刻的每一件事情都要交代清楚,别人能够看到的行动交代清楚,别人不能看到的心理活动也要交代清楚,反复交代,狠斗私字一闪念,大公无私为人民。审查的日子异常难熬,它的残酷程度远远胜过当初的特训。
洪哥挺过了心灵煅烧的六个月后,回到了家乡。
此后,洪哥成为一个农民。那段专职民兵的历史没有人提起,他也不想提起。有一天,当他有机会翻阅到自己的档案时,才发现那段历史根本就没有在档案中记载。
第二节:与知青的冲突(1)
洪哥回到家乡后,坠入了痛苦的深渊中。每个认识他的人都在议论他,每一个熟悉他的人都在用探测器一样的目光看着他,他像被扒光了衣服一样被人展览。他当初是敲锣打鼓被欢送着离开家乡的,而现在则是灰溜溜地冷静静地回到家乡的。他吃了一段时间商品粮,现在又成了吃农业粮的。虎落平阳被犬欺,凤凰落架不如鸡。那时候的家乡有很多关于洪哥的传言,每一个传言都与他的生活作风问题有关,每一个传言都说得有鼻子有眼,煞有其事。人们都有对桃色新闻兴趣盎然津津乐道的天性。
那些日子里,洪哥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他像被关进了铁屋子里,连呼吸都感到困难。白天,洪哥蒙头大睡,他只有在睡梦中才能暂时摆脱困窘和尴尬;夜晚,洪哥就悄悄起床,穿过睡梦中的村庄,一个人来到那条传说中闹鬼的小河边。他想遇到鬼,和鬼大战一场,他浑身的肌肉紧绷绷地,像一张拉满了的弓;他的骨节巴巴作响,充满了跃跃欲试的渴望,可是,小河边只能听到像厉鬼一样尖厉的叫声,没有见到一个鬼。洪哥大失所望。
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洪哥攀着嶙峋的岩石,来到了悬崖边,走进了传说中厉鬼出没的洞穴。一群不知名的鸟从岩洞里飞出来,在月亮的映衬下,它们的翅膀显得硕大无朋,它们尖声鸣叫着,凄厉的声音在明亮的月光下经久不息。洪哥打着手电筒,走进了那座亘古以来从未有人走进的山洞,那座传说中有鬼出没的山洞。
山洞里,一对狼夫妻在黑暗中盯着他这名不速之客,黄橙橙的眼光在黑暗中显得异常恐惧,像两对烛光。洪哥操起石头,向一对烛光砸去,砸出了一声长长的惨叫,然后,那对烛光黯然熄灭。另一对烛光突然扑过来了,携带着风声,洪哥操起装着三节电池的长长的电筒,砸向一只烛光,那只烛光熄灭了,剩下的一只燃烧着仇恨的光芒,洪哥手中的手电筒也熄灭了,手电筒在他的手中变成了曲尺,灯泡前面的玻璃哗啦啦掉了一地。狼咆哮一声,猛一回身,又向洪哥扑来,仅有的一只烛光明亮可鉴。洪哥扔掉手中曲尺一样的手电筒,略微一侧身,张开鉄钳一样的大手,扣住了狼的脖子,一扭身,将狼的身体掼在了岩石上,狼凄惨地叫两声,很不情愿地恋恋不舍地闭上了仅有的一只眼睛。
特战队出来的洪哥,一只金钱豹都不在话下,何况见到金钱豹就屁滚尿流的狼。
那天晚上,洪哥沿着洞壁继续向前走,看到远方有一星亮光。他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他能够从周边的影影绰绰辨别出自己所处的位置。快要走到另一处洞口的时候,突然起风了,午夜的风浩浩荡荡地灌进洞口,又丝丝缕缕地从另一处洞口溢出去,声音时而低沉,时而昂扬,时而像怨妇呜咽,时而像婴儿啼哭。这就是外面传说的闹鬼,这就是鬼过河的声音。
第二节:与知青的冲突(2)
而几十年后,我在暗访煤老板的一个夜晚,和长生走进了人字形瓜庵中,还能听到看瓜老汉在说鬼过河的事情。原来传说中的鬼过河,就是风过岩洞。这个情节,我在《暗访十年》第四季中写到了。
那天晚上,洪哥走出了岩洞,站在凄厉的寒风中,脱光了衣服,俯瞰着脚下的苍茫群山,仰望着月明星稀的浩淼夜空,洪哥发出一声声长啸,声音在山谷中激荡不绝,经久不息。寒风吹过来,穿透了洪哥的胸膛,穿透了洪哥的四肢,也穿透了洪哥的心灵。洪哥真想一伸脚,就会跳入亘古无人的万丈深渊中,从此解脱了所有的痛苦和郁闷。
然而,人生天地间,倏忽一百年,发肤魂魄受之于父母,你有什么权利结束父母给予你的生命?天地之间,漫漫无边,苍天之下,厚土之上,芸芸众生,人流熙攘,但只有一个你,每个人和你都不一样,你的容貌,你的心灵,你的性格,没有第二个人和你一样,你是天地间独一无二的人,你是亘古未有的,而将来也不会再有,你怎么能忍心结束这天地之间独一无二的生命?
无论如何,都要坚强活下去,洪哥对自己说。
上世纪七十年代,家乡周边的几个县市合起来兴建一座大型水库,抽调了一万名精壮年男子,组成浩浩荡荡的水利大军。那座水库,直到今天还在使用,流经丛山峻岭的汉江之水,流进了这座水库里,浇灌着几十万亩良田。
兴建水库又苦又累,没有人愿意去,很多人都是被生产队长逼迫着去的,但是洪哥抢着去,他想离开老家,去一个没有人知道他过去的地方。
但是,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洪哥依然是人们议论的焦点。那些年里,从吃商品粮又回到吃农业粮的人,比偷汉子的潘金莲还稀少,关于洪哥的谣言像风一样吹遍了洪哥足迹遍及的每个地方。洪哥像一只可怜的鸵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只能把自己的脑袋埋在沙堆里,以为这样就能躲避猎人的枪口。
然而,他错了。他是特战队的队员,又被从专职民兵队伍里开除了。他无论走到哪里,谣言都会如影随形。
洪哥在水库里拼尽全力干活,他将心中的悲愤发泄在了劳动中,一根根锨把被他别断,一把把
第二节:与知青的冲突(3)
水库越挖越远,吃饭越来越难,因为食堂只能选择在有水的地方,所以,以前上下工步行,现在就只能骑自行车了。有一天,收工回来,洪哥一个人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骑在最后面,远离了大部队,在一个拐弯处,洪哥与一群骑着自行车的知青相撞了。知青,就是知识青年的简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数百万城市知识青年来到广袤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以后,在他们回城后,他们掀起了一场“知青文学”的热潮,在他们的笔下,农村荒蛮破败,贫穷凄凉,他们认为在那里耽搁了他们的青春。至今,还有人在谈论知青和上山下乡。
那一天,洪哥和一群知青发生了冲突。
小时候,我经常能够看到我们那里的知青,他们穿着瘦腿裤,说着普通话。他们喜欢骑着自行车到处游逛,一出动就是成群结队,一骑车就是风驰电掣,老年人都说知青很像抗战时期的汉奸队,那时候的汉奸们都是人手一辆自行车,以便及时给鬼子报告八路军的行踪。
那天,洪哥的自行车和知青们的自行车倒在了一起,洪哥一个飞跃,跳在了路边,而知青们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得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剧烈的冲撞让他们的腿脚青黄不接,多处隆起。他们爬起身来,哭爹的哭爹,喊娘的喊娘。
一个个子很高的知青怒气冲冲地走到洪哥的跟前,嘴里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