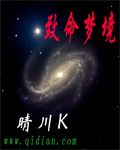致命的治疗-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头有50英尺长,一直延伸到下面的湖中。
尼琪立即同阿尼·扬森玩在了一起。他们跑到森林中,阿尼急着带她去看那儿的一个树上小屋。安吉拉走进厨房,同南茜·扬森、克莱尔·扬格和盖尔·亚巴勒一起高兴地准备着晚饭;戴维参加了男人的行列,一边喝啤酒,一边漫不经心地观看着手提电视机中播出的“红袜队”的棒球赛。
下午过得很安静,只被8个好动的孩子所引出的一些小麻烦所打断。他们不是碰破了皮肤,就是摔倒在石头上,再不就是相互吵闹。杨森夫妇有两个孩子,扬格夫妇有一个,而亚巴勒家有三个。
在这高兴的一天中,只有凯文的情绪欠佳。由于鼻子的扭伤,他眼睛周围出现了一些青紫。他不止一次地朝戴维大声喊叫,说他动作笨拙,不断地犯规。最后戴维把他拉到一边,他很惊异凯文居然为这么件小事而大兴问罪之师。
“我已经道过歉,”戴维说道,“现在我再次向你道歉。实在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完全是偶然事故,我绝对不是故意的。”
凯文恼怒地看着戴维。戴维觉得凯文并不想原谅他。但接着,凯文叹了口气,“算了,”他说,“让我们再喝一杯啤酒。”
吃过晚饭,大人们围坐在一张大桌子周围,孩子们则跑到外面的码头上去钓鱼。西方的天空仍然红彤彤的,霞光映照在湖面上。雨蛙、蟋蟀和其他昆虫早就开始了它们夜晚的合唱;萤火虫在树下的阴影中狂飞乱舞。
开头,大家谈论着这儿环境的秀美和居住在佛蒙特的优越性,大多数人只有在短短的假期中才能来这里。可后来大家的话题便转到了医药以及另外三位妻子的委曲和悔恨方面。
“我宁愿听一些体育趣闻。”盖尔·亚巴勒抱怨道。南茜·扬森和克莱尔·扬格衷心同意她的看法。
“现在正在进行所谓的‘改革’,很难不谈到医药问题。”特伦特说道。特伦特和斯蒂夫都不是佛综站的医生。尽管他们一直努力想同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及蓝盾公司共同组织一个受欢迎的医疗机构,但他们的运气不佳,行动迟了一步。大多数病员基地都被佛综站抢了过去,因为佛综站的计划具有某种侵略性和竞争性,占据了整个市场。
“这整个事情都使我感到消沉,”斯蒂夫说道,“如果可以想出某种办法养活我自己和我的家庭,我会马上脱离医学界。”
“那可是对你技术的一大浪费。”安吉拉说道。
“我认为,”斯蒂夫说,“那也会比这样强得多。我几乎要和某人一样打穿自己的脑袋了。”
提到波特兰医生,使每个人都怔住了。最后还是安吉拉打破了沉默。“我们一直没有听说波特兰医生的整个情况,”她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对此一直很好奇。我见过他那可怜的妻子;丈夫的死显然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她很自责。”盖尔·亚巴勒说。
“我们只听说他很抑郁,”戴维说,“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他最后一次打篮球时,对他的一位臀部手术病人的死亡感到十分紧张,”特伦特说,“是那位艺术家萨姆·弗莱明。后来我想他还失去了其他几个病人。”
戴维感到一阵寒颤透过自己的脊背。他想到自己作为初级住院实习医生时,看到自己的几位病人死亡也有过同样的反应。这记忆就像一阵寒气穿心而过。
“我甚至怀疑他不是自杀的。”凯文突然说道。这话使大家大吃一惊。这一天,凯文除了抱怨戴维撞断了他的鼻梁之外,一直没有说什么话。甚至他的妻子,此时也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他,好像他的话亵渎了神灵一般。
“我认为你最好解释一下自己的看法。”特伦特说。
“除了兰迪本来没有手枪外,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凯文说道,“这种令人困惑的事情,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他从哪里弄来的手枪?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手枪是兰迪从他那里借来的。他并没有出过城;他在哪里搞到的手枪?难道是从路边拣来的?”凯文大声笑起来,“想一想吧。”
“不管怎么说,”斯蒂夫说,“他反正弄到了手枪,只是没人知道而已。”
“阿琳娜说她一点也不知道他有手枪,”凯文坚持说,“另外,他是直接对准自己的前额射击的,而且角度朝下,所以他的小脑溅到了墙上。我从未听说过有谁是那样朝自己射击的。人们一般是将枪管放进自己的嘴里,以免血浆四溅;还有的人是对准头的一侧射击。很少有人对准自己的前额射击,尤其是使用长管的马格南左轮手枪。”凯文像遇到戴维的第一天那样,用手指做了一个开枪射击的动作。他将手枪对准自己的前额射击时,那动作显得特别别扭。
盖尔感到一阵恶心,不禁打了个寒战。尽管她嫁给了一位医生,但一谈到血和内脏,她就觉得心里难受。
“你是说他是被谋杀的?”斯蒂夫问道。
“我只是说我个人认为他不大像是自杀的,”凯文重复说,“除此之外,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评判。”
雨蛙和蟋蟀的鸣声充满了整个夜晚,大家都在思考着凯文扰人的评论。“好了,我认为这都是胡说八道,”盖尔·亚巴勒最后说道,“我认为他是因胆怯而自杀,我很同情阿琳娜和她的两个孩子。”
“我也是这样看的。”克莱尔·扬格说道。
又是一阵令人难受的沉默。最后斯蒂夫打破了沉寂,“你们两个怎么看?”他问道,眼睛看着对面的安吉拉和戴维。“你们觉得巴特莱特怎么样?你们过得愉快吗?”
戴维和安吉拉交换了一下眼色。戴维先开了腔,“我过得很愉快,”他说,“我喜欢这个城市。我既然已经成为佛综站的一员,我不担心医疗政治。我已经走进了一项艰巨的医疗实践,也许有点大艰巨了。我遇到了很多肿瘤病人,这是我没想到的,我也不想有太多的这种病人。”
“肿瘤是什么?”南茜·杨森问道。
凯文不相信地怒视了妻子一眼。“就是癌症,”他不屑地说道,“南茜,我的天,你连肿瘤也不懂!”
“对不起,”南茜同样恼怒地说。
“你遇到了几个肿瘤病人?”斯蒂夫问道。
戴维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让我想想,”他说,“约翰·塔洛得的是白血病,现在正在住院;还有玛丽·安·希勒得的是卵巢癌;乔纳森·埃金斯得的是前列腺癌;唐纳德·安德森据说是胰腺癌,但最后确诊为良性腺瘤。”
“我知道这个名字,”特伦特说,“那个病人接受过惠普尔疗法①。”
①惠普尔(1878…1926),美国病理学家,通过动物实验发现动物肝脏可用以治疗恶性贫血,与Minot和Murphy共获1934年诺贝尔医学奖。
“谢谢你们告诉我们这些。”盖尔讽刺地说。
“也只有四个病人嘛。”斯蒂夫说。
“还有呢,”戴维说,“我还遇到了桑德拉·哈希尔,她患的是黑瘤;还有玛乔里·克莱伯,得的是乳癌。”
“亏你都能记得他们的名字。”克莱尔·扬格说道。
“这很容易,”戴维说,“我记得他们是因为我把他们都看成朋友。我定期给他们看病,因为他们患有多种疾病。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都经历过多种治疗方法。”
“好了,那问题在哪里?”克莱尔问道。
“问题是,我既然把他们看作朋友,并且负有为他们治疗的责任,我就担心他们会死于疾病,我会感到自己有责任。”
“我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斯蒂夫说,“我不理解一个人怎么会去学肿瘤学。愿上帝保佑他们。我之所以学妇产科,因为一般说来,这是一种愉快的专业。”
“眼科也是这样。”凯文说。
“我不同意你们的看法,”安吉拉说,“我很理解那些学肿瘤学的人们。那些患有绝症的人很需要人们的帮助,能为他们治疗是一种安慰,是值得的。而在其他的许多专业中,你永远不会真正地知道你是否帮助了你的病人,但对肿瘤学来说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我同玛乔里·克莱伯很熟,”盖尔·亚巴勒说,“她是我第二个孩子钱德勒的老师,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教学很有创造性。她用塑料飞机在挂图上移来移去,使学生们对拼写课很感兴趣。”
“她每次应约前来看病时,我都很高兴见到她。”戴维承认说。
“你的工作怎样?”南茜·扬森问安吉拉。
“再好不过啦,”安吉拉说,“科主任沃德利医生是位很好的指导老师;设备也是一流的。我们工作很忙,但一点也不枯燥。我们一个月要做500至1000个活组织检查,这是了不起的数字。我们能看到有趣的病理现象,因为巴特莱特医院是一个三级医疗中心。我们甚至有一个病毒实验室,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总之,工作很富有挑战性。”
“你同查尔斯·凯利闹过别扭吗?”凯文问戴维。
“从来没有,”戴维吃惊地说,“我们一直相处很好。事实上,我本周刚同凯利和来自伯林顿的佛综站质量管理主任见过面。对病人在评价表上提出的各种反馈意见,他们两个人的态度都很客气。”
“哈!”凯文不屑地大笑起来,“质量管理只是小菜一碟,等你看到你的利用率报告后就知道了。那通常要花两三个月时间;到那时我再看看你对查尔斯·凯利有什么看法。”
“我不关心这些,”戴维说,“我对医学是认真的,只知道好好为病人看病。我不在乎什么住院率奖励计划,也绝不打算为获得去巴哈马旅行的大奖而花费心机。”
“我不管,”凯文说,“我认为这是个好计划。在批准某人住院时为什么不多想想呢?这儿的病人都听你的指示。病人住在家里的条件比医院里好些。如果医院要送我和南茜去巴哈马旅行,我是不会反对的。”
“眼科同内科有些不一样。”戴维说道。
“不要再谈这些医学方面的事了,”盖尔·亚巴勒说,“我刚才在想我们应该把电影《大寒流》的录像带带来的,大家在一起看这电影棒极了。”
“它可以激起大家的争论,”南茜·扬森说,“可比这些医学方面的无聊话题要刺激得多。”
“我可不需要那电影让我想到我是否愿意让自己的丈夫同我的一个女友做爱,以便她可以生一个孩子,”克莱尔·扬格说,“绝对不需要!”
“唉,听我说,”斯蒂夫说道,一面从懒散的姿势中坐正,“我不会在乎的,尤其当那人是盖尔的时候。”他伸出胳膊,抱了盖尔一下。盖尔正坐在他旁边。她咯咯笑起来,并故意在他怀中蠕动起来。
特伦特将一些啤酒朝斯蒂夫的头上浇去;斯蒂夫想用口接住。
“那一定是一种绝妙的情景,”南茜·扬森说,“而且,还总有烤火鸡吃。”
在其后的几分钟里,大家都狂笑不止,只有戴维和安吉拉没笑。接着大家又谈了一些下流笑话和桃色新闻。戴维和安吉拉一直似笑非笑,偶尔也点点头,但他们并没参与。
“大家等一下。”大家正为一个有关医生的极为淫荡的故事狂笑不止时,南茜·扬森突然说道。她极力控制住自己。“我认为我们应该打发孩子们上床睡觉,这样我们自己可以进行一番裸泳。你们觉得怎样?”
“我说就这么办。”特伦特边说边与斯蒂夫碰杯把啤酒喝完。
戴维和安吉拉相互看了一眼,不知道这一提议是否是在说笑话。每个人都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