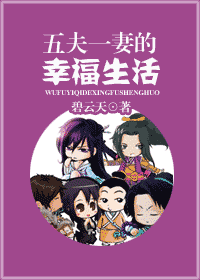������������-��70����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ˡ�
��������˴�һ·�����Ͷ٣���ЪϢ�գ���������ѰΪ����Ϊ������Ҫ̸����
��ŵ����
��۬��ȥ֮��ȥ�ˊ�ľ��ҡ��������ᵽĸ�ף�����Ҫ̸ʲô������Լ�IJµ��ˣ���Щ���ҵ������չ�Ҫ�������������Ϊ������֮�ã����ú�������ʵ��۬���ˣ����в���̫��о���ֻ����Щ̾Ϣ�������������������Ӱ㣬���ڸ���ֻҪһ�뵽����֮����֮��ü������ʲô��˼Ҳû���ˣ�Ȼ����Ҫ��һ��Υ��ʼ��ǰ�ӵ�ĸ��ô��ĸ���Ƿ�Ҳ����Զ�һ�㡡������ŭ�����ڊ�����
��ȥ��ĸ��Ҳ�ü�����ת���������˼��ֻ����ʱ����ĸ������Թ����Ų������ᣬÿÿӦ��ȴ�ٳ����ж���������������ȥ������
��ֻ۬�����з��ҡ�
���ˊ��ң���������ͷ������£���������С��Ӧ�ò����W�ģ���ô����Ϊ�˶�����ĺ����ˡ�
��۬վ�����⣬�����ȥ���������ˣ����ϲź���Щ��
��ij�����δ�U�����ʵ��������˽����ں�˿�ϣ�����һ����⡣
����ɾ�������һ�߰�æ���ߣ���������֯��ݸϯ�������봺��ÿ���ʱ�������ܿ���ĸ��Ϊ�˲�ͣæµ�ģ�����Ȼ��
���ɣ������ٴ��ʵЩ����ϸЩ���У�С���Ӹճ���Ƥ��ϸ�廬�ۣ���˳��ߣ������������ÿ������ٵ����ˡ���
��˵���ɣ��ۿ�ȴ�Ǻ�ģ���Ȼ�տ��ˡ�
������ˣ���۬ע�������ˣ��ܸо���ͬ��ĸһ�����˿��������Ĺ�ϵҲ��Ϊ���ܣ�����˵����ʱ�ľٶ���ȫ����һλ�������е�λ�ã�����ȫ����һλ�����ߣ���Ȼ�DZ�����۬����֪������ȹ���ĸ��ֹһ�Σ���ĸ����������³���������������ǿ���ģ�������ÿ���˶����ĸ����˼������
����ԏյ���Խ����δ��ʾ�����ã����������˵Щ��Խ�Ļ���Ҳ�����Ž�����㣬���Ǵ�����������
��Ҳһ�㡣���ԣ��ι�֮�У���Щ�۹����˵ģ��������۸�������
�����ˣ����ۺ�ʱ�����ǰ�Ĭ����
���ȷ���վ���ſڵ���۬��æ�����������ӡ���
�����������֮������
��Ҫ��������۬æ����ǰ����ס�����ֱۣ����������������������ӽ��տɻ��á���
�ว�˸��Ǹ�ЦЦ�������ã����������������������ˣ���
��۬������ֶ��˶٣����ţ���������ˣ���������ȥ�������ǡ���
�������������Ȼ֪������ô���£�ֻ��ͷ�������ˣ��㲻��������
��۬��Ȼ��Щ���ţ��������ɼ���ȥ�������������������ϣ����࣬�����ٶ��������ա���
��һ㶣�̧ͷ������۬���غ��д��뷨�����Ƿ������£���������������У���ֻ۬һ�㲻�Ծ������Ϸ�����
���ͷ��
����������ȥ���ң���
û��ͷ����۬������˼����������δֱ���ᣬ������ȴ����������ģ������ἰ�ڸ���������ɫޓ�죬����д��뷨������һ�����ˡ���
���˽����������ǣ�ԭ��֪��ʱ�켺���ˡ�
������ڊ�����Ϻ���������������ɫ����Ī�������÷���������۬����������������룬��ȴ�Dz�Ը�������Ҽ�������������ź���롭��
�������������ģ���Ϊ��Ļ���ƽ���������к��Dz������ģ����²����缺����ô�����Ŷ�ʱ��������ˣ��������ˊ࣬�������IJ��ǡ�
�������ȫ��ͬ�����������ۣ���ȴ��������ȥӦ��ĸ��ѹ������Щ���Ҽ���������֣�Ҳ������������֣���ЩŮ���ǵ���������Ȼ���ᣬ�����NJ�ȥӦ��ǿЩ����Ҫ������֮�ã��������Ҳδ�����ɡ�����
��۬�����Ŋ���Ѱ�ŷ��ӵģ��������˺����˯���ˡ�
�ڶ��գ���Լ���������IJ��ң���ȴ���������ˊ������档
��������˵���ز������ࡣ���գ�����һ�£����븸������Լ����������۬��Ը����ϣ������ĸ������������ҡ���
�����٣�������ȷʵ˵���˻�����ȴ��֪�����к���ɣ���
��������Ϊ��һ��Ů�ӣ��������㲻�ÿ���������������λŮ��Ըͬ�ڸ������������
��������ר����
˵�������ͷ���ؾ���Ƭ�̣�ĩ������������ͷ��Ц��Ц�������ʣ���������Ϊ�أ���ʼ���Ÿ�������ŵ֮�ˣ�����˵����������ز���������������ҷ���������ң������������ڸ�����������ô�������Ŀ�������
�κ��Ǿ���˵����������ֻ�ͺ��������㶶��Ŋ���ϲ�����Ů��������������Դ�Ϊ���������Σ���ŭ�����죬�����ۣ����ۣ���������������֮�ã��Լ̺��á���
��ЦЦ����ʹ���������������ף���ʱ���˶���Ը�ޣ�ǰ��������ڊ࣬��������Ӵͻ飬������һŵ֮�ԡ����ȴ��������֮�ã��Լ̺���������۬������֮�á���������������������̺��ں���λ�ã��NJ����鳯������������֮���ö��ˣ�����ز����ģ����ο������������������dz��Լ���һ������˼�������Ƶ�����������ר����ȴδ�ز����ּ���ɡ������Լ̺��ã��༺�������պ�Ҳ�������˸�ʮ������������ɣ��ֺαض�Ҫ����ֵò�ʹ�죬������ŵ������������ʳ�Ѱ�������Ӣ������Щֻ�±Ȋ����ʮ���գ���
һ�����ۣ��κ����ƿ�������
��۬������ͷ���̲�ס��Ц�������������ࡣ����ʮ���˸�����Ȼ����������Ҳ˵��������ֻ�Ǹ���Ƣ�������ף��侫��������ʱȴ�������������ͯ�����ֱⷬ��֮�ֻ�»�ü�����ɫ���ˡ�
�κ������������ζ�����ը�ˣ�������DZ����ö��Ӽ����ˣ����߳�ŭ������۬������������ʱѧ�����������������������������̸����
��۬�������죬���һ�£�������ɫ��ȥ��
����һ����Ц�Ċ࣬������̲�ס���ˡ�
�κ������������������һ�����������˺佫��ȥ������ȥ����ȥ����
������������
ҽʦϸϸ�鿴������ҩʯ��ų�ȥ��
��۬�����������ã����̲��ã�����ҽʦȥ�������ġ�
��ҽʦ���Ḿ�ɰ�����
ҽʦÿ�ձ����˷��ϼ����缺���ͣ�������������ü���Ҫ������ˣ��ֱ�ȴ�DZ���ס��
�����ӡ���
��۬�����ĺ죬����֪����֪�Ƿ����й���֮��
ԭ����㣬�ѹ��⼸���ܲ�����ͣ��
�����ǣ�����ȴ���С��Щ����
������˵�ţ���ͷ��һ����ɫ������ײײ�������������ӣ����ӣ����²��á�����
��۬����һ·���������ڣ��������ש���ϣ�һֻ���۶��������꣬��ɫҩ֭����һ�أ������볣����Ǹռ岻�á�
�����ɫ����������Ȼ������ȴ��δ�������������Գ����ֲ�������������������ۡ�
������£���
��۬�����������ţ�ʼ�����ŵ������£�ȥ�������֣�ȴ�������ְ������š���һʱ����һ���������Ê���˾��£�
��ò�����ƽ�����������̧ͷ�����赭д�������������һ��������
��۬�ס�������ˣ���
��������榡���
��榣���۬���������һ�飬�벻�����Ǻ��ˡ�
��Ϊ�ν���榣���
��ȴ������ɫ�䣬���˴��ǣ���������¶��ߡ�����˵�����棬�������ˡ�
�¶�����۬�ֳ���һ����
δ�ع���������ȴ���ַ��˷���ͷ�������������������ˣ�������Ը�������ǰա������ӽ����ָ�Ѫɫ��
��۬�Ļ�������˼����Ἲ��������������榾�����¶������Ê���˵�����
��������£����ˣ�ȥ������榸�������
��۬�������������H�¶���Ϊ������֪���˶��ٿ࣬������Щ�£���һ������������Щ�����ǰ�����֣������������ߣ�
�������ˣ�����ȴ������������䣬�����������գ���
���˳���ȥ�����ˣ�����������۬��ը�����飬Ц��Ц��
�����ʱ��Ц�ó�������
��Ϊ�β�Ц����ʱ�����������ˣ���������һֱ������������֮�˶����أ���Ȼ����ȫ�����㣬����û�ж��裬һ��ˮ��ƽ�ˣ��Ļ�����Щ���H�¶�����
��۬���˶٣��������ȴ������֮���������NJ࣬���������裿��
��Ӽ���ȡ��������������������֮�����ж��ۣ���Щ���¶���һ��ȥ�գ�����۬һʱ�����Ŋ����˼�������Ǵ��㡣����
��Ȼ���Է�����ʼ���²�������������������۬������������
����û��δ������ϣ������ǡ�������
����Ժ֮�£���۬�������ٹ��ʣ�������û�£���������������������
��һ������������࣬ÿ�յ��б����档
������۬�����������ŵ�Ů�ӣ������������˼���²�������ȴ���˴������ô����榼��羪��֮��ÿ�ռ��Ŋ�ʱ�����Ӳ���Ȼ�Ľ�ֱ�š�
��ȴ��ʼ����δ��������һ�ۡ�
ĸ��֪�����£�����������Ž����������ߣ�����ݵĺ�������ĸ�׳��ˣ��ѵ�����NJ����˼�������Ժ�ĸ��ȴ����δȥѯ����Щ��Ժ֮�¡�
һʱ���ð���������ֱ����������
�����е�Ů��һ��������ʹ���죬���������ף������밢ĸ������æ�ż���������
�W��֪����������ˣ��һ������Ҫ�����������ʮ���飬ֱ�������ܡ�
������ˣ�ȴ�Ӱ��ܳ��������ˣ��������ϲ���ϰ��ܣ��Wԭ�Ǹ������ġ�
*********
ʮ����ι�����ƺ���ϣ���̺��һ��ݸϯ��������������Ұ�ͣ���Ȼ���ض��ǽ���Щ�ģ������κ�ް����۬���Ǻ��ѵ���������ˡ�
���W����������
��Զ�����Wһ�����������˺���������������������ϥͷ�ϵIJ�м��Ӧ���ǣ��Ͻ�����ǰȥ��ۡ�
����������ů�����밢ĸ����������棬��֪��ĸʹ�˺η��ӣ������游������ͷ���������İ������ι�̫�ӣ�ȴҲӦ�����̾������յܼ���
��ʱ�W���ٽ������ݵ����ӣ���ɫ�������Ͼ����ף�����۬�м������ƣ��ֻ�����ס�þ��ˣ�������������������
����ĸ������������Ծ�ʮ��ǰһ�㣬����̫��仯�����۽�һ˿ϸ�ơ�
��۬��������׳�ֻ꣬����ʱ�ķ�ɣ�һ�����ż�ֻС�ܲ�ͷ��ȫ����Щ��������Ŭ���Ľ����
����������������������ܣ���ĸ������춼����Ӧ��������һ�������ܽǵ�С�����������죬�ܲ����Ⱒ��ÿ���к���ģ��������ֽ�����һ�˿��
���ף��٣�Ī���������´ζ�����ͬȥ����
�W����Ц������Ӧŵ���������ַ����ͣЩ��
���W��������������
����ĸ���������W����������ô���W����һλ��ʫ�٣���
��ʫ�٣���Գ��ܵĹ�ְ����̫�����������֪��һЩ����ʫ�ٹ���˼�⣬����ȥ�����ɼ�ʫ��ġ�
��Ϊ����Ҫ����ʫ�٣�����۬�����ף����źúõ�����ȥ���Ҫ����Щ��
��ֻ����ﰢĸԲ���α���ܵ��ΰ������W��������غӱ�һ·�η������������밢ĸ˵�ģ�������Ѱ����������������
�ཫ��ʳһһ����ݸϯ��Ц��Ц�������������ģ���ȥ�ա���
�ְ�����һ�۽���һ�������ι������ˡ����������ֻ�²�֪�������������ɣ����ı㶼һ������Щ����Ϊ�Ŵ��£���֪�ھ��˶��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