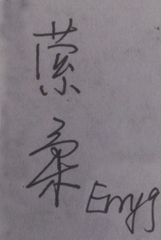萦柔-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萦柔痉挛,而她的反抗在曾尧逸眼里就是一场笑话。
梁萦柔觉得下体很疼,曾尧逸的肉刃像在千刀万剐著她,他高高在上,俯视著卑微的她,梁萦柔痛苦地闭上眼睛,经受著这场凌辱。
曾尧逸似乎还嫌不够,硬生生又把她的衣服扯坏,肆意地蹂躏她的双乳,用指甲用力地扣著他的乳头,疼得她想要死掉,梁萦柔紧紧地咬著双唇,可是曾尧逸各方面的施压和侮辱终於让她崩溃,哭喊道:“不要了……求求你……呜呜……疼死了……我疼……”
梁萦柔的求饶并没有让曾尧逸心软,反倒是更加凶狠地冲刺,梁萦柔快乐并痛苦著,曾尧逸的抽插速度不断加快,让她率先达到了高潮,而後就感觉到体内一股热精喷射进来。
当梁萦柔以为就此结束的时候,曾尧逸让她翻了一个身,从背後再次进入,毫无疼惜之意,继续凶悍地狂抽猛顶。
梁萦柔悲哀地哭泣,她呻吟低喘,曾尧逸清楚她的每个敏感点,仿佛就为了把她击溃,次次往那些地方顶去。
这个夜晚梁萦柔像是失去了自尊般,在曾尧逸的刻意用途下,不断地在他身下高潮,到最後全线崩溃,身上布满了淫靡的痕迹,汗液、爱液、精液,还有尿液,她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大脑,尿了不止一次。
<% END IF %>
☆、005
梁萦柔醒来的时候,还是以狼狈的姿势躺在沙发上,而曾尧逸早已不见人影,她的身上黏腻不堪,痕迹斑驳,这是第一次她跟曾尧逸做爱之後,他没替她清理身上的黏液。
梁萦柔跟曾尧逸一起的那麽多年,两个人肯定有过争吵,就算那样他们性爱後,曾尧逸也不会忘了替她把身体洗干净,那完全不像一个黑道老大有的细腻。
梁萦柔很费劲地站起来,外面的太阳射入房内,她才知道窗帘都没拉上,她该庆幸她的出租房对面没有建筑物,梁萦柔赤裸地走到窗前,用力地拉上窗帘,今天的她就适合黑暗。
看著沙发上糜烂的痕迹,梁萦柔一阵嫌恶,要不是她没力气将沙发扔掉,她绝对不会留著如此具有羞辱性的家具。
梁萦柔拿了一个大垃圾袋,把沙发上的毛毯和枕头全部扔了进去,再去浴室拿了手套、抹布和消毒液,使劲地擦拭沙发,直到弄得满屋子都是消毒气味了,才就此作罢,她把手套和抹布也全部丢入了垃圾袋,把垃圾袋绑好,扔在门口,然後进入浴室。
梁萦柔望著镜子里的自己,双眼无神,面色憔悴,虽然平时的她也没有丰富的表情,可是现在就如同失去灵魂的躯干。
梁萦柔的大腿内侧满是干涸的精液,而她的小穴里还不断地流出来,可想而知他们昨晚做了多少次,曾尧逸是个性欲很强的人,梁萦柔应付他其实很吃力,但是他不会勉强她,不过昨晚的曾尧逸应该没有自制,她现在还觉得甬道里仿佛有硬邦邦的肉柱在抽动。
梁萦柔站在花洒下,打开冷水的一面,刺骨的寒意终於让她元神归位,她紧紧地抱紧自己的身体,终究忍不住哭泣的冲动,在水声的作用下,开始放肆大哭。
起先梁萦柔还是站著哭泣,到後来完全支撑不住了,直接坐在地上,抱著双膝痛哭。
在她十四岁之前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有个和睦的家庭,疼爱她的父母,在学校又是三好生,不仅受著老师的关照,跟同学关系也很融洽,找不出一点不如意的地方。
可能就是之前的人生太过完美了,才会让她连遭挫折,先是父母去世,再是跟曾尧逸的纠葛,以为生活终於平静了,结果曾尧逸又出现在她的视野里,让她不断地回忆起过去的日子,哪怕快乐居多,她也不想再跟曾尧逸扯上关系。
梁萦柔在向警方提供了曾尧逸的罪证时,就决定了跟他一刀两断,那天晚上她就收拾了行李,乘著火车离开了这个城市,战战兢兢地躲在小旅馆里,整天看报纸和新闻,等待著曾尧逸的宣判,就算等到了他的宣判,梁萦柔依旧不敢放松,她又继续了几个月,确定了没人在寻找她,才敢再次出现,而她也懂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她搭车重新回到了这个城市,选择了郊区的这所学校读研。
梁萦柔的成绩虽然不错,可是她落下了不少功课,整日刻苦学习,才勉强考上研究生,校园生活让她开朗了不少,她渐渐地放开胸怀,准备重新生活,没想到三年这麽快,曾尧逸已经从牢里放出来了。
曾尧逸防备心很强,就算对待最忠诚的手下也有所保留,那些全是跟他出生入死的人,梁萦柔并没有把握能让他放下戒心,但是结果让她意外,曾尧逸没有对她说谎,而是老实地交代了那些重要文件的藏身之处,她其实不懂,既然是犯罪证据,为什麽他要一直保留著,不过她没有问出口。
梁萦柔不是铁石心肠的人,跟曾尧逸相处那麽多年,怎麽可能不动心,尤其是曾尧逸在她深受那麽大的创伤後,一直陪伴在左右,填补了心底的空缺,所以她选择了判刑可能最轻的罪证交了上去,她原先以为只会判他一年左右,足够她逃出他的势力范围,没想到最终判了三年
梁萦柔跟警方说好要在曾尧逸生日那天逮捕他,他的生日是大事,不少人会来道喜,而他被抓走,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只会在曾尧逸身上,没人会特别注意她,事实也确实如她所料。
梁萦柔到火车站的时候,售票处明确说不会再卖票,她从未买过火车票,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她是在月台坐了一整晚,买了第二天一大早的票离开。
梁萦柔坐在月台不敢睡觉,一会儿担心自己的安危,一会儿又担心曾尧逸的安危,她忍不住落泪,觉得自己很糟糕,只是世界上没有後悔药,她只能继续往前走,她的生活又一次发生了转折,而这一次没有人再陪著她,唯有孤身上路。
梁萦柔是被手机铃声给打断了回忆,她今天不想接任何电话,好在手机铃声响了一次後就没继续。
她双腿发麻地站起来,往身上涂抹沐浴露,然後开始用力地揉搓,把白嫩的皮肤搓得通红一片,让身体布满了疼痛,知道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才停下凶狠的动作。
梁萦柔披著浴巾走出房间,径自躺到了床上,她身体蜷缩成一团,脑袋里犹如翻江倒海,无数的画面开始闪过,实在曾尧逸让她想忘记的过去一一回笼。
<% END IF %>
☆、006
梁萦柔再次醒来发觉屋里黑暗一片,她摸索地下了床,才发现自己头重脚轻,摸了摸滚烫的额头,真的发烧了。
梁萦柔先是打开灯光,然後从柜子里翻出几粒感冒药,混著冰水吃了下去,开始找她的手机看时间,她不清楚自己到底睡了有多久。
手机上显示了好几个未接电话和未查看的信息,无不意外是师兄和师姐发来的,她礼貌地给两人回了信息,告诉他们自己因为发烧了,所以没接他们的电话。
梁萦柔的出租房他们都不知道,她是个不擅长交际的人,万一客人来了,她也不会招待,所以没透露过自己的住处,他们只能打她电话而已。
梁萦柔饥肠辘辘,冰箱里只剩鸡蛋,她从橱柜里拿出一包方便面,家里连开水都没有,她干脆放到锅里煮,顺便打了个鸡蛋进去。
梁萦柔的胃口不错,她开著电视,吃完了一整碗的泡面,总算填饱了五脏庙,便开始收拾她的蜗居,都说发烧出身汗就行了,她要干活来出汗了。
梁萦柔的身体还挺健康的,偶尔有点小痛小病,不过都很快康复,所以这次的发烧她也没放在心上。
房子很小,但是收拾起来依旧费力,梁萦柔把许多不用的东西都清理了出来,她有个不小的箱子,像是存封她的过去,里面有她父母的遗物,还有对於曾尧逸的回忆。
父母有再大的过错,梁萦柔都没有资格批判他们,因为对於她这个女儿,她的父母总是尽心尽力,可是那晚的记忆始终是梁萦柔的噩梦,在她往日的日子里总会反复播放。
梁父还不了钱,最终选择了自杀这条路,而梁母羞愧难忍,无法面对梁萦柔,同样选择了这条不归路,留下无依无靠的梁萦柔,她的亲戚没人愿意替他们家背负这麽多债务,自然不敢收留梁萦柔,谁知道高利贷会不会突然追上门来。
梁萦柔为了抵押父亲的债务,被迫留在了夜总会当服务员,因为她才十四岁,逃过了陪客的一截,可是难保他日她成年了,不会被逼著去陪那些男人。
在她当服务员的一段时间里,已经有不少人问她的价格,梁萦柔必须为自己打算,靠著当服务员的这点工资,她根本不可能从这里逃脱出来,之前的人生里她纯洁得像一张白纸,可是现在她已经学会了看人脸色做事。
而就在梁萦柔当服务员的几个月後,她碰见了曾尧逸,当天曾尧逸的包间里有不少人,所以叫的服务自然多,梁萦柔本来是不进包间服务,那些全都是贵客,有专门的服务员,恰好那天那个包间的服务员临时身体不适,确实找不到人了,才让梁萦柔临时盯上,她还记得那个经理千叮咛万嘱咐,让她千万要小心,不然这间夜总会都要关门。
梁萦柔心想关门了正好,她就可以逃出生天了,不过她年纪小,也只敢想象而已,那些高利贷势力遍布,可能她躲垃圾桶里,都会被揪出来。
梁萦柔端著昂贵的洋酒敲了敲门,里面喧闹不已,她在门口就感觉到耳朵刺痛了,梁萦柔没有听见任何应门声,所以走了进去,包间里装潢很高档,只是他们做得事情却糜烂得很,角落里正上演著真人秀,梁萦柔就怕长针眼,看也没敢看,就因为她这样一个微小的动作,手上不稳,把所有的酒都摔在了地上。
太大的动静让房间里所有人安静了下来,他们都目不转睛地盯著梁萦柔,而角落里一声低吼,宣告完事,那个男人走到梁萦柔面前,猥琐和地笑著:“长得还不错嘛,要不陪哥哥一晚,地上的酒我全部买单怎麽样?”
说实话,梁萦柔的脑袋已经完全懵了,她已经身背巨债,也不在乎地上这点酒钱,她是被在场人的目光给看得发寒战栗,也忘了该如何回话。
这时候角落里那个女人走到男人的身旁,嗲声嗲气地嗔怪道:“若哥,才跟人家好完,这会儿就看上这位小妹妹了啊?你坏死了。”
男人马上哄道:“我当然最爱你了。”
梁萦柔感觉自己像个小丑,站在这里供他们娱乐,眼里忍不住蓄满了泪水,不断地说著对不起。
自从来了这个夜总会,梁萦柔觉得自己不断在道歉,她从未这麽低声下气过,可是她的自尊并不值得,没必要为了它而让自己再遭苦难。
男人装模作样地说道:“哎呦呦……怎麽就哭了啊?心疼死哥哥了,来来,我抱抱。”
梁萦柔很慌乱,她无法接受这个陌生男人的拥抱,在场的人都一副看好戏的样子,她没有任何求救的对象,随著男人气味不断地离近,终於从人群里传来一声:“好了,别逗她了。”
梁萦柔这才注意到说话的人,他就是曾尧逸,曾尧逸一站起来,所有人都跟著站了起来,嬉闹的表情瞬间不见了,梁萦柔知道这人不简单。
曾尧逸走到梁萦柔的面前,面无表情地讲道:“再去拿同样的酒过来,钱我们会照付的。”
梁萦柔逃也似的的走出房间,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