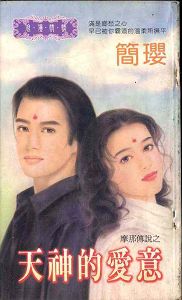又疼又香的爱情:无爱不欢-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人很响地放着屁或打着饱嗝,居然还有人挤出一小块地方打扑克,我掏出一本王小波的书读着,假装有学问,除去读读书,听听随身听,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我就是在思念顾卫北了。
当我度过了几十个小时到达顾卫北的面前时,顾卫北说,我好像接了一个民工。
学校里几乎空了,大家都回家过春节了。
宿舍里只有我们两个了。
我想起了冉红燕。
想起了她的呻吟声,但我发过誓,我要做处女,顾卫北的处女,一直到结婚。
他买来好多吃的东西,然后说,在这我们慢慢享受完它们,然后我带你去成都玩两天,再然后,我们打道回府。
可这里充满了危险,我坏笑着说,呵呵,顾卫北,想想吧,孤男寡女啊,我看,我还是去住旅馆吧。
顾卫北跳过来,离我极近,看着我说,林小白同学,你又多想了,我总以为你很纯洁,谁知道你比我还坏,你这么不相信自己吗?
夜晚来临了,窗外飘着细细的雪,我说,我冷。
顾卫北跳过来,然后说,让我为你取暖吧,我愿意当你的暧炉。
他的身体贴了过来,然后我们双眼看着对方,他说,妖精。我说你说什么,他笑着,看着我。
我们看了对方至少有十分钟,到最后我坚持不住就扑哧笑了。我发现我不如顾卫北有定力,他趴在我耳边说,林小白,为什么你这么迷人?你能给我个解释吗?我哈哈笑着,掩饰着慌乱,我怕他这样引诱我,你知道的,顾卫北,他是个非常非常有魅力的男生,他声音磁性,贴在我耳边的时候,我的心里毛茸茸的一片,很痒。
我说,我想改名,他一边喝着一瓶青岛啤酒一边吃着一个鸡腿说,那叫什么?
忍痒。
他扑哧就笑了,然后笑眯眯地说,我也想改名,我说你叫什么,他说,忍住。
那天晚上,一九九六年的寒假,我们各睡一张床,终于忍住。
半夜,他又跑过来,说太冷了,抱着我没有别的目的,只为取暖。
这是个很正当的理由,我往里面去了去,他却一下子抱住我,然后,他翻过身把我压在了下面。
我一下就把他踹下了床,也许我劲太大了,他哎哟一声。
我下床,开了灯,把他拉起来,他说,还真踹啊。他有点恼我,下手真狠啊,以为你对付流氓呢。
我替他揉着,吹着他刮破了的胳膊。
怎么补偿我?他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态度。
我撒着娇说,那亲亲你行吗?
他点了点头,这次算你亲我啊,你得主动。
我踮起脚,努力地缠上他,他伸手关了灯,我靠,又整这暧昧的事,我的呼吸急促起来,他伸手握着我的细腰,我的牙齿打着哆嗦。
你会亲嘴吗?他说,真笨,来,舌头伸过来。
这句话让我更是全身颤栗,我到底是被彻底亲了,用顾卫北的话说,我亲了林小白个体无完肤!那个吻,至少有半个小时,最后,我说,饶了我吧,太折磨人了,我嘴都累得慌了。
后来我想起两个词:孤男寡女、干柴烈火。可我们愣没烧起来!条件多好,时机也成熟了,可我们愣坚持住了。天亮以后顾卫北说,我都特崇拜我自己。
我说,我也是。
顾卫北说我们一直在创造奇迹,他说,诺贝尔奖应该颁我们一个,叫孤男寡女坚守贞节奖。
去你的吧,我说,你整天脑子里全想的什么啊。
可是,我心里想,唉,我们都是成人了,真是足够坚强,如果不是我坚持完美,大概早就坚持不住了。
和顾卫北缠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是甜蜜的,去吃早饭,来回喂饭,终于把吃早餐的人看烦了。有个女孩子瞪我们说,简直过分。顾卫北说,估计这孩子还是跑单帮的那种,不然,怎么会说出这种没水准的话来!
在公共汽车上,我们也会抱在一起,根本不管别人如何看,根本不管少儿宜不宜!
顾卫北说,这叫将不要脸进行到底!
完全同意,我说!
第二天我们去了成都,看那里燃放的烟火,并且泡了成都的茶馆,顾卫北说,这地方适合老两口住着,以后,我们就定居在成都吧,成都是最适合人类喝茶做爱修身养性的地方了。我们约定好了,等我们结婚时,我们再来看成都的烟火表演。
………………………………………
无爱不欢7(2)
………………………………………
也许我们说的将来太多了,或者说,总笃定我们会成为两口子,然后活到八十岁,结果中途出了岔口,再也继续不下去的时候谁也接受不了,这场爱情,到最后差点要了我的命。
回到苏州的我们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全国各地的同学们全回来了,大家说着大学里的新闻,更多的人有了恋爱经。再也没有学习的压力,终于可以活动活动筋骨了。这是我们班一个男生说的话。
大家一如既往叫我嫂子和弟妹,玩笑开得特别大,有人问顾卫北和我到了哪一步了?顾卫北说,唉,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
当然,我少不了到他家转转,而他也跟着我到了我们家,在两家父母都表示同意我们恋爱时,我们更觉得自己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过有一天顾卫北在枫桥上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的脸腾地红了。
他说,他妈妈千叮咛万嘱咐,学业第一,恋爱第二,还有,千万不要搞出意外来。
什么意外?我又傻傻地问他,是不是怕你这个花花公子变心?
他笑我弱智,我一下就明白了,脸腾就红了,他妈,是怕我怀孕!
那个寒假,不是他找我就是我找他,我们找来找去,寒假就过完了。
当然,其中有两天,我没有和他在一起。
因为周芬娜回来了,她从上海回来过年,这次见周芬娜,我明显感觉到她的变化,周芬娜,已经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她?
她在我家楼下喊我时,我伸出头去,看到了一个穿着朴素到极点的女生,是的,这是我第一次把女生这个词用在她身上。
她一袭白衣,黑的长发,似童话中的人物站在了我面前。我吓了一跳,因为她的形象和从前反差太大,从前的她,妖艳花哨,唯恐露得不多,但现在,她变得这样素净,从头到脚,几乎全是白色的,这倒让我无法适应了。
周芬娜好像彻底变了一个人,有脱胎换骨的感觉,装什么纯情,我想。那真是我最初的想法!
我跑下来,她安静地站在那里,看着我笑。
我也对她笑了。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从良了啊。我开了她的玩笑,她给了寻呼机号,但我一次也没有呼过她,我以为,她在上海一定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不纸醉金迷也会是夜夜笙歌,她本是那个江湖的人,不夜夜笙歌还能如何?半年多,我一直没和她联系过,好像她是另外世界的人了,倒是我和戴晓蕾,天天混在一起,戴晓蕾问起过周芬娜,我淡淡说了一句,去上海了,跟一个男人开夜总会去了。
对她,我很有些嗤之以鼻了。
一个没什么思想的人,一个贪图享受的人,一个用自己的身体来赚取生活费的人,我还能怎么看她?
但她一直拿我当朋友。我去北大半年,收到她几封信,字还是那样丑陋,可我没有给她回,一是因为正在和顾卫北热恋中,二是有戴晓蕾在身边附庸风雅,三是觉得她已经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了,所以,我连回都没回。
可我没想到,她对我还是这样好,拉着我的手去请我吃饭,她说,我赚了钱,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买给你。
我不想花她的钱,她赚钱不容易,她的钱,我还总觉得不干净似的。
我们一起去观前街吃饭,那条老街更繁华了,我们挑了一个小酒店,然后坐下来点菜。
我以为她还会请我喝酒,如前两次一样,喝五粮液,但这次,她只要了几个清淡的小菜,然后和我说了她的故事。
她说,这次,我确认自己遇到的是爱情。
我不相信她会有爱情,但她的眼里放射出醉人的迷茫,那是只有恋爱中的女子才会有的眼神,她点了一支烟,慢慢地和我说起了她的故事。
………………………………………
无爱不欢8(1)
………………………………………
她总是这样,似一只飞蛾,追逐着自己的爱情,无功而返的时候居多,可她这样锲而不舍地努力着。
那天晚上周芬娜对我说,她爱上了一个男人。
这次,是她的桃花劫。她吸一口烟说,你信吗林小白,人的一辈子总会遇到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就是生生世世,就是你等了又等的那个人,你为他生为他死都行,你信吗?
我说我当然信。我和顾卫北不就是这样吗?假如有人让我为顾卫北死,说这样可以让他活下来,那我可以立马去死。
这世界上只有顾卫北可以让我这样。后来,再也没有男人能让我为他两肋插刀了,因为我已经不再相信爱情了。
周芬娜告诉了我她的故事,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
周芬娜说觉得自己快绝望死了。
那天晚上,周芬娜一直在叙述中,在去上海之前,我已经和很多男人睡过觉了,然后学会了抽烟、打牌、花枝乱颤地和男人说黄色笑话,和张建邦到了上海以后,我们开了一个夜总会,夜夜纸醉金迷,然后,我遇到了姚小遥,你信命吗?反正我是信的。
跟着张建邦是因为他看中了我的机灵。他是来苏州谈买卖的,后来他来我的发廊洗头,那一天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不但和他聊天,他说生意上的事情我也跟着他说,请他放宽心,什么事都一样,车到山前必有路。
张建邦的生意很大,房地产、娱乐业,还卖汽车,所以,有人说,谁要是让张建邦看中了,就等于发了。
我就让张建邦看中了。他拍着我的手说,多大了?我说二十。我撒了谎,我才十八,我故意要把自己说得大些,这样人家用起我来就放心了。
跟我走吧,张建邦说,给我做老板娘,那个夜总会交给你行吗?你有一些股份,但必须和我一条心。
行,我说,我这就跟你走。
我来到了夜总会,来到夜总会的第二年,我真正二十岁这一年,我遇到了姚小遥。
然后,一切改变了。
周芬娜到这里又抽了一口烟,她的眼神迷茫,和我比起来,我是为爱情疯狂,她是为爱情痴迷。
我不是张建邦唯一的情人,我只是他众多情人中的一个。来到夜总会一年后,他对我厌倦了,可我经营夜总会是个天才,他舍不得让我走,所以,他说,继续吧,就算为了钱。
钱真是个好东西。有了钱我就有了自尊。
我不再鸟那些狗男人。我想跟他们睡就跟他们睡,不想跟他们就点一支烟在吧台前坐着,听着翻来覆去的爱情歌曲。我很爱听齐秦的歌,他一唱,我就想哭,他说不让你的眼泪陪我过夜。
没有男人的眼泪陪我过夜。
我自己的眼泪陪自己过夜。
然后我就遇到了姚小遥。
一袭白衣,风度翩翩的姚小遥。他和所有男人不一样,他不去包间,也不要个小姐。他来了,就坐在大厅里,安排好那些声色犬马的男人,不动声色地看着周围,我过去和他打招呼时,他总是爱理不理的。
我知道他看不起我。他身上有好闻的薄荷香味,他只穿白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