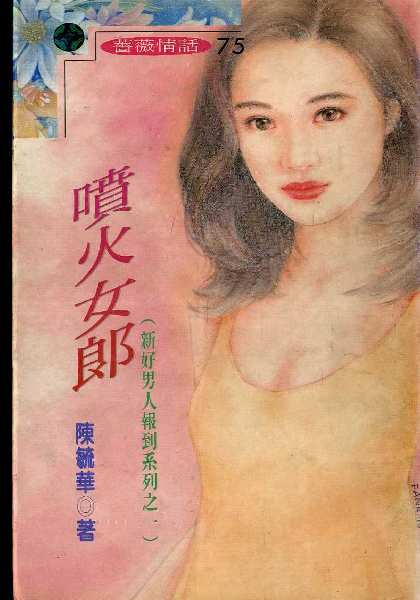嬉春女郎-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蛮拖上床,把他脏衣服脱了,给他擦洗身子。
妮娜帮这个赤膊躺直的男人洗脸。
蛮蛮面色铁青,睁着空洞的眼睛,看一样什么东西。
妮娜剥开粗大的香蕉,亲手送进蛮蛮嘴里。那张嘴傲慢地张开来,颇有绅士风度地动起腮帮子,并视妮娜的侍候为理所应当。
妮娜需要的不是回报,她渴望向蛮蛮付出。回报不是妮娜需要的,向蛮蛮付出是她渴望的。她饶有兴味地看,这个颓丧的男人进食。香蕉剥了一根又一根,蛮蛮大口吃着。他越是吃,就越是气,他越是吃,就越愤怒。
妮娜嘤咛一声,扑上去。她把红嫩的唇,印到他嘴上。他嘴上,印来一双红嫩的唇。
她闭上双眸。
在双眸紧闭的黑暗里,她发现自己就像秋叶一样,飘起来,像冰场上的舞女样,滑溜溜地转起来。突然,什么东西闷闷地响了一下,仿佛是梦里飘出的奇迹。她只觉天旋地转,臀部和腰部有巨痛。
她被一双大掌推倒在地。当她明白了怎么回事。
她就无力地撑起身子,娇弱地气喘着,柔弱的眼神瞪着那个一骨碌坐起的男人。那一骨碌坐起的男人被柔弱的眼神瞪着。蛮蛮弹簧般跳起,踢她,抽她耳光。她的世界开始下雪。她有点冷了。
“什么男人你不找,偏偏找上他。我打,我踢。”
“嘻嘻,你好好打吧。”
“你以为我不敢打。”
她身上开始布满了伤痕。可她不哭。乌溜溜的黑发忐忑不安地遮住了她的脸。她从发缝里,睁眼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她是从发缝里看到的。
蛮蛮一屁股坐到床上,开始大口大口地抽烟。
门窗紧闭的屋子里,青烟缭绕。妮娜握嘴,咳嗽起来。然后,她就嘻嘻地笑。她的笑很妩媚。
她脱下乌溜溜的闪光风衣,爬到蛮蛮脚边,伸手去抱他的腿,然后,顺着他的腿再往上爬。她爬上蛮蛮怀里,去抱他。她是一个这样害怕寂寞的女人。她又是这样一个需要男人拥抱的女人。
“蛮蛮,我是你的,你也是我的。我要你。”
蛮蛮把烟一扔,搓了搓大掌。这是一双美妙的大掌。这是一双春风得意的大掌。这双大掌真美妙呀,这双大掌真是春风得意呀。他扑上去,要了她。这个鸟男人,快活了一场,立刻爬起来,穿衣服。他照镜子,梳了一遍头发,提起椅上的旅行包就走。
“蛮蛮,你去哪里。”
“我这就回顺德去。”
妮娜脑子里嗡地一响。她眼泪都急出来了。急出来的是她的眼泪。
她匆忙地套上睡衣,鱼儿一样,溜下床来拉他。那个男人面朝大门站着,头也不回过来,头回不过来,也不回过头来。
“蛮蛮,不要走,我不能没有你。”
她生怕,他飞了,紧紧地从背后去抱他。她拼死力要留住她爱的人。
“求求你,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只要你留在我身边。”
蛮蛮突然伸出大掌,做了一个夸张、鲁蛮的动作,挣脱妮娜的手,夺门而去。他留下一句话。这句话,在以后的好几个年头,常常把妮娜从半夜里吓醒,然后,出一身汗。
“我对你已经没有兴趣了。”
“怦”地一响,冰冷的关门响传来。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她输得这样惨,男人的心是什么做的?好久,屋子里的女人瞪着眼,怔在那里,然后,她回到床上开始蒙头大睡。被窝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呜咽。她的呜咽断断续续。断断续续是她的呜咽。
夜色上来,上来了夜色。温柔的夜色。
街头,盈盈的暖风飘来飘去。霓虹灯亮起来,车灯亮起来。
一个着横纹红T恤的男子在这华灯初上的街头,踯躅。他孤单孤单的影子在街头,飘移。
暗巷里,一栋四层的握手楼。一条黑影爬上三层。
他摸出钥匙开了头道门。他进去,敲响一扇没有灯光、漆黑一团的房门。他轻轻地敲,然后他响亮地敲。没有人。
他在昏暗中闷了许久,好似困顿如牛。他点燃一支烟。昏暗中出现火光点点。
突然间他扔掉烟头,摸出钥匙费了许久的劲才找到钥匙孔。他开灯。灯开他。贼亮的灯给他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女人的私人世界。
这个私人世界很奇怪。
这个私人世界,嘿,这个私人世界乱套啦。看地上,横七竖八,都是用手摔下来、狠狠扔下来的。代表了愤怒和绝望。看桌上,一本巨幅影集打开来。一些照片,被剪刀修理出几何图形来。另一些照片,被放在手心里抓成了一团一块。照片上的人儿,荣幸地做了变形金刚。还有一面尺把高的镜框,痛苦地碎了,死了。这个代表愤怒和眼泪。女人的眼泪。
通常,女人流眼泪,男人都看得见。很少有真正的女人偷偷地哭。通常,男人流眼泪,女人都看不到。很少有真正的男人在人前大哭号淘。
床上,睡在床上的女人见灯亮了,立刻呜呜地哭起来。
她翻了一个身,面朝里。一头黑发比鸡窝乱。看不到她的脸。她的脸看不到。
“妮娜,你怎么了。”
妮娜哭得更响了。更响的是妮娜的哭。
被褥像活人样,突地弹跳起来,满枕黑发突地像活人样,飘起来。呜呜痛哭的女人做了一个夸张的动作,一扑,扑到山盼怀里。山盼顿觉自己半边脸湿了一片。
“山盼,连你也不要我了?”
第二十七节红脸 腥嘴
太阳热辣起来,热辣起来的是太阳。辛苦的人开始出汗。
今天,是五一节头日,厂里,只放一天假。一大早,山盼就被妮娜叫去,陪她。妮娜昨天刚从考场走出来,大战惹得她一身疲惫,满嘴饥渴。她要山盼去喂她,喂个饱和状态。一个人,若是长期地处于非饱和状态,日子就不好过了。
原本今天他有别的事,只是妮娜对他太重要。妮娜是他生命之航的舵手。他生命之航的舵手是妮娜。他自己的事再急,也要放一边先顾她。他怕她生气,怕她不理他,不再挂他。
妮娜最喜欢喝牛奶。她刚刚上街,一气买回一打牛奶,和山盼开荤。她坐在床上,要山盼用嘴哺到她嘴里。两人一边接吻,一边进食。红尘俗世,所有的烦全部的痛所有的伤都抛开。妮娜不眨眼地看着山盼,伸手,脱下衣服来。她第一次当着山盼的面,把青春亮到大白天里。她双乳直立起来,脸红起来。
她身上放出求爱的气味。那气味酒一样,醉人。'奇‘书‘网‘整。理提。供'山盼像喝了酒一样。
她把山盼推倒,扒他衣服骑上去,做爱。
床上人满头大汗。
山盼松松垮垮地走出来。松松垮垮走出来的是山盼。他搭上一辆摩托,让摩托车仔带他到广场去。他去广场等一个人。
姐弟俩他乡一见,分外亲切,一路上说说笑笑。山盼领着姐姐上自己宿舍里来,他先去超市买了些姐姐爱喝的椰子汁之类。山容抿着嘴,一言不发,听弟弟讲起初来石狮的悲喜遭际。他还提到席一虫,山容面色刷地苍白起来。这个名字对她而言,是一串鞭炮,点着了,会噼噼啪啪作响。她拉起山盼,去到附近一家排档吃饭,吃完,又同去商场买了两套入时衣裳,花钱配了一部手机,都是给弟弟的。
山盼自从“鸟枪换炮”,照见镜子里,惦着自己也有些份量了。他眉飞色舞起来。
下午,五点,她跟弟弟作别时,天降大雨。她满怀心事,从雨里湿湿地回厂来。
五月的夜晚,梧桐花香放过来,糯米条花放过香来。
一辆摩托打着光束,飘在山间公路上。飘得极快。匆匆,忙忙。忙忙地,匆匆地。
今天,是五月二日,夜空中布满星子。四野,响着五花八门的虫子叫,空气也在耳旁呼呼地响。
摩托进入无极农场,车手顾不得摘下头盔,下车便奔屋檐,拿起一根长竹竿,嘴里喊:“一虫,席一虫,你出来。”
原来,是个女子。一个年青的女子,一个既年青又害怕的女子,一个既害怕又执着的女子。屋子里,没有灯。
没有灯的屋子里,走出一个人来。摩托打出的光束照见那人穿的编织拖鞋,照见那人穿着白睡裤的腿。
年青女子扔了竹竿,竹竿呀地一响。狼犬并未蹦出来咬她。
“一虫哥,是你!”
她两步并做一步,跑上去,扑上去。
“我想你!”
一双手把她抱了起来。
她本能地挣扎了一下。这双有力的手,抱着她进屋。在屋子里,她被放上了床。抱她的人牛喘着,来扒她衣服。屋子里,漆黑一团。
“一虫,不要。”
她缩做一团。缩做一团的是她。她慌乱。她用嘴“发贴”。
“我迟早是你的人。你干嘛馋猫一样。”
那人却不应声,抱着她,吻她的颈啃她胸上。她晕了,湿润了。晕了她,湿润了她。她的嘴总算找到一只手。她三不知地咬下去。她咬得三不知。她的咬,像她的爱一样深。这一咬十分管用。那人痛叫,抱着手触电般,倒向一边。
山容溜下床来,整了整凌乱衣裳,飞车而去。飞车之前,她丢下一句话。
“嘻嘻,一虫,明天来看你。”
路上,山容感觉嘴上怪怪的,好似有液体在蠕蠕地动。嘴里腥腥的。腥腥的是她嘴里。她纳闷,她不解。回到镇上,家里,她飞奔。她开灯。她照镜子。镜子照她。她一瞪眼。她尖叫。她尖叫着捂嘴。她看自己的手。她又尖叫。她手上有血。她满嘴皆血渍!
她把席一虫咬坏啦。席一虫挂彩啦。
第二十八节花样·嗷叫
天气预报说,今晚到明天,晴天,卫星云图上,家乡的上空悬着一只笑眯眯的太阳。明天就是今天——5月3日。
山容一早醒了,听见屋外,只淅淅沥沥地响,原来是雨。她苦笑,天气预报也有失算之时。打开玻璃窗,她看到一旁怒放的粉红色蔷薇,那样地湿,不停地漏着水。
她想起,昨夜自己也漏了。这次例假差不多该告个段落了吧。昨夜替下卫生巾,上面一片夺目地红,都是血。她讨厌女人的月经,做男人多好。她天生是怕血的女子。
她突地撩起花睡衣来,对着镜子,照自己的乳房。那是一对梨形乳房。昨夜,被自己看中的男人碰过,它们就发生了奇妙的形象之变化。虽说仔细看去一只大一只小,但它们变得更好看了。
山容突又想起,昨夜星空下的事。不由眉头一皱,一朵疑云上来。
席一虫是谦谦君子,怎会随便唐突女人的?今年春节,看这个男人为人处世,实是时下男人之表率。她就觉得跟这个男人缠,可以一百个放心。只是昨夜,席一虫那馋猫一样,太突然了。他也不事先培养点情调出来,只是来蛮的。太不尊重人了。这席一虫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的是席一虫。他好似一辈子没碰过女人。
她骂了一句:“这个饿鬼,寂寞了吧。”
也许,他只是太寂寞。
毕竟,这个男人三十岁了,又是个结过婚沾过腥的人。她相信自己不会看错他。她一向很少看错一个男人的。
爱他,就给他好了。
扒了几口早饭,山容打扮得漂亮,骑着摩托,直奔无极农场。飘细雨。这雨如烟如乳的。这雨丝丝缕缕的。微微地发凉。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