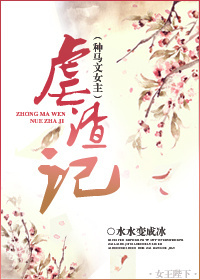梁山伯与马文才-第5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谢家诸人都没有说话。
梁山伯明白,此举会大大伤害世族的利益,恐怕难以推行。他正色道,“事已至此,若再不狠心改革,国将不国。”
谢玄扯开话题,“那也需时局安稳再议。你看当下情形,如何挽回我大晋王祚?”
好了,还是最核心的问题,又是内斗了。
“拖。”梁山伯低头看自己的手心,“桓温不敢背千古骂名,也惧怕世家大族联手相抗,如此便有拖。”
“万一他按捺不住,他手上可有荆扬精兵……”
“自枋头大败,他手上的大多是些残兵……”
谢琰忍不住插嘴道,“足以取京都。”
梁山伯冷冷道,“不足以守天下。”
谢玄出神地望着梁山伯沉静如水的侧脸,看他微润的嘴唇,心脏猛地一跳。
“桓温自北伐大败便失了民心,现下梁益仍有成汉后裔拥兵叛乱,海寇猖獗,又有邪教教众频频发难。若此时兴师动众,江南怕会陷入一片大乱。前秦又如何会放过大好时机?苻坚正守着仇池虎视眈眈,就等我们自己打起来了。”
谢琰又忍不住插嘴,“说不定他会先打张天锡……”
“张天锡纵情声色,不理朝政,前凉内部早已怨声载道,不足为惧。即便要打,挨不过前秦半个月。”梁山伯目光灼灼,那时竟是把所有人震慑住了,“苻坚马上会攻打梁益,此时不能乱了阵脚。桓温年事已高,我们拖得起,他却等不起了。”
谢玄一阵大骇,他所说的他也听谢安说起,只是不如他如此笃定。
谢瑶与他交换一个眼神,问道,“那之后呢?”
“荆扬平,天下和。”梁山伯抿了一口酒,怀疑自己是不是说得太多了。他不知道自己在历史上算是个什么角色。可万一本该注定他影响了这一切,万一谢家正是照着他所说的打压了桓家呢?那他不是自己把马文才推入火坑……罢了,也没有别的路可走。
“除了桓温,桓家还有桓豁为右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桓冲为振威将军,南中郎将,江州刺史。扬州、徐州、兖州、荆州、豫州、江州尽收囊中。”谢瑶言下之意是桓家势力庞大,怎容得荆扬相平?
“桓家内部貌合神离,桓温一去,其子与桓冲不和,又损元气。桓冲此人与其兄大不同,谢家想来是知道的。”
“那也不见得能让出扬州罢?”
梁山伯放下杯盏,“徐徐图之。习彝、朱序、王蕴可用。”
话已至此,梁山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可以挑几个原本是桓家阵营,然而又不是桓家人的过渡一下,如习、朱。只是为何提到王蕴,在座均是不解。不过再说以后的事也没什么用处,谢玄及时地把话题扯到当下。
直到宁康三年八月,孝武帝司马曜迎娶王蕴之女为后,谢安几番出请王蕴任徐兖二州刺史,谢玄说起多年前梁山伯早已断言“王蕴可用”,谢安自是唏嘘一番,愈发以上宾礼遇梁山伯。
“山伯方才说道前秦将攻梁益,有何良策?”
梁山伯苦笑,“梁益怕是守不住。不是我长他人志气,只是多年来在周家搜刮下百姓早已苦不堪言,因此频发暴动,冒充成汉后裔者众。苻坚收服仇池,我们早已失了先机。何况梁益边境一些少数民族本与氐人是一源,这人心向背……何况我们如今内政动荡,如若谢家出兵,说不定还有回旋之地。”
谢瑶和谢琰一起呵呵了一声。搞笑,他们手上还真是有多少兵力啊。
谢玄问道,“山伯似乎一语未尽?”
梁山伯看向谢玄的眼睛,“不错,之后仍有反击之时。待内政稍缓,兵力恢复,前秦狼子野心必然来攻。我军退守江淮南岸……”
谢琰不满道,“什么?放弃北岸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地?”
“山伯说得对,我也正有此意。”谢玄挥挥手,“北岸平原易攻难守,如若被逼,进退两难,不如以退为进,以擅长的水攻取胜。”
梁山伯提点道,“骑兵我们也要。”
谢玄沉吟,殊不知正是在这一刻萌生了组建大名鼎鼎的北府军的念头。
所以说,蝴蝶效应什么的,冥冥中自有天定。
在遥远的弋阳,夜色如冰风如刀,淮水南岸一群士兵呼喝着夜巡。绵延不绝的军营亮起点点烛火,四五个棚下篝火蹿得老高,煮了一锅又一锅杂烩,又不住烫着酒。
纵使是马文才一个月下来也吃吐了。日日俱是干饼,煮得稀巴烂的土豆芋头草草加些肉啊菜的,随便放些盐,酒也一股怪味道,下肚暖胃倒是有些作用。
以后梁山伯要是跟了他,也天天吃这些?
哼,前些日带这群大兵们出去打了一次猎,险些碰上氐人,可不被桓熙一阵臭骂。
“朱雍,”马文才叫了一声不远处的参谋,“前面那群人聚在一块儿干嘛呢?”
朱雍不好意思地摆摆手,溜了。
马文才叫了声“等等”,抓住他一起走过去,“臭小子,不会给我聚众赌博罢……”
“哎呀不是……”朱雍忙不迭解释。
马文才走到喧哗的中心,听见一阵一阵的叫好声,还有嘿哟嘿哟的喊声,“干嘛呢?起开!”他见围着一圈俱是看好戏的,更有衣衫不整者,一见到他都缩了缩脖子,只是嘻嘻哈哈的不肯让。
马文才恼了,一手提一个拎开,“干嘛?”
朱雍羞道,“文才……军妓,你没见过?”
马文才一愣,眼角瞥见中间那趴在地上衣衫凌乱的依稀是个女子,伏在她身上的男子完事了,草草擦了擦,“下一个!”
“这也……这也太不堪入目了罢。”马文才质问道,“你们往常都这样?”
“这些女的都是些罪犯的家眷,或是俘虏……也没什么……”
马文才一脚踹开一个解衣服的,“白天还没操够!还有力气?还有力气滚去蛙跳!”
朱雍连忙拉住他,“使不得使不得……这些当兵的整日没个消遣还了得,军规定的不准乱跑不准赌博,要这点都禁了谁还甘愿给你打仗呢。”
马文才气道,“打仗自然是为了保家卫国!还要什么消遣!”
“唉……这些人,无非都是些过不下去被拉来的……”朱雍挤挤眼,把他拉走了。
“那也不能……那些女子……”
朱雍拍拍他的肩膀,“军营里都是这样的。你还小。”
马文才忿忿地走回军帐,忽地一个小兵进来献殷勤:“今天逮住几个逃犯,大哥要寻些乐子不?”
马文才不耐道,“滚滚滚。”
“有个十三四的姑娘兄弟们还没碰过……”
马文才起身要踹。
“男孩子也有!啊!”胡垣飞出去。
马文才烦躁地坐下,无比地思念梁山伯。
63、
将近年关,梁山伯跟着柳逸舟在谢家住了月余,是时候告辞了。
谢玄一直闲居在家,想来是为了避嫌。梁山伯知道他的清净日子没多久了,他自己也明白,因此整日陪着谢瑍,只是可怜这孩子是当真没什么悟性,一直傻呆呆的,不过终于不再叫梁山伯娘。谢玄也难得,没有丝毫嫌弃,万般疼爱这独子。
真说起来,谢玄绝逼是温油攻妥妥儿的,心思细密又不黏人。
临走前,谢玄送了柳逸舟些许年货,叫人跟着马车送过去。又叫住梁山伯,表态道,“你先在那儿做个一两年,等时机到了……”
梁山伯不等他说完便点点头。
谢玄像个大哥哥一般摸了摸他的头,“好好干。”又抓住转身的梁山伯,犹豫道,“时常来看看瑍儿。”
“知道。”梁山伯笑起来。这些日谢玄好容易劝得谢瑍改了口,也不知道他真明白了没,改口之后又硬要叫他师傅。谢家倒不嫌他。
待他目送车轮辘辘远去,谢琰一没了外人,嘿嘿地不正经起来,“堂哥唉你可快三十了~”
“还没过年呢。”
“嘿嘿嘿嘿嘿老牛吃嫩草~”
谢玄面上一红,抬脚踹他。
谢瑶赶紧拦他,“好了好了他说的是我还不行吗。”
谢琰也不管他口无遮拦的,横竖他们那点破事家里还不知道么,因此反驳道,“我哥才大我三岁……哎哎……山伯可才十七八呢!”
谢玄被戳破心事笑了,“你们两个小蹄子,嘴里没个数的,你看我们可能么?”
“怎么不可能,我们亲兄弟不也……”
“打住打住赶紧打住,还要不要脸了。”
谢琰嘻嘻哈哈跑远了。人前是个翩翩公子,人后有大哥罩着就成了猴孩子。
马文才扛着几车的土特产回家,一进门就被吕氏拉到怀里,那叫一个心疼,连声说瘦了又说黑了。马文才回来后沉默了不少,有些憔悴。见过了家人,又应酬了一顿晚饭,抬脚就准备往庄家去。
马誉拦住他,不阴不阳地斥道,“回来第一天就往外跑什么意思?坐下。”
马文才已很久没听见老爹用这个语气说话,只得偃旗息鼓。
饭后陪着吕氏散了散步,闲话了一阵弋阳的日常起居,又被马誉叫到书房里去。
马誉遣散了下人,背手站着,看着墙上一幅山水画。那是马双效生前得意之作。马文才心里咯噔一声,隐约嗅了些什么。
马誉不转身,悠然问道,“你小时候就脾气大,四处惹事,有次给人堵在巷子里打,你大哥跑去救你,结果脑门给砸破了,你可记得?”
马文才手心微微出汗,“记得。”
“你七岁高烧不退,你哥守在你床头不吃不喝三个晚上,你可记得?”
“不敢忘。”
“那我问你,你哥的玉佩呢?”
马文才解下腰上的玉,“在呢。”
马誉转过身,大怒,“那你的呢?”
马文才不语。
“你……你和那小子果然!我就知道……”马誉气得直喘,在屋内来回踱步,“我不管你怎么想的,爱怎么玩随你,这家传玉佩也是随便送的!明日就给我取回来!”
“送了人的,哪里还能取回来?”
“叫你取回来!听不懂是不是!”马誉气得双眼发红。
“好罢。”马文才懒怠下来,“爹,我不是玩玩的。”
“你……你什么意思?”马誉气呼呼地瞪着他,又思及他近些年的成长,松下口气来,“罢了,罢了,你做得小心些,别让人捕风捉影了。”想来马誉仍是没放在心上。
马文才很想说我是要和他过一辈子的,又怕马誉受不住,因此踌躇了一会儿没说话。见马誉没什么气了转身准备离去。
“等等,你的佛珠总在罢?”
“嗯嗯。”马文才随口应了,转身开溜,马上吩咐马兴到城隍庙里求个长得差不多的佛珠来,叫人刻上他的名字,以免以后马誉生疑。
第二日马文才终于见了梁山伯,心心念念了两个月,见面时他鼻尖都有点酸。马文才又壮实了不少,看得梁山伯心痒痒。马文才又何尝不是,日思夜想了多少天,根本把持不住,直接把人往车上拐,往城郊的客栈去。
“不去你家啊?”梁山伯知道他们要去开房了,想来马文才会更加没完没了,禁不住有些紧张。
“我爹好像有点知道了……”
“他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