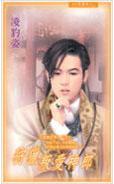叛-第8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如今绝对不能主动去找胡灵,我一主动那就陷入局面的被动,与其我自己傻了吧唧地到处去找胡灵,还不如让胡灵来自动找我。整个事情无论真相到底如何,必然胡灵是始作俑者,她每次都会在有必要出现的情况下出现。要想化被动为主动,我就得把胡灵给钓出来。
可什么情况才能令她认为有必要出现了呢?很简单,这就如同钓鱼,现在不管胡灵是不是真的爱上我了,只要她想玩我想把我逗猴儿耍,那么我在她眼里就如同一条鱼,她会丢下诱饵,诱惑我或者左右我的下一步思维;可是她有这想法之后,那么她也就成了我的一条鱼,只要我丢的诱饵合适,那么她也会出现的。
我用来钓胡灵的诱饵又是什么呢?更简单了,那就是我自己。我把自己做饵,而且啊,我这饵还必须带点霉变,清新爽口的诱饵对胡灵这般古灵精怪加变态的人无效,必须带些臭味,必须全身长满绿毛。只有霉变的诱饵才能钓出她这条有怪癖的怪鱼。
我在广州芳村租了一套一房一厅,芳村的租屋和深圳并无二异,小姐多二奶多无业游民多。兰姐和樊玉极力劝阻我不要去芳村租房子,可我还是选择了这里,而且我把对面的那套房也租了下来,我托兰姐买了三个针孔摄像镜头,我将对面那房门上的猫眼给取了下来,安上一个针孔,然后又在自己住的房子客厅里卧室里安上一个。我为什么这么做?我确信胡灵他们一定会再次派人来安装偷录窃听设备,我要逮住一两个,把他们揍一顿,然后逼问他们,这样我才能师出有名地再去找杭夕,如有可能我就直接去香港。我很留心身后是否有人跟踪我,可我一直没有发现过,七天之后我也没有从录下的针孔摄影里发现半点蛛丝马迹,但是被跟踪的感觉却越发强烈,我一定要抓住他们。
楼下就有一间麻将馆,不两天我就和他们混熟了,他们很热情地邀我打牌,我也不客气地赢了点。我和兰姐樊玉也又玩过一两次,却玩得寡然无味,她们也时常打牌,却不准我上桌,只准我买马,理由我记得住牌。我在他们的圈子里出了大名,家仔自己在赌场已经输得一塌糊涂,几次想约我再去,我都拒绝了,不是我不去,而是时候未到。
这里鸡店林立,店里总是照着暗红色的灯,招牌上必然是写着“松骨按摩推油”等等,店门口小姐们抛开她们的长相不讲,个个衣着裸露,打扮妖艳,言语更是大胆,每每我从她们门口路过时总是遭遇如此的轰炸——“帅哥,进来坐坐啊!”“靓仔,来,妹妹陪你聊天。”“帅哥,轻松轻松不?很便宜的。”“来来,靓仔,进来吧,不要你钱。”。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甚至还有老板娘试图拉我进去。村里的治安巡逻大队虽然每日里拿着电棒到处走来走去,基本上都是摆设,我还见过几个队员和一些小姐们打情骂俏着,警察自然也是有的,派出所就在不远处,可他们对小姐们视而不见,我想他们一定是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些小姐们都是在为人民服务,为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作贡献,为减少社会强奸案的发生立下汗马功劳,为他们自己的腰包鼓囊程度建立了不朽功勋。
在芳村住了十天,除了认识了那些热爱麻将的附近七八位二奶并得到她们眼神和言语的暧昧暗示外,我一无所获。这天下午我正在午睡,突然被隔壁那栋楼的里叫骂声吵醒,趴在窗户上向外看去,看到一男一女正在客厅里挥动拳脚,那男的把那女的打得鬼哭狼嚎,细细一听,原来是那个香港男人感染了性病,他自诉他根本没在外乱来过,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他的二奶有偷情嫌疑,女的极力争辩说她规规矩矩,那男的就大骂说“你他妈的还规矩,以前就不会做鸡了!老子看得起你,才和你交朋友,你还敢背叛老子,……”,接着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抓住那女的头发狂抽耳光,把那女的鼻血都打出来了。
我看不下去,拿起电话报告110,110 询问了详细地址。我随即冲那厮喊道:喂,警察来了,你把门关好。这家伙闻声立即向我看来,冲过去把窗帘拉上,我听到他嘴里叫骂了一阵后就低声说“不准对警察说,说了你就给我滚!”,那女的呜呜哭声微弱下来。
我摇摇头,出门下楼,去了一家比较正规的理发店洗头,然后去小饭馆吃了一碗桂林米粉,正滋滋有味地吃着的时候,却听到隔壁桌的一对男女在说流产打胎的事,那女的指责那男的不晓得疼她,结果弄得她去流产。那男的说哪个女的不流几次产,干这号子事就得有随时怀孕的准备。那女的就嗔道你不会戴套子啊。男的摇头说戴套还有个屁味?那还不如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那女的把他打了一下,说杜蕾丝的牌子很不错,还有浮点。这男的浪笑起来,说浮点算个屁啊,我呆会去买荧光的。
强烈的呕意顿时涌上来,我慌不迭地丢下五块钱逃跑。无聊啊,我一路走去,街上一溜都是大大小小的乳房,黑白不一的大腿,肥瘦不均的腰肢,黑黄颜色的头发,形状各异的屁股,他们彼此的五官面目我却看不清了。我来到公共汽车站台,一辆小巴开过来,我腾地跳上车,见司机抽烟,我也不客气地点了一根,坐在身旁的一个二十来岁女孩却厌恶地皱起了眉头,还不时地用手在鼻子前扇。
坐了三站路,我又下车,在一间衣服店里买了条裤子,又买了件T恤,T恤是梦特娇,总共不到两百元,都他娘的是假货,纯粹是想去买假货,一个脏不拉西的小男孩瞪着热情的大眼睛手里拿着几张碟,对我说大哥哥,买碟吗?我看这小男孩长得满可爱,便问都有什么碟?他急忙道最新美国大片世界大战,大哥哥你要毛片也有,最清晰的,还有人兽交。
我心一痛,就对他说道毛片多少钱一张?你有多少?你都给我拿来。小男孩闻声不喜反恐,道大哥哥,你不是在骗我吧,你是不是文化局的警察?你都要?我们有几百张呢!
我点头说我不是警察,你都拿来吧,我全要了。小男孩说你全要的话,我给你打折,五块一张,好不好?我说好。小男孩转转眼睛又道不过大哥哥,你要这么多,我做不了主,我把我大哥二哥叫来,好不好?
我摸摸小男孩的头,说不好,我就买你带来的这些吧,你数数有多少。小男孩忙拉着我走到一处树荫下,麻利地从随身小挎包里掏出一把,指着那碟片上淫秽的性器官性动作特写道:大哥哥,你看看,这是日本的,这是美国的,黑人和白人,这是同性恋的,这是泰国人妖的,这是好多人一起的,这是在娱乐场所偷拍的……
我一把将碟片全抓过来,从裤袋里抽出几张票子向他手里一塞,转身就走。小男孩熟练地检测着票子的真假,然后冲着我背影大声道大哥哥,谢谢你了!
我走了几百米后,走到一处十字路口,突然抓起这些碟片对着路口上空使劲一抛,顿时碟片象天女散花那样飞旋着坠落,我对这十字路口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人群,痛痛快快地大喊道:我操你祖宗啊!活该!
我已经记不得我是何时第一次看这淫秽的色情影碟,我只记得当时看得心潮澎湃,小弟弟软了又硬,硬了又软。再到后来这些影碟我就再也没有任何兴趣来看。现在这个小男孩最多不超过十二岁,他比我强,居然能用如此专业的口气向我描绘每一张碟片的内容提要,我无法判断他是对此麻木还是对此无知,同样地我也无法判断这周围的世界对此麻木还是对此无知。
其实我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整个世界都病了,病殃殃的,病到了骨子里去,我却还穷极无聊地在无法解释的某个黄金分割线上思考为什么得病。
又是一个星期过去,我始终没有从自己安装的针孔摄像机里发现有进出过我房间的人影,也从没在房间里发现有被人隐秘安装的镜头或者窃听器,更没从周围人群中发现有谁是跟踪监视我的人,日子就这么麻木地过着,我不禁有些怀疑我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我曾特意找到一间专业的手机维修铺,我写了一张纸条交给他,纸条上说:请你不要说任何话,直接把我手机拆开,看看里面是否有不属于手机原有的零件,如果有,就请指给我看,我给你两百块报酬。维修师父纳闷地看着我,我把两百块放在他面前,他也不问缘由了,打开手机后,果然看到了一个小扣子一样的东西,他指着这东西,并在纸上写道这不是手机里的,是被人放进去并接在电路上。
这就是王先生所说的被人安插在我手机的窃听器,我的声音随时都会发射出去,安装这样的窃听器需要极专业的技术,这又证明我的确被监视着。
又是数天过后,我走进了期货公司,我拿出二十万开户炒作金属期货,一个经纪人屁颠屁颠地围着我转,整天向我展示他的金融才华,指点着图形做什么技术分析,向我灌输哪个哪个老板一天赚几十万上百万,还吹嘘他最高纪录曾经一手单赚了十八万,那老板给他两万块红包。他满心希望我可以授权他下单,希望我可以每天做上个几十手单。可我愣是一个星期一笔单都不下,我不是二楞子,深知一切股票期货的经纪人都是王八蛋,他们赚取佣金的代价就是你的资金缩水。
我并没有其他才华,短暂而又匆忙的大学研究生时期里我并没有学到多少有用的知识,且不说自己专业物理学,我除了赌和泡女人,我其实一无是处。我现在只不过是找个地方过日,等待跟踪我的人露出行迹,等待胡灵他们因忍受不了我的无聊而不得不帮我安排新的节目。
我很清楚,胡灵他们要帮我安排节目也必然是赌和女人,可我的确不想再进赌场,而我对女人又实在提不起半点兴趣,兰姐樊玉好几次又要和我风流,我也知道通过樊玉再搭上她那在胡灵手下集团担任董事的香港男人,并借此辗转进入香港,接近胡灵,未尝不是一条路子,可我觉得这样的法子太臭。我推辞她们说我在外玩小姐,不幸感染了尖锐湿疣和硬下疳,目前正在治疗,要想浪漫只能等我病治好以后再说。她俩直骂我下流,我回答说她们错了,我这才叫上流。
如果胡灵真喜欢我,那么她就应该不会安排女人来捉弄我,相反她会对一切接近我的女人吃醋。她们那些人安排的节目毫无疑问就是要刺激我的情绪,把我逼向一个两难选择的境地,然后再用我的两难选择来开赌。现在我兜里有钱,我又不玩女人,我有理由认为她最佳的节目安排就是诱导我去赌,而期货股票就是比较有新意的赌博方式。
又是三天过后,那期货公司来了个新经纪人,这新经纪人据说有三四年从业经验了,经济学本科,公司老总安排他来负责我和另外一个客户的资金运作。这人名字搞笑,叫游日吾,言语木讷,电脑操作却相当灵活。
我笑着对他说:你的名字中英结合,游日吾,YOU日我。男人叫你名字的话就有玻璃嫌疑,女人叫你名字却显然是想勾引你。
他笑笑说:甄生,你说笑了。
他在这半天中为另一个客户下两手单,赚了四万,分析行情头头是道,明显不是一般的水平,我猜想他操作过大资金,可他却到这小公司来做经纪人。当我故意问他有关世界金融行情时,他的评述也和我在网络上搜寻到的最新观点无异。我心想:他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