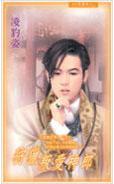叛-第6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邵刚没骗我,凤姐是有病,那么也就基本上不可能是他或者华家人在检查爱滋时做手脚,可这个推论到底又有几分可靠呢?
我没有告诉凤姐关于陆子亨自杀的事情,当然她问起了陆子亨和我是不是去做了检查,我忍着痛说做了检查,我和他都没感染。我听到她长长地舒了口气,而后挤出极其难看的笑容对我说:甄甄,真对不起,我想告诉你们,可我又不知道怎么开口,我当时想如果陆子亨他感染了,那他是罪有应得,谁叫他有了那么爱他的女朋友还要到外玩女人?可你呢,唉,我是想,如果你有了的话,那么我下黄泉也就有伴了,我和你就能在一起了。
我本想痛斥她是意图征服我的情感,意图得到我的情感,可她都那样了,我还斥她做什么?且让她抱着美好心思过这“不是囚禁,胜似囚禁”的日子罢!
我站起身子,对她说:凤姐,我们俩,叫做有缘却无份,男人女人啊,真想在一起的话,除了有缘结识,还得需要福分的。
凤姐喃喃自语:是啊,是啊,福分,人都是要福分的,我真傻,真的,我真傻。
我上前摸摸她的头,替她擦去眼泪,最后道:我走了,你好好保重吧,以后别看这些恐怖电影电视,多看看开心的。嗯,如果你心里真的很烦,那就去信佛吧,听说佛教可以帮人解度人生困厄烦恼忧愁。
凤姐哇地狂哭起来,想抱我却又不敢伸手,我心黯然。
我把门打开,她母亲满脸是泪的站在门口,旁边还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这可能是她父亲吧。我掏出三千块塞给她母亲,道:我走了,不打扰你们了。
下楼后,那些狼狗土狗还在对我吠叫,她父亲一阵吆喝,那狗们立刻不吱声,我出了院门,她父亲陪着我,我走了十几米,回头看见她就站在阳台上双手捂脸。
她父亲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在我上车的那一刻,这位老人终于哭出声来,道:小伙子啊,你是第一个来看凤妹子的好人!
第四卷 迎着风 第九章 狼皮羊皮都是皮(中)
从凤姐老家回到深圳的途中,我一直感觉有人在跟着,可当我猛地回头寻找时却又看不出有半点异样,在那小乡镇如此,在县城如此,到了火车上这种感觉异常强烈。火车上我坐的是卧铺,车厢里一溜过去都是铺位,旅客们不是坐在床铺上就是坐在过道的小凳子上,我装着去上厕所或去车厢接缝处抽烟的样子,扫看着旅客们的脸,却又看不出哪个有嫌疑。可我就是感觉有人正在跟踪着我。
火车到了广州,那些到广州站下车的旅客都下了,我看着表,在快要到点开车的时候,我突然拎着包就跑下车,然后站在水泥柱后面观察还有哪个要跟着我下来,我看到一个人疾步走到车厢门口,却又停住了脚步,我旋即再向车上冲去,他见我上来了,掏出烟点火,摆出一副抽烟的样子。
他二十八九岁,相貌普通,身材中等,难道是他在跟踪我?不像啊,我在凤姐家乡的小镇上或小镇去县城的汽车上也没见过。我冷笑着站在他面前,也掏出烟对他道:朋友,借个火。
他把烟头递给我,我点燃烟后道:朋友,去哪?
他面无表情地说深圳。我再次道:朋友是做生意的还是上班的?这次从哪里过来啊?
他瞄了我一眼,冷冰冰地道出差。然后转身就进入厕所。我冷笑着想:老子就不信查不出你从哪里上车的!操你妈,只要发现你是和我一个站上的车,老子要你好看!
我找到车厢列车员,给她两百小费,问了这家伙车票,他的卧铺票是后来补的,上车比我晚。我不禁再次问自己:难道我真神经过敏了么?
再次回到租屋,虽是暑日却觉得屋里冷清无比。我一边冲凉一边想:凤姐有病,子亨不带套,子亨得了病,我没病,可我却被检查出了病,一个医院检查可能会出错,可三家医院检查都出错的话那就只能证明一个事实,那就是的确是有人在故意陷害我,那么子亨自杀的责任与这个做局陷害我的人有没关系呢?必定是有的!
我已经和华菱闹成这样,如果是她家人做局,那么现在就已经没有继续做局的必要。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去这三家医院把这事调查个明明白白。可那三份血检报告呢?唉,当场就被陆子亨给撕了啊!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去找那些做检查的医生。
我随即去找这三家医院的那几个医生,搏爱医院当时还有个医生特地找我谈话,可我却找不到他了,我询问其他医生,其他医生都说没这个人,我再找当时带我去见这医生的那个护士,其他医生却告知我那个护士早在半个多月前就已经辞职,现在不知去向。
我立刻又去深圳人民医院,找到医院负责人要求他们追查我被误检的原因,他们问我这血检报告在哪拿的,我说是检验室的一个护士给我的,而且那护士还要带我去见主治医生,我见是阳性就走了。医院负责人要我拿出那次的检验报告,我说撕了,他随即派工作人员带我去查存根和找那护士。可存根上却没有我和陆子亨做过血检的记录,而那护士根本就没这个人!
这工作人员认定我意图敲诈医院,他嗤笑我不要用这么拙劣的花招。我火冒三丈,直想掐住他脖子,可我不得不忍着,请求他再去查阅那日的电脑收费记录。他不允,说他没权。我本还想缠着医院负责人来同意调查此事,可我却放弃了,我甚至连再去第三家医院调查的念头都取消了,就算我找到了那些人又有何用?最多能问出来他们是被雇佣的,真正的做局者我能查访到么?对方既然是做局,那么他们就一定会消除掉做局的痕迹,怎么会让我找到局的明显突破口呢?除非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局的漏洞或者软肋。
我突然迫切地想知道巫菡到底是不是也感染了爱滋。
我买了四瓶啤酒和一些卤菜,还有香纸钱,再次来到原来的大楼租处,我将酒打开,放一瓶在我对面,又多点上一根烟放上,然后我举酒和那瓶酒碰一下后道:兄弟,烟给你点上了,酒给你开了,知道么,好想再和你喝一次酒,再一起吃顿饭,再一起泡一次一夜情,唉,一夜情还是别泡了,我们就喝酒吃饭抽烟吧,还记得我们半夜没烟抽了,捡烟屁股抽吗?你一定记得的,伪处那家伙在自己枕头下发现了一根被压扁的烟,馋得我直流口水啊!
我又为他点上一根烟,我不停地说着我和他的往事,说着我们闹过的笑话,最后我说道:你有病,你也别怪凤姐了,她够惨了,活得生不如死。我没病,你心里啊,也千万别不平衡,老天爷就是这么不公平的,你认命了,其实我也认命了,命就命吧,命就是那个样。子亨,我怎么也理解不了,那些个骚逼为何要对我做局,可你放心我一定会查下去,把一切查得水落石出。另外呢,许素梅一直没联系过我,她那些朋友可能没对她说你走了,或者她还在日本快活。我知道你没有告诉他你有病,我现在在犹豫,要不要告诉她这一切呢?如果我告诉她了,那么她就会更加恨你,可我不告诉她呢,我的良心啊又不安宁,这样吧,我们来投硬币做个决定,有字面就表示你同意我告诉她,花面就是你不同意,好不好?
我仰头将酒喝尽,随即在身上摸出一枚一元硬币,右手食指勾起来,大拇指掐在食指上,硬币放在大拇指指甲上,用力对空一弹,硬币叮地撞在天花板上,啪地落在地板上,弹跳几下后,是花面。
我叹了口气道好吧,既然你不愿意,那我就听你的了。
这间房子已经再无保留的必要,我准备退掉,把押金拿回来。我仔细地整理起物品来,在一堆旧杂志里我发现了那些冥纸。这些冥纸我记得,就是胡灵塞进我腰包里的,我记得她给了我好多张,那上面的币值是1后面很多零,而陆子亨的冥纸则是她同伙给的,只给了一张,币值却是零!
我猛然醒了!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冥纸都有一个币值,乡野山间的那种纸钱,一个一个的,那是一枚枚的铜钱,现在流行起来的印刷冥币,上面也全部有币值,为何给我的冥纸有币值,而给陆子亨的却没有呢?!莫非这就是在暗示陆子亨一钱不值,下场就是死?!
我哈哈狂笑起来,这些冥纸啊,我得收好,一张一张我都要收好的。
我随即打电话给房东说要退房。房东也听闻了陆子亨从这房间跳下去的事,对我脸色很不好看,嘟嘟囔囔说了好多怪话,我咧嘴狞笑道:你妈拉个比的,再他妈鸡巴说的,老子把你从这里扔下去,摔死你狗日的!
他被我抽跳的面部肌肉吓坏了,慌不迭地把钱数给了我。我提着装有杂物的塑料袋走了。
我把东西扔在皇岗租屋里,随即打车来到古董市场,直奔那古泉专铺,那老板一见我立刻迎了上来,满脸含笑地说老板,好久没见了。我点点头道再不见就见不着了。他被我说得一愣,笑道老板你真会开玩笑,来坐,坐,饮茶。
胡灵给的那块金币就悬挂在我脖子上,我每走一步,金币就会轻轻撞我胸脯一下,尤其是当我俯下身子再站直的时候,那金币就会撞在我的胸骨上。类似的每一次撞击都会令我想起她。可同样的,我也会想起我所经历的事。
今天,我要卖了它!
我将金币从脖子上取下来,放在他面前,说给钱吧。他登时惊喜地道真卖?你想通了?我咬咬牙说三十二万,上次你说的那个数,去银行转帐。他立即一把攫过金币,紧紧握在手上,直点头道好好,马上去,马上去!你等我拿卡。
他和我来到工商银行,把钱转给了我,我随即将十万汇到母亲账上,又打陆子亨家里的电话,询问他父亲工行存折号码,再给他家汇过去五万。我又办了一张新存折新卡,把这些钱又转到新卡上,我不能把自己的存折卡帐号让任何人知道,我清楚胡灵那伙人能盗取卡的密码。
那古泉铺老板在银行里拿出金币托在手上,道:小伙子,再看一眼吧,明天可就看不到了,去香港了。
这金币,我很想留着它天天在我身上,让它每时每刻都和着我的心跳。可我必须卖,老子没钱,老子不想再把这金币这些人当成是个东西!天理不容啊,一次又一次的真相假象,重重阻隔着我透视的视线,现在我完全确定了,这些事就是她们对我所做的天理不容的事!老子不把这狗屎一样的金币变成白花花的银子,老子是傻逼啊!
当我把所有银行帐务都搞定后,我又来到古泉铺,我找那老板要那个想买金币的香港老人的电话,他说不方便给。我笑了,道那我们以后再联系吧,我要是还有好东西啊,保证第一时间卖给你,只要你价钱出得合适。
我取出两万块,直奔水库新村里地下赌场,赌场正开着,里头还有不少我见过的赌客,我嘻嘻哈哈地和他们赌着,到天黑的时候我赢了九千,随后我又到麻将馆,找上两个有出千嫌疑的家伙打麻将,打得很小,十块一注,他们出千初始还有些小心翼翼,担心被我发觉,可我装作不知道,后来他们就明目张胆了,我笑眯眯地看着他们,另一个对局的家伙是个只晓得低头打牌的,我问他输了多少,他说输了九百二,我说我输了一千。
重新开局摸牌,就在一个家伙用抓换墩俗称推火车的手法换牌时,我一把抓住他双手,此时他两只手上都抓了四张牌,他出千成了铁证,他想抵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