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早就听说他跟家里关系不太好,不过傅守瑜不知道具体原因。意识到自己失言了,想说点什么来弥补一下,沈阅却轻轻松松地用别的话题岔开了。傅守瑜看看他的神色,没有异常,嘴上说是无所谓,恐怕心里没那么看得开。傅守瑜滥好人基因显性表达,抖起全副哄这可怜孩子高兴。
找点事情来做,也就不会再去胡思乱想了。
傅守瑜喜静,很少来太吵闹的地方,刚一进去就被暴躁的音乐和沉闷的空气给冲得晕头转向,找准门的方向正准备逃命,被沈阅一把拖住。
幸好没几步就进了包厢,门一关,外界的喧嚣也随之远去,不适感得到缓解。
沈阅要了啤酒、果盘和开心果,转过身来问傅守瑜要什么。
傅守瑜问:“有果汁吗?”
服务员刚想说有,沈阅插嘴:“果汁没有,有果啤。”一点酒精都不沾,没意思透了。
傅守瑜点点头,果啤也行。
一曲终了,傅守瑜跌回沙发,下一首不是他点的,把话筒还给沈阅。口渴得厉害,也不管到底是什么了,抓起桌上的瓶子就喝。
沈阅刚唱了没两句,手机响,没看屏幕直接接听。
傅守瑜朦朦胧胧间就见他捂着耳朵吼:“你管不着!”吼完挂电话,扔手机,傅守瑜撑起眼皮问:“谁啊?”
沈阅“哼”了一声,说:“王八蛋。”
傅守瑜呵呵笑:“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骂我呢。”
沈阅耸耸肩把这首歌跳掉,重点,提前,开唱。
到后来都顶不住了,靠在沙发上睡,凌晨六点退了包厢出来,路灯还亮着,完全没有天亮的迹象。傅守瑜和沈阅互相搀扶往学校走,沈阅一路哈欠不断居然还坚持着一直把傅守瑜送到宿舍楼下。
傅守瑜一觉睡到午后,醒来才发现手机没电了,插着电源开机,一下涌进N条短信,提示他昨晚错过了曾钊多少个电话,头痛欲裂,傅守瑜扔了手机倒回床上缩进被子里。
第四章
再度醒来的时候,傅守瑜只觉得浑身乏力,窗外天光黯淡,也不知道几点了。抬起手背探了探额头,有点发烫,呼吸困难,喉咙肿痛,挣扎着下了床,在抽屉里翻出阿莫西林,一口气吞了四粒,又昏昏沉沉地爬回床上。
傍晚七点的时候,傅母打来电话,再次确定归期。
傅守瑜买的是后天上午的火车票,还有一天的时间养精蓄锐,回到家一定不能让老人孩子担惊受怕。
他那三岁的女儿傅宝宝在一旁闹着要跟爸爸说话,两手捧着话筒,小丫头软娇娇地用方言唤:“爸爸~”
傅守瑜眼泪都快下来了,吸吸鼻子答应:“哎!”
小丫头听出不对劲,问:“爸爸,你生病了?”
傅守瑜说:“没有。”
小丫头奶声奶气地叮嘱:“生病了要赶紧吃药,不吃药就送去医院打针,打针好痛的!爸爸怕不怕?”
傅守瑜对着话筒傻兮兮地笑:“爸爸不怕!宝宝怕吗?”
小丫头一挺胸脯,学她爸爸的口气说:“宝宝也不怕!”
“宝宝真勇敢!”
傅母把话筒挪开:“好啦,大后天就回来了,有什么话回来再说。”又叮嘱:“瑜瑜啊,你感冒了要记得按时吃药,那么大的人了,不要让女儿来提醒你。”
傅守瑜乖巧地笑:“我没感冒,就是天冷鼻炎犯了,您又不是不知道。”
刚放下电话,手机又响了,又是沈阅,问:“还好吧?”
傅守瑜裹着被子像个蝉蛹,瓮声瓮气地说:“还好。”
“出来吃饭。”
“不去了。”
“你声音不对,感冒啦?”
“嗯,有点。”
“那我们去喝粥。”
“算了吧,我是真不想动。我已经吃了药了,你让我睡一会儿就好。”
“那行,你好好休息吧。”沈阅吧嗒挂了电话。
傅守瑜觉得冷,抱着被子抖啊抖。
又睡了不知道多久,隐约听到门铃响,实在不想动,便盼着那人放弃,哪知一直不得清净,门铃按完了又开始捶门,跟强盗似的,再这么下去恐怕整栋楼都会被惊动。傅守瑜无奈地披衣起床。
沈阅拎了一大堆东西,进门就找厨房:“我买了粥、饼和小菜,还是热的,盛出来就能吃。碗在哪儿,盘子在哪儿?”
傅守瑜闻见食物的味道心里就不舒服,苦着脸看沈阅进进出出,一点不把自己当外人。
沈阅一边摆餐桌一边打趣:“哎,我说您老人家不是有喜了吧?”
傅守瑜翻翻白眼,懒得理他,转身回了卧室。
不一会儿沈阅端着碗进来了,说:“你好歹吃点东西啊,就这么饿着病怎么会好?”
傅守瑜气若游丝:“我是真不想吃,你别管我。”
“没人性的就不管你,”沈阅走到床边伸手摸额头,抽了口气,说:“这么烫,你查体温了吗?多少度?”
傅守瑜蒙着被子迷迷糊糊:“我睡一会儿就好,你让我睡一会儿。”
沈阅动手挖人:“不行,你得去医院。”
傅守瑜誓死捍卫被子:“我不去医院,我不打针!”
沈阅笑喷,戳着他的额头问:“你几岁,还怕打针,嗯?哈哈哈哈……”
曾钊出门办事,眼角余光瞥见学校东门外街沿上两个人搂搂抱抱,其中一个的身影分外熟悉,下意识地踩了一脚刹车,摔车门下来厉声质问:“他怎么了?!”
沈阅正奇怪这人是谁呢,脖子一梗,反问:“关你什么事儿?”
曾钊一股无名邪火燃起八丈高,一言不发伸手抢人。
沈阅抱着人腾不开手,自然是吃亏,一使劲把怀里的人给勒醒了。
傅守瑜眯缝着眼睛对了半天焦距,喊:“曾老师。”帽子围巾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巴掌大的一张脸,烧得通红。
沈阅再一打量,想起来了,这不是生科院那作威作福的霸王曾钊么,傅守瑜的老师。得,原来是熟人,还是老熟人,那么闲杂人等就可以自动退散了。沈阅干脆地把人交到曾钊怀里,叮嘱:“他发高烧呢,带他去医院啊。”
曾钊臭着一张脸,没好气地说:“你走吧。”
沈阅吐吐舌头,暗暗不爽。
曾钊打开后面车门,正准备把人扔进去,可那人就跟没骨头似的,一松手就往地上滑,要是把他一个人扔在后座,指不定一踩刹车就滚到座位下面去。曾钊只好又把他弄到副驾驶座上,一边扣安全带,一边骂:“冤家克星!”
这段时间气温反复,因感冒来就诊的人很多,输液室早满员了,护士就让在走廊里打吊针。
傅守瑜一直迷迷糊糊的,曾钊不知道他是清醒还是不清醒,其实有时候真是不想管他,可一见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又忍不住心软。拿出手机来翻通讯录打电话,找熟人搞到一个床位,把人抱起来,真瘦,跟把柴火似的。
傅守瑜闭眼昏睡,曾钊守在一旁看护士熟练地配药做准备,伸手摸了摸输液瓶,眉头就皱起来了,这么冰,三大瓶全输进去人都给冻死了。叮嘱护士先别急着扎针,转身出病房去医院外面的小卖部买暖水袋。
护士在口罩背后笑问:“你弟弟?”
曾钊苦笑一声:“我儿子。”
口罩遮住了护士惊讶的表情:“看不出来啊,你很年轻。”
曾钊叹息着摇头:“老了,早都老了。”
傅守瑜在点滴还剩一点点的时候醒来,神智清楚许多,看看输液瓶,再看看空无一人的病房,直犯晕。
从医院出来,才发现已经时候半夜了,街上空荡荡的,路灯寂寞树立。他在寒风中站了半天才拦到一辆出租车,上车之后给沈阅发了条短信:“今天谢谢你了,什么时候方便,我还你钱。”
到家了才接到沈阅的回信:“不用谢,钱你还给曾钊吧。”
傅守瑜的心情五味陈杂。
第二天傅守瑜在家收拾,给老人和孩子腾出地方来。
实验室的师弟打来电话,哭哭啼啼地说:“大师兄,这次我死定了,救命呀!”
傅守瑜问他:“怎么了?”
小孩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不小心把新买的上样枪摔坏了,老板会杀了我的!”
傅守瑜揉揉太阳穴,问:“摔成什么样了?”
“外壳裂了,弹簧都掉出来了。”
傅守瑜很想问他:你是从四楼窗台直接扔出去的吗,怎么会摔成那样?
小孩自顾自接着嚎:“那玩意儿值多少钱啊,卖了我也还不起啊,老板这两天本来心情就不太好,我这是走的什么背字啊,往他老人家枪口上撞,呜呜呜呜呜,我不要活了,活不下去了……”
傅守瑜连忙安慰:“没有那么严重,一把枪也就几百块钱。”
小孩抽抽噎噎:“啊,不是进口的吗?我听说好几千块钱一把呢。”
傅守瑜说:“当然不是,国产的,就是从安和买来的,是三百还是五百来着,反正没你想的那么贵,就是真让你赔也不会赔不起。”
小孩又说:“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也才三五百块钱呐!”
傅守瑜想了想说:“这样,我给安和去个电话,让他们派人过来看看能不能修好。”
小孩简直要山呼万岁:“还是我送过去好了,免得惊动老板。大师兄,我爱你,我爱死你了!”
傅守瑜正待要挂电话,听筒里忽然传来熟悉的声音,用的是最陌生的令人不寒而栗的语气:“你不做实验在这儿躲着打什么电话?”
师弟“呃”一声,受惊过度。又听曾钊说“电话给我”,木愣愣地就把手机交出去了。
傅守瑜只觉得头皮发麻四肢冰凉,捧着电话半晌无声,曾钊那边也不说话,好几分钟过去了,只听见彼此渐渐平复的呼吸声。
曾钊绝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他现在只想知道这人能犟到什么程度,怎么,打算躲一辈子呢?完全忘了自己昨晚上刚当过一回逃兵。
“曾老师,要没什么事情我就挂电话了。”傅守瑜说。
一瞬间,曾钊只想掐死他。
傅守瑜居然还真抢先挂了电话,反了他了!曾钊想摔手机,一扭头看见小孩眼巴巴地望着他,磨着牙把手机还回去,骂:“什么事情都去找他!没了他就不会做实验了?”
小孩畏畏缩缩。
曾钊深呼吸几次,稍稍缓和语气又问:“这次又是怎么回事?”
小孩见实在躲不过去了,只好含泪坦白,再三保证:“曾老师,我赔,我一定赔!”
“算了算了。”曾钊颇不耐烦地挥挥手,拂袖而去。
小孩吓得都快翻白眼了。半小时后,接到傅守瑜的慰问电话,心惊胆颤地问:“大师兄,你说我这次不会有事吧?”
傅守瑜听他复述了一遍想了想,想了想,笃定地说:“放心吧,没事。”
小孩又问:“那我还要不要赔钱啊?”
傅守瑜笃定地说:“他说不用就不用了。”
这孩子是去年刚从外校考进来的,跟曾钊接触不多,不了解他的为人,刚才又受了惊吓,一味地忐忑不安,问:“师兄,你说老板他会不会、会不会……”
会不会什么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傅守瑜自然是晓得的,更加笃定地说:“放心吧,他不会。”
其实有时候傅守瑜都为自己的这份笃定感到惊异,他不了解他,绝大多数时候根本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也没那份自信去揣测他。
沈阅想进生物楼,被门卫老大爷拦住:“同学,你是哪个实验室的?”
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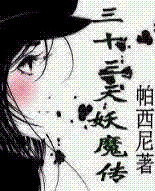




![一个妈妈,四个爸爸[现代np文]封面](http://www.3stxt.net/cover/19/1901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