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曾钊从方老家出来时间已经将近下午三点,这附近的专家宿舍都是一色的二层小红楼,楼外花坛栽一圈玉兰树,正是开花的时节,一树一树美不胜收。那树底下就站着一个人,是任静。
曾钊恍惚记起来了,第一次见到任静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开满白玉兰花的春天,那会儿他还是个刚出校门不久的愣头青,方云深连路都不会走,方老也还住在东门的教师宿舍里,他们并肩走在校园里,他紧张得手心直冒汗,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任静的眼眶红红的,妆也花了,像是刚大哭过一场,甚至气都还有点喘不匀。她迎着曾钊走过来,手里拿着刚才当着方老的面签署的文件。
曾钊眯起了眼睛,像头进入警戒状态的豹子。
任静在离曾钊两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一手捏住文件的一端,往相反的方向用力,一下,又一下。
曾钊的眼睛慢慢瞪大:“你……”
笑容浮上任静依然美丽的脸庞:“刚才就想这么做了,可是当着方老的面,不好。”
“你究竟想干什么?”
“不干什么,”任静的嗓子哑了,可是语气轻松愉快,“曾钊,我同意离婚,你要是方便的话,现在就可以去民政局办手续。”
曾钊抄着手等她接下来的话。
“但是,我不要你一分钱。我嫁给你,不是卖给你,我们的婚姻不管是开始还是结束都跟钱没有关系,你明白吗?”
当初结婚的时候,曾钊一文不名,这么多年了,曾钊没有想过任静为什么会嫁给他为什么死撑着不离婚。那份感情虽然不知道已经在什么时候变质又在什么时候消逝,但曾钊不能否认它曾经存在过。
曾钊大概是愣了几秒钟,才笑了出来:“我怎么有种yesterday once more的感觉?”
任静说:“我还记得当初方老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说过你是锅我就是锅盖。”
“可惜咱俩不是一套。”
“是啊,咱俩不是一套。”
“我的车就在附近,你去哪儿?我送你。”
“去民政局吧。”
“不着急,我还有些事情要办。”
“那就下周一。”
“行。”
任静目前住的那套富丽锦城的房子、还有一半以上的存款,曾钊还是准备都给她。这是他应该给的。
曾钊去附属幼儿园接傅宝宝放学,没见那对流氓父子,问傅宝宝后来还有没有受欺负,傅宝宝用肉嘟嘟的小手戳着他的脸颊说老实说乾乾生病啦好几天都没来上学了,爸爸!
曾钊手一抖差点没把她给摔了,顺着小丫头的目光望过去,却见傅守瑜站在加拿大杨下面冲他们微笑招手,满腔惊喜化为云烟,回头瞪小丫头:“小白眼狼!”
傅守瑜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问:“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叫我来。”
曾钊笑道:“没事就不能找你啦?”
大庭广众之下,傅守瑜跟他保持着距离,问:“到底什么事?”
曾钊笑啊笑:“没事,就是高兴。”
傅守瑜说:“那麻烦您把宝宝送回家,我回实验室了。”
曾钊拉住他:“别呀,难得高兴,一起吃饭去!”
傅守瑜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放开!”
确实有人往这边看,曾钊赶紧松了手,可心里老大不高兴,傅守瑜同志现在对他的态度有问题,看来得找个机会立立规矩了。
傅家父女俩最后还是一同坐上了曾钊的车,傅守瑜深知这一顿饭一吃就回不来了,在后排座上给博士生师弟刘晓发短信请他帮忙收PCR里的东西。
曾钊问傅宝宝想吃什么。
小丫头答得干脆利落:“肯德基!”
傅守瑜立即苦口婆心地教育女儿:“宝宝,这个东西吃多了不好!”
小丫头吮着手指头问:“那什么好吃?”
傅守瑜把她的手从小嘴里拿出来,琢磨着是不是该给小丫头手指甲涂上黄连水,不然这啃手指的毛病恐怕改不了。他也不知道吃什么好,看向前方征询曾钊的意见。
曾钊想了一下,问:“吃鱼好不好?东三环那儿好像新开了一家河鲜馆子,听说味道很不错。”
傅宝宝一听要去吃鱼连忙喊:“不吃鱼不吃鱼!”奶奶眼神不好,有时候鱼刺挑得不太仔细,她嗓子眼儿有特别小,被卡怕了。
傅守瑜忙说:“宝宝乖,吃鱼聪明。”
傅宝宝委屈地说:“鱼有刺……”
曾钊说:“没事儿,曾叔叔在呢,保证把鱼刺挑得干干净净,卡不着你。”
傅宝宝一脸不信任的表情,扭头看爸爸,她爸爸立即帮腔:“嗯,他天天挑鱼刺,他就是干这个的,挑得可干净了。”
观后镜里,曾钊的脸阴云密布。
车子开出学校东门,傅守瑜突然“咦”了一声,曾钊看过来,他指着窗外说:“小方。”
方云深正和一个三十来岁西装革履的男人在一起,那男人背对着他们,只能看见方云深的脸,表情有些不耐烦,说了两句扭身欲走,被那男人一把拉住,方云深想甩开他,没成功,于是起了争执。
曾钊把车停在路边,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傅守瑜说:“不去帮帮忙?”
曾钊像是不解:“帮什么忙?”
“小方那样子像是要吃亏啊。”
“放心,他吃不了亏,光天化日众目睽睽呢。”果然,那男人很快就松了手,方云深瞅准时机跑掉了。傅守瑜也跟着松了一大口气。
曾钊发动车子:“走,吃饭去!”
那男人曾钊不认识,可肯定跟姓安的脱不了干系。曾钊想甭管之前是怎么回事吧,反正现在就是方云深想断,那姓安的恐怕不情愿,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纠缠下去也不是办法,真闯出大祸来后悔都来不及,总得想个法子彻底解决了才好。
饭桌上傅守瑜说起萧定的事情,说他已经同意在生科院内部再开一场专题讲座,这次不讲纳米细菌了,改讲生物材料。
“萧教授真是名不虚传,非常博学。”傅守瑜随口说了一句。
感觉到曾钊在瞪他,又呵呵一笑:“他是我的偶像。”
曾钊拿勺子敲了敲碗:“什么意思,跟我这儿示 威呢?”
“啊?我没有啊。”傅守瑜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实心里早笑翻了。
他的演技实在是不高明,曾钊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不做理会,埋头专心给小丫头挑鱼刺,想着晚上再收拾他。
傅守瑜见他真生气了,连忙赔笑,曾钊夹了一筷子挑好的鱼肉送到小丫头嘴边,小丫头摇头说不吃,曾钊就送自己嘴里了,看都不看傅守瑜一眼。
“对了,细胞实验下周该开了,助教您选好了吗?”傅守瑜另起了个话题。
生科院的专业必修课都配有实验,不过实验比理论课晚开两周,教理论课的教授一般都不亲自带实验,一个班一百来号人分成五个小组,也实在是带不过来,都是交给助教和研究生带,曾钊的助教从来都是傅守瑜。
所以他抬头望了他一眼:“选什么?”
“助教。我已经跟教务处打过招呼了,他们说让您最迟后天必须把新的助教人选报上去。”
“怎么突然想起撂挑子?”曾钊有些不防备。
傅守瑜叹了口气,放了筷子,与他对视:“我不是早跟您说了吗,这学期我有点事,可能没法带实验。”
他一说曾钊想起来了,好像确实说过,某天晚上,在床上……曾钊觉得这不是自己的责任,谁让傅守瑜非挑那么个时间地点跟他说事。
“你有什么事?我怎么不知道?”曾钊拨拉着碟子里的花生米,夹了一个起来问小丫头吃不吃,小丫头不吃,拿在手里玩。他不是不重视,而是太自信,傅守瑜的事情没有不在他的掌握中的,实验、上课,这人的生活单调得不可思议,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就是郭青那个女人,这方面也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曾钊也私下跟她谈过好几回,她愿意收下钱放弃孩子的抚养权——那还有什么事情能烦到他?
本来坐在对面的傅守瑜起身来到曾钊这边挨着他坐下,把曾钊给惊了一下,立即打趣道:“公共场合,注意影响嘿~”
傅守瑜低着头闷闷地说:“有句话我得跟您说,可您得保证听了不生气。”
曾钊的太阳穴抽了一下,直觉没什么好事。
“说。”
“我妈已经住进了省医院,下周做手术。”
“什么手术?”
“脑瘤。”
“这事你确实没跟我说过吧?”曾钊觉得自己让他折腾得都有点精神分裂了,总是恍恍惚惚地记不清楚事情到底是真的发生过呢还是没发生过。
“没有。”傅守瑜说,不太敢看他,却偷偷用眼角余光去瞥他的表情。
曾钊“啪”一下摔了筷子:“傅守瑜,你胆儿够肥的啊,这么大个事情你瞒我到现在!”
被他搂在怀里本来自娱自乐得不亦乐乎的小丫头受了惊,“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一听见女儿哭,傅守瑜的心都揪成一团了,又不可能跟他顶真,只能好言好语:“不是有意瞒着您……”
曾钊气犹未平:“难道还能是无意的?傅守瑜啊傅守瑜,我每天都在你眼前晃悠,你怎么就从来想不起这世上还有我这么个人呢?”说到最后,语气中竟有了秋风的萧瑟,这明明是大好的春日。曾钊是真觉得痛心疾首,他简直怀疑这么久以来,自己是不是剃头挑子一头热,那他也太失败太可悲了点。
傅守瑜也觉得这次自己没处理好,虽然一开始确实跟曾钊闹了矛盾,那时候连面都不想见,就更不想把事情告诉他,可是很快他们就冰释前嫌相处得非常融洽,他还是不透半点口风,曾钊生气也是应该的。
大家都说曾院虽然厉害,可是好涵养,总是从容不迫,常常你都急得快疯了他还不疾不徐。
那是因为他压根就不在乎你。
“跟你在一块儿还真是‘每天都有新惊喜’,”曾钊越说越激动,“不行,你今天非得给我一句明白话——我到底是你的什么人?”
傅守瑜猛地抬头,与他对视,白净的面皮渐渐泛红,可曾钊打定了主意绝不心软,用眼神无声地逼迫,反正他今天是非要一个说法不可。
“曾叔叔。”小丫头嚎了一声见没人搭理,便转为比较省力气的抽噎,可两个大人还是不来哄,干脆出声以吸引眼球。
曾钊拍了她的小屁股一下:“乖,别闹,让你爸爸把话说明白。”
傅守瑜万般无奈:“是我不好,没考虑到你的感受,下次不会这样了,我保证。”
这当然不是标准答案,曾钊哼了一声:“我要你的保证干嘛,又不能当饭吃。”
这次是真把傅守瑜给逼急了,四目相对,傅守瑜诚恳而严肃地说:“我是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不想穷折腾了。”
曾钊嘴上念叨:“你以为我想折腾啊?我就是想折腾也折腾不起了。”心里想的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好吧,既然都不想折腾了,那就凑一块儿好好过日子吧。
曾钊夹了一大块鱼肉喂到小丫头嘴边,乐呵呵劝道:“宝贝儿,再吃一口。”
小丫头一扭头,不乐意吃了。
曾钊笑眯眯地自己吃下去了,傅守瑜在一旁小声提醒:“刺!”曾钊从容地把鱼刺一根一根吐出来,看了他一眼:“急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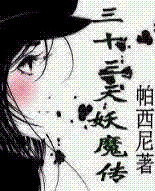




![一个妈妈,四个爸爸[现代np文]封面](http://www.3stxt.net/cover/19/1901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