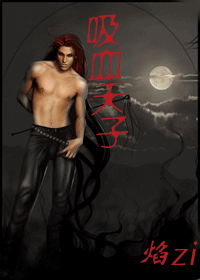一朝天子一朝凰-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顿时觉得非常尴尬,想理清思路告诉他,我画的不仅仅是鹧鸪,那两只鹧鸪就代表着我和他,天上飞的是身为君王的他,地上蹲着的是默默守着他的我,他所在的那个高度,全天下的鹧鸪只有一只能够飞上去,那就是身为龙的他。有了这样的寓意,两只鸟没能双飞就很容易解释了。我组织好语言说给他听:“其实我画的不是鹧鸪鸟——”
他蓦地打断了我,我还以为他心领神会,懂得了我的良苦用心,却只听他张大了嘴巴尖叫道:“不是鹧鸪鸟?难道画的是鸭子?!”
……我简直要被气死了。
☆、第九章 隐瞒
四周红梅清香萦绕,我们在雪地里玩了许久,像小时候一样嬉戏打闹,直到他累得连连咳嗽,连站都有些站不稳,才被我强迫着回了寝殿休息。
可我回到臻园阁,右眼皮却一直跳个不停。回想今日的湛儿,与往日相比实在大为反常。
湛儿性子偏冷,偶尔笑起来也只是淡淡的弧度,转瞬即逝,今日却欢声笑语地打了一下午雪仗。
我猜想,雁门关失守,湛儿虽表现的像个没事人,心里终究是不好受,他今天的表现显然是在强颜欢笑。
我越想越觉得我猜的在理,越觉得在理越放心不下他,辗转半夜不得安眠,终于熬了一碗莲子羹,裹了条狐裘挑灯去了紫宸殿。
我小心护着手里的莲子羹,夜里的寒风席卷着漫天的雪花和冰晶,每一阵风都像一把锋利的剑,可以在人身上撕扯出一个血淋淋的口子,门窗在呼啸的狂风中吱呀吱呀的响。
湛儿还未入睡,窗内一豆烛光,几乎要被无边无际的黑暗吞噬。
我灭了灯递给应门的小厮,小厮刚要进去禀报,被我止住。
我悄悄挨到门边,想这样看他一眼。他消瘦的身影投在身后悬挂着大唐版图的墙壁上,好看的手握着毛笔,在案几上的军事图上画着一个又一个符号。
良久,沉默中传来他小声的叹息。“大雪啊,你为何要与我做对?”话落突然浑身一震战栗,捶着胸口,忍不住猛力咳嗽,良久才平复呼吸,案几上一片模糊红色。
“陛下!陛下!”老药官提着药箱惊慌的扑过去,给他端热茶。
他摆摆手:“不用了,只不过是小小的伤寒而已……”他低头盯着案几上的红色,整张脸面无表情。
老药官哆哆嗦嗦地端着茶,讷讷提醒:“陛下,不是伤寒,是肺痨啊……”
他面无表情的一张脸默然浮起一丝苦笑,那双向来冷厉的眸子仿佛阑珊的烛光。
手里的莲子羹猝然摔落一地。湛儿闻声猛然望向门边。
“这么大的风雪,你怎么跑来了?”他摆出一副晴朗的笑容,不动声色地将话题引开:“是又画了幅画让我看?”
他还想瞒着我,可我已经听到了。我打断他:“湛儿,他刚刚说,你得的是什么?”
老医官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烛光扯出三个人的黑影,我撇过老医官三步并两步到湛儿案几前。案几上的一滩血,染红了地图上那个名叫雁门关的关隘。
“为什么要骗我?”声音已经不知不觉地瑟瑟颤抖。
他抬头看着我,那双冷厉的眼睛里流转出生动的温柔,这样的眼神,明明是有很多话要说,可是说出口的话却寥寥:“我不止骗了你一个。”
话落就是沉默,他低头不再理会我,将染了血的地图卷起来,重新铺上一张新的地图,老医官跪在地上不敢言语。
按道理来说,当你得知你喜欢的人将不久于人世,你该无时无刻不守在他身边,度过最后的时光。可是我只想逃,好像只要逃跑了一切就可以假装不知道。
他才十八岁,天为什么要绝他,我张了张口,却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转身就往外跑。
“姐姐,你可知道——”他突然喊住我,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他。他并没有抬头看我,眼睛盯着案上的地图:“你可知道,如果皇弟们得知我的病情,他们会怎么做?”
没有等我回答他就继续道:“现在朝廷面临外敌入侵,已经应接不暇,如果让皇弟们知道我的病情,势必还会为皇位之争掀起一场血雨腥风。外忧未除,大唐再也经不起内乱了。”他抬起头,脸色苍白却威严。“我已经将阿涵封为皇太弟,将阿瀍封为镇边大将军,不日就会出征雁门关,让他自此远离长安,远离纷争。”
咆哮的寒风在四周发出轰鸣,火炉里不时有火花爆出哔哔啪啪的声响。
“怎么哭了?”
狂风裹挟雪花飞进窗棂,帷幔被风吹出类似鬼魅的影子。直到他这样问我,我抬起袖子摸了摸脸,才发觉自己已经满脸泪痕。
我为什么哭了。这样不言而喻的问题。我心疼他拖着一副将死的身子不知昼夜地守护天下苍生,百姓却毫不领情的痛骂他;我心疼他直到这时候心里想的不是自己的病如何能缓解,而是自己的病会陷皇城于内乱。
我看不下去这样的无私,因这无私对我而言太过残忍。
我捂着脸跑到他身旁,从身后环住他,这是我第一次把持不住自己的情感,紧紧抱住他,好像松一点他就会从我双臂间滑走。“你是不是要丢下姐姐一个人了?”
他笑笑:“我不会死,在收复雁门关之前,我不愿意就这么死了。”
我躲在他身后,自私的想,若是如此,那么雁门关永远都不要收复了。
忽然感觉手背上附上温软物什,正在想是什么东西,发现竟然是他与我十指相扣。以前很多次我都在幻想自己能够嫁给他,那时候就如同此刻和他相依相偎,十指相缠。我狠狠抖了两抖,更紧地握住他的指尖,听到他一贯清凉的声音,听不出悲喜:“等我死后,再寻个良人陪着你,在那之前,姑且陪着我罢。”
……
我从没想过要为自己寻个良人,因为我的良人始终就在我身边,他离我那么近,却也离我那么远。
自那一夜之后,湛儿依旧常住紫宸殿,比平日更加夜以继日的工作。我寸步不离地陪在他身边,直到他熄灯就寝。
他以为我离开了,其实我始终躲在门外。我听到每一个荒寒的长夜,他蜷缩在龙榻的一角,一次次在痛苦中**。有时候会深深的梦魇,时而哭,时而笑,像一个不经世事的调皮的小孩子。我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但这变成之后三个月里我最痛苦的事。这个人,我原本想好好守护他,珍之,重之,到最后他独自一人承受骂名与苦痛,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第十章 阴阳两端
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精神也大不如前,但是为了不引起朝中猜忌,还是会坚持每天上朝。
最近他已经没有精力再熬夜批折子,昏睡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只有十八岁的男孩,却已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我忍着泪珠子趴在他床头,看着漏刻里的滴水滴答滴答落下来,一看就是一整夜,就怕他一睡再也醒不了。
三个月后,已是春来的时节,天空却毫无征兆地卷起漫天飞雪。狂风搅的天昏地暗,房檐上的铃铛哐啷哐啷响,像手持摇铃的巫师正在布下一道索命的法阵。
又一封急报自雁门关传至长安,是阿瀍的亲笔信。
自他担任镇边大将军后,与戍边将士食同灶,寝同帐,同仇敌忾,一鼓作气将回纥军队赶出大唐边境千里之外,成功收复雁门关。
我攥着报信的竹筒,伏在湛儿床头等他醒来,他日夜期盼的就是这个消息,或许解开一道心结,他的病会稍缓一些。
他这次睡了格外久,直到晌午才醒来,但醒来之后,似乎是养足了精神,竟比往日精神许多。
我将雁门关大捷的喜讯告诉他,他拆开竹筒看着阿瀍的亲笔信良久,攒出一个笑来。“该好好办一场庆功宴,犒劳三军将士!”
他瞥向窗外,天地一片混沌。“如今是几月了?”
“已是三月。”
他靠着床头想了想:“三月,臻园阁里那株红梅,怕是凋谢了吧。”
我起身拿来他玄黑的锦袍:“还开着呢,今晨我看到它,还有含苞欲放的花骨朵呢。”
“今夜庆功宴后,陪我赏赏梅花吧。”
我使劲点头,看到他有所好转,我开心昏了头。
他手里拿着玄衣,并没有立刻穿上,犹豫了一会,说:“你知道我做了一个什么梦吗?”我看向他。“我梦到小时候,你总让我穿白衣,说白衣飘逸,我偏要穿黑色,说黑色显得成熟稳重。你就说我是在找借口,说我就是嫌白色不禁脏。”说完自己笑起来。
他说:“你做一件白袍给我,今晚庆功宴上穿。”
我将他手里的衣服夺过来,裹在他身上:“那怎么来得及。”
他将脸一扭:“我说来得急就来得急。”
我愣了愣:“你这是在撒娇吗?”
他转回脸来,一脸正经道:“是。”
“……”
最后我还是从尚衣局要来一匹白色锦缎,紧赶慢赶做出了一条长袍,上面还有白色狐狸毛滚边。
做完已入夜,庆功宴上王公大臣皆已入席。
他穿上身,对着铜镜张开双臂照了照,很好看,月白长袍配他修长身形,墨发整整齐齐束起来,一丝乱发也无。其实,他穿什么都很好看。
可我看着这衣裳白的太过单调,犹豫了一下还是劝说道:“还是不要穿了,丧服似的。”
他从镜子里望着我笑了笑:“无妨。”
我伴他身侧直至宴会之上,他容光焕发,白袍在千万盏花烛的掩映下有璀璨光彩,嘴角始终噙着笑意,全然不像是被肺痨久久折磨的将死之人。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所有痛苦只有自己一个人承受,而他留给世人的,永远都是高大而尊贵的身影,有十八岁的男孩所特有的意气风发,也有身为一个帝王的赫赫威严。
因这场宴会是他携几位王爷为三军将士接风,我并未过多停留,便与他约好在臻园阁等他。
行至紫宸殿却撞见一个陌生身影行色匆匆跑出来。竟有人擅入紫宸殿,莫非是盗取某些重大军事机密?我瞬间焦急万分,提着裙子飞快跑过去拦住她。是个面容姣好的女子,看行装,并不是宫中婢女。
她似乎比我还焦急,抓着我就问:“陛下呢?陛下去哪了?”
虽然对方是个美人儿,我也没听说过有对女子还用美人计的,但我依然不敢放松警惕:“你是谁,找陛下做什么?”
女子平静下来,上下打量我:“我认得你,你是清源,李涵的姐姐。”
我愣了愣,更加摸不清女子的底细:“你到底是谁?”
她突然扣住我肩膀,我以为她要挟持我,正要出手反抗,听见她的唇凑到我耳边轻轻说:“拜托公主务必要找到陛下,告诉他千万莫要吃李涵敬他的那杯酒……那酒里有……有毒……”
“你说什么?!”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表示坚决不相信。
女子望着我,这张陌生的好看的脸上染了玉兰花的清香:“难道你们之间的嫌怨还需我来提醒你?李涵今夜欲弑兄篡位,你要帮我拦住他。”
听到此处,尽管被她扣着肩膀,我还是一个踉跄,眼前一团漆黑,险些跌倒,幸好她扶住我。我抓着她的手臂站好:“湛儿……已经去了庆功宴……”
我猛地推开她,转身往回跑,漫天飞雪在身后纷纷扬扬。可越是着急,脚下就像粘着浆糊一样,怎么都跑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