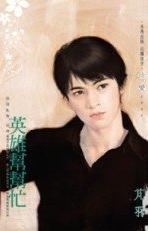乱世英雄之一衣带水-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官?”两人对视一眼,同时想到了葳香楼里天降的援兵,忙道,“快快有请!”
不消片刻,刘安便引着两人走进前厅,当先一人紫衣长靴,正是那手持强弓为大伙打开生路之人,此时终于能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广颡隆准,躯骨伟岸,英武不凡,举手投足间似有一种睨视万物的气度,见二位门主起身相迎,忙站定抱拳:“晚辈上官彦韬,这位是师兄郭成,见过三位门主。”郭成也上前一步,跟着抱拳行礼。
夏侯彰伸手相扶:“上官公子多礼了,我们三家才该谢你救命之恩。”
“门主无需客气,直呼彦韬其名即可。”上官彦韬谦逊笑道,“此次能脱大险,是众人舍生忘死、齐心合力所赐,晚辈三人功薄蝉翼,怎敢居功?”
夏侯彰抚须而笑:“呵呵,贤侄过谦了。”双方又寒暄几句,分宾主落座。
皇甫一鸣精明的眼光在两人之间逡巡,心中不由犯起了嘀咕,此二人高鼻深目,轮廓分明,郭成更是筋骨粗壮,不类我汉家男儿,便微笑探问道:“上官公子师从何人?”
上官彦韬似并未察觉他目光中的探究,仍是泰然自若地与他对视,恭恭敬敬地答道:“晚辈出自上官世家凉州分支,去岁胡人南下,才与本家会合。此次乃奉家主之命,前来联络江南侠士。路闻三大世家广洒英雄帖,不由大喜过望,便同范、郭二位师兄一同星夜兼程,终于在今宵赶至。”
夏侯彰关切道:“上官兄近来可好?四大世家本来同气连枝、情谊甚笃,去岁以来却断了联络,我等都很是忧心。如今得见几位贤侄,我等也可安心些许。”
“晚辈替家主多谢几位门主惦念。”上官彦韬起身欠身一礼,“家主受了些轻伤,身体还康健,对江南形势也甚为关心。”
“刚才你称范师兄的那位……名讳可是范福?”皇甫一鸣心念一动,问道。
“正是。”上官彦韬笑道,“皇甫门主还记得范师兄,晚辈可要替他道一声谢。”
夏侯彰微微颔首,范福在上官本家弟子中排名第八,武功虽不见得多出挑,但为人伶俐、办事活络,上官门主每每出门必带他随行,是以于三家门主都很熟络。夏侯彰点点头,问道:“不知现下他人在何方?”
“这还是等范师兄回来,再让他同二位门主细说吧。此外,彦韬有要事禀报,”上官彦韬说着从怀中掏出两个瓷瓶,“托众位洪福,晚辈有幸不辱使命,于陵野渡口截住贼人。诸位将此瓶中之物倒出少许至香炉或火塘之中,至多三五个时辰,内力自可回复。”
皇甫、夏侯二人先是一惊,再是一喜,随即又是喜怒莫测。上官彦韬心领神会,补充道:“晚辈已证实此药无毒,二位门主尽可放心。”
闻言,二人均露出大喜过望的神情,忙令刘安将解药送与众人。皇甫一鸣悄悄递了个眼色,叫他务必先试试这解药有没有诈,刘安会意,告辞离去。
上官彦韬并没错过这一幕,却只笑笑视而不见,对身旁魁梧大汉说道:“郭师兄,劳你把解药给那位中了暗器的姑娘送去。”
那汉子一点头,又对二位门主一抱拳,转身离去,仍是一语不发。
“二位门主莫怪,”上官彦韬解释道,“郭师兄被贼人所害,伤了咽喉,因此不常说话。”
他说这话的时候,双目低垂,脸上笑容淡去,显是不愿多谈,两人也不便再问,转而问起如何遇到净天教众人,如何得了解药。上官彦韬略略说了经过,只一径强调贼人惧怕皇甫家追兵,不欲多做纠缠,自己诸般辛苦皆略去不讲。
可夏侯彰哪有不明白的?感叹道:“幸亏贤侄仗义相助,否则今日之事势必不能善了。”
皇甫一鸣却是一皱眉:“贤侄既已料到贼人去向,为何不知会一声,我等也好调派人手支援。”
“皇甫门主说的是,是晚辈走时匆忙,考虑不周。”上官彦韬爽快地自承其责,转而又道,“不过倒也歪打正着,范师兄极善轻功,已经暗中跟上了他们。”
他到底还是对厉岩留了一手,他说“我们三人各赴一处”,便是故意让厉岩以为当时当地只有一人可虑。其实早在发现净天教踪迹时,他就已经通知范福速速赶去藏马之地守株待兔,拖延时间与其说是等皇甫家的救兵,不如说是等范福就绪。“如此顺藤摸瓜,定能找出二位少主下落,或许还能知道这伙贼人从何而来。”
闻言,夏侯彰心中暗讶,他能听出来头一句不过是给皇甫一鸣留着面子,这位公子早就已经想得通透,抓住这几个人,远没有探清他们的底细重要。在他们这些浸淫江湖多年的武林前辈对层出不穷的变故应接不暇之际,这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就已算到几步之外,上官家有这般出色后生,他竟从未曾耳闻。可惜了只是出身旁支,不然恐怕早已声名显赫了吧?
“二位门主且放宽心,”上官彦韬胸有成竹地一笑,“吉人自有天相,二位少主定然平安无事,只需静候佳音即可。”
正文 章四 重重疑云(3)
云梦客栈最里间,隔着一道影墙修着一座小院,院内亭台楼阁,月桥锦鲤,翠竹幽径,真有几分江南园林的秀雅精致。如今夜漏初静,月映华苑,隔着轩窗看去,别有一番风味。
然而室内之人却没有这般闲情逸致,欧阳英坐在窗边凳上,忍不住板着脸数落起来:“承儿,你今日也太莽撞了些。”说着抬手制止了徒弟的告罪,“你的性子为师明白,可总这么不管不顾地往前冲,有几条命可以让你挥霍?再说,就算不为自己着想,难道就不怕师父师娘……还有你师妹担心吗?”
姜承一张脸涨的通红,本就不是伶牙俐齿之人,听到此言更加丢了舌头也似,半个字都说不出来。
“以后拼命前,千万记得多想想。”欧阳英慈爱地拍拍他的肩膀,“好了,你早些休息,好好养伤。”语毕,却没有立刻离去,扫了他一眼,欲言又止。
姜承会意:“师父,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承儿,”欧阳英皱起眉头,“你和那唐海……”
听到这个问题,姜承一时默然,良久,才答道:“徒儿与唐兄……唐海结识,正是在去岁北抗胡人之时。唐海是往来南北的商贾,那时他正押着一船货物欲往江北贩卖,行至半路赶上贼寇南侵,只好滞留下来。谁料贼寇攻势如此迅速,转眼就席卷了大半中原。那时百姓仓皇南逃,江边渡船不敷使用,唐海便毅然舍弃货物,将自家货船权当渡船使用,活人无数。后来我和众位兄弟赶到,抗击贼寇,便与他结识。唐兄本出自书香世家,小时候身子骨弱,才送去清虚观习武强身,但他的父亲一直希望他走学而优则仕之路。后来父亲去世,再加上朝局动荡、报国无门,这才毅然弃儒从商。”言及此,不由神色黯然,“唐兄一代奇侠,腹有大才,不知为何……”
欧阳英点点头,劝道:“别想太多,人生在世为当为之事,对得起天地良心即可。若他真误入歧途,咱们设法导回正道便是了。若他执迷不悟,你身为友人,更应竭力阻止他铸成大错。你放心,师父和你几位伯父都不是小肚鸡肠的人,若他悔改,定会给他机会。”
姜承郑重点头:“是,师父。”
……………………………………………………………………………………………………………………………………
不知何时,天上飘起了细雪,擦过枯木衰草,发出簌簌轻响。葳香楼的火渐渐熄了,剩下一团黑黢黢的焦木。
暮菖兰的愤恨与不甘,仿佛也似这团火一般,烧过之后只剩下一片辨不出形迹的空茫。官府的人来过又走,众人也渐渐散去,她仍是在青石板路上席地一坐,淡看对面火星暗淡,听着身边水声潺潺,天地之间仿佛只她一人。
几个时辰前还是雕梁画栋,转瞬间就成了断瓦残垣。是不是她所拥有的东西永远都是这样,即便看起来再美再好再牢不可破,只要别人动动手指,顷刻间就会化为泡影?
街上响起一阵脚步声,伴随着天塌下来也一样嘻嘻哈哈的大嗓门:“掌柜的,你怎么还在?走吧,再看也看不出花儿来。”
听到这个声音,暮菖兰渐渐熄灭的怒火登时有了复燃的迹象:“姓谢的!还不是你!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才会留下你!”
“这话可就不对了,”谢沧行不以为意,“命里有时终须有,再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说的轻巧。”暮菖兰冷哼一声。
谢沧行见她没有动窝的意思,随随便便往她身边一坐,连地上的雪都没拂一拂,伸手递过去一件外袍,邀功似的说道:“欧阳老爷给的,细棉布的好货。”
听他这么一说,暮菖兰还真觉得有点冷了,犹豫片刻,板着脸接了过来,嘴上不依不饶地抱怨:“某人不是说自己功夫天下第二、除了他师兄再没敌手?”
“不不不,”谢沧行连忙摆手,澄清道,“我俩还没分出胜负呢!顶多算并列第一,我那是看他年纪比较大才让他当第一的。”
虽然不是头一次听他大言不惭,暮菖兰还是不由得目瞪口呆,扶额叹道:“见过脸皮厚的,没见过这么厚的。”随即戏谑地睨着他,冷笑道,“天下并列第一的谢大侠,怎么还打不过那红发小哥?难道他就是你师兄不成?”
谢沧行仍未见丝毫愧色,搔了搔头:“唉,我天下无敌的是剑术,今日手中无剑,本事再高也施展不开呀!”
一听这话,暮菖兰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满场子都是剑,随便‘借’一把又有何难?”
“那哪儿成?满场子的剑都又短又轻,没一个够份量,跟玩具似的……”谢沧行突然意识到不妙,连忙止住话头。
不过还是晚了一步,就见暮菖兰秀眉一轩,凤目一瞪,一手轻轻摩梭着腰间的剑鞘:“哟,那我们这些拿玩具的,都是拿着好玩儿的了?”话音未落,连着剑鞘就往他头上敲去。
眼瞅着暮菖兰突然发难,谢沧行立刻跳开一大步,嘴里嚷嚷着:“掌柜的你悠着点!”
“还敢躲!”暮菖兰柳眉一挑,手腕一翻就往谢沧行额际头维穴点去,这要是中了,管你几尺大汉一样得眼前一黑。
谁曾想谢沧行竟真的听话不闪不避,暮菖兰一惊,指尖用力鞘尖一偏,总算错开毫厘。
谢沧行额际当即鼓起一个大包,一边揉着脑袋一边嘟囔:“哎呦!完了完了,本来脑子就不灵光,以后更不顶用了怎么办?”
暮菖兰也没料到这种展开,今日横遭无妄之灾,心里一直不痛快,再想起被这人硬拖下水的恼恨,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心想着怎么也得揍个鼻青脸肿才解气。可看他额际顶着一个大包的滑稽样子,这股子气又忽然没了着落,悻悻然收了手,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只好僵着脸一语不发。
谢沧行倒是胆大,还敢往她身边落坐。暮菖兰尽力不去转头看他,两人好久没说话,直到谢沧行打破了沉默:“掌柜的,你见多识广,倒是跟我说说,这净天教到底什么来头?”
正文 章四 重重疑云(4)
暮菖兰瞪了他一眼:“你连他们什么来头都不知道就往上冲吗?”
谢沧行眨眨眼:“我没想冲上去,那不是你……”见那双凤目危险地眯起,哪敢再装傻,赶忙收了口,“这……我看他们手段不光明,一时看不过去。”
“随你怎么说。”暮菖兰懒得跟他争辩,单手支颐,有气无力地说道,“大概三十几年前吧,最开始是一些世代为奴的长工护院不满主人家虐待,仗着身强力壮、有的还有一身功夫,逃出家来聚在一堆,号称要为受苦的弟兄们讨个公道,着实打劫了不少官商富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