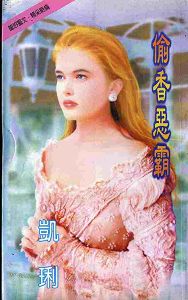迷谍香-第7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郑安平急道,“那如何是好?”
他黯然戚笑,“魏冉岂会饶我今次?既然已无他日之期,又何来他日之忧?”
他的思绪断在那里,因为听见有人踏着枯叶向他走来,细细碎碎的声响随风而过。他回过头,看见那张素白明润的脸、秀若水墨的眼。
他不禁感恩一笑,轻轻唤道,“小令箭。”
她走近了、他才看清,她的双眼又红又肿,似乎哭了许久、刚刚拭干。
小令箭在他坐的那块石边跪下,仰头看着他,啜喊了一声“淮哥哥… ”
他见她忍不住、眼眶里又盈满泪。他明白,她是心疼他的苦楚,担心他的处境,却又说不出来。
范雎温柔一笑,将鱼竿挑起,搁在石边,空出手来摸着她圆润的脸庞说,
“我的小令箭,哭起来还真是和小时候一样。”
小令箭连忙低头擦了泪,目光看向一旁,岔开话题说,
“淮哥哥明知浪急无鱼,为何还直钩独钓?〃
范雎漠然一叹,“当年尚公垂钓于渭水之滨,寒江凿冰,无饵而渔。此番从舟亦是直钩而钓,以己为饵,他们搏的都是‘愿者上钩’。他们都搏赢了。”
他口中随意的几个字,又触到楚姜窈心痛的地方,她像个孩子般伤心地哭泣起来,埋下头,低低地呜咽,“ …现在怎么办?该怎么办?”
范雎心疼地摸了摸她的肩膀,微笑着说,
“我既然是‘愿者上钩’,心无怨忖。随命随缘也罢。”
心无怨忖… 小令箭闻言抬起了头,范雎看着她,眼神愈发柔软。
“……入秦这几年,我一直在以命相搏。从前、我从不去想自己搏的值不值得,也不知道能不能赢。但那时我不害怕,若我搏输了,不过化作草芥鱼饵,被人穿于钩上。但如今,我怕自己若成了鱼饵,会牵连他亦被拴于勾上……”
小令箭忍不住哭喊,“淮哥哥,此番回秦国危险,我随你一起去!”
“不许去!你帮不了我。”范雎立刻打断她,话未说完,见小令箭视线一斜,望向他身后。他随她看去,见从舟从远处走来。
小令箭知道他们二人有话要说,默默站起身,退到远处,倚在一棵树下。
虞从舟走到他身边,见范雎仍不肯多看他一眼,低了头、拿出一双皮绒手套递给他说,
“哥哥,昨晚我看你… 手很冰,这个暖… ”
范雎似乎并未拒绝,他又有了些勇气,“我听说,兄弟就像一双手套,若丢了一只,就等于丢了一双。”
“哦?在我眼中,‘兄弟如衣服’,少了一件,正好,还有另一件可以穿。”
虞从舟闻言瞬间蹙了眉,“我想了一夜,还是想不明白。你既然心软来救我,为何偏偏心狠不肯相认?”
范雎冷冷笑了一声,“心狠?怎比得过你心狠,以鱼为饵,诱鱼上钩!”
“我们既是兄弟,本是一江之鱼,只要一人镬于钩上,另一人又岂能走脱?!”
从舟此时忿懑上涌,眼神凌厉、脸色透红。但范雎只是轻轻淡淡一个眼神瞟过,落在他眉心,他就立时沦陷了气场,低了眼、绉绉道,
“我… 我只是想证明给你看,你我之间的牵连,根本就斩不断。你心里早已认下我,到底你要嘴硬心软到什么时候!”
范雎仍是不语,只是淡漠地望向河水对岸。
从舟寻不出话来说,过了片刻忽然想起昨日范雎叫他办的事,连忙从怀中取出两枚雕得浑似的玉,交给范雎说,
“哥哥… 你昨日要我刻的。”
范雎并未伸手去接,他低头看向从舟手心。哪一枚是真、他自然烂熟于心。但另一枚仿刻的,也确实是惟妙惟肖。若非所用玉石并非纯白、亦没有那抹红晕,从舟雕得简直可以以假乱真。即使是八只虎爪的细微之处,亦面面俱到,所费匠心,可见一斑。
他向从舟走近一步,盯着他带着血丝的双眼说,“昨夜… 一晚未睡?”
虞从舟听见范雎忽然与他说话、语声还似带着关切,不由痴了痴,唇角牵起一丝孩童般的笑。
范雎取过从舟仿刻的那枚,仔细收好,但他将自己原本那枚满玉依旧留在从舟手中,
“若我果真时日不多,这枚你留着,这是当年父亲留下的。”他语调中并无哀伤,从舟听来却字字刺耳,“…务必尽心保管,它可救你性命,亦可能毁你一生。”
虞从舟一把扯住他说,“父亲给你的?哥哥既然如此紧张此物,为何不跟我回家、亲手把它交还给父亲?”
范雎忽然一声哂笑,默默摇了摇头,转过身冷冷道,“我和你不是兄弟。我的父亲,早已不在人世。”
从舟怒极,立时一手攥拳,猛地将他打倒在地,不可置信地吼了一句,
“你抛根忘本!”
范雎一手撑起身体,一手抹去嘴角血迹,冷笑着抬头、挑睨着他道,
“你没资格同我说这个。”
虞从舟见他被自己打得脸颊淤红,踉踉跄跄站起身、却仍旧毫无眷恋地转身要走,忽然心慌心痛心堵都纠在一处,不知所措地在他身后倏地跪下,苦求道,
“哥哥!娘亲临终要我找到你,与你相认。哥哥,求求你,就当成全娘、成全我……”
范雎身形微乱,但他还是无有停留地向远处走去。
从舟涩涩地低下头,“娘亲…是被我害死的。”
范雎心神一痛,脚步滞留,不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已经罪孽深重,哥哥,如果我连答应过娘的最后一件事都办不到,你就不怕我被天打雷劈么?”
范雎只觉心中阵阵凄凉,浑身痛麻。血亲的弟弟就跪在身后,他也想相认,他也想再最后看他一眼,但那样是不是太过自私?他抬头看了看苍天,他到底该做什么,他到底能做什么?这诸般问题、他问了一生,又有谁来作答。
他终是闭了眼,苦笑说,
“如果做不到承诺过的事,就会遭天打雷劈的话,这个天下早已电闪雷鸣。”
他复又大步向前走去。忽听从舟言辞凿凿道,
“这是娘亲唯一的遗愿,哥哥你若不从,就是不孝!”
他的话语像利索一般缠住他双脚,他忽觉步履维艰。母亲温暖如花的容颜瞬间绽放在他面前,儿时仅剩的记忆中,母亲的只字片语,他都不知重温过多少遍,一日都不敢忘。而从舟,是父母留给他、今生今世唯一的骨肉牵连…
眼泪在他眼眶中盘旋,他很想转身,用一个拥抱换掉从前那半生的迷途。这世上除了小令箭之外,从舟—— 或许是他今生唯一应该坦然面对的人。
彼时彼刻,如果从舟只是安静的等待他的转身,或许二人的命途都将改写。
然而从舟急切中又喊出第二句,
“…你身为赵人,却助秦为虐,乐处敌营而不知耻,就是不忠!”
范雎眼中的泪水尚未流下,即已像沸腾的油珠,狠狠灼痛他的眼。原来这半生走过的迷途终究还是解无可解的死结。亲情又怎样,血脉又怎样,这死结留他一人去解即可,切莫再套上他现世这唯一的血亲。
他朗朗冷笑,
“我不是赵人,我也没有兄弟!虞卿虞大人,你我之间最好再无纠葛,做我的兄弟,只会是一条不归路!”
☆、束手就擒
虞从舟见无法将他留下;心一急,扬身立起,跃起几步已欺至他身侧,一把将他紧紧钳住,眼神愈发强势,刺在他脸上、半分不移;
“就算是不归路,也不是我可以选的路。你我既是兄弟;自从出生,就注定走在同一条路上!”
范雎见他竟以武力强迫;怒气冲冲地欲甩开他的双臂,但他那点文弱书生的气力,再挣扎也不过是激怒虞从舟更加蛮横地扣牢他双手。他欲用肘撞击从舟胸口;却反而被从舟一提一拽,猛地推按到一旁的老树杆上。
楚姜窈在远处看着,心急如焚,但范雎始终未出声,她不敢出手妄动。
冷风呼啸中,却传来一声嘶鸣,仿佛疯马脱缰,裂空而来。这样的声音好生熟悉,从舟侧目,见一匹黑色大马似受了惊着了魔、铮铮铁骑踏起一路尘埃、直笔笔地向他二人奔驰而来。
若只有他一人,他可以以武功避开,但哥哥手无缚鸡之力,万一被那疯马冲撞,定会伤的不浅。
没有时间多想,他双手抱住范雎,侧身向树后草地上扑倒去。他以背为盾,全身护在范雎身上,下一瞬间、那黑马的蹄声已然奔近,又是一记长嘶,竟似与他有仇有恨,猛然扬起前蹄、正正踹踏在他背上。
虞从舟的视线一片墨黑,他痛得一闭眼,脑中嗡嗡鸣响,只能紧紧咬牙忍住痛呼,但喉中血腥满溢,他克制不住、一口血雾喷在范雎的衣上。
但他的双肘仍旧死死撑在地上,身体竟未因马蹄踹踏而压痛范雎半分。只是此时、耳边似乎听见那马又抬起马蹄,他心中黯道,
“也罢,若我一命换哥哥一命,娘亲莫再怪我。”
那马却并未踹下,竟是范雎以凌厉眼神制住了它。范雎冲那黑马急喝一声,
“林风,退下!”
这一声入耳,从舟比那马儿还要受惊,小心肝抖了三抖。原来、、竟然、、那马却是范雎的坐骑?!自己这口血喷得冤枉,简直是妄作好人、跪地伏诛,还是被一匹马!
他艰难地睁开眼,再瞧了瞧那黑马,分明就是洺烟湖畔所见过的那匹‘林风’,刚才心急竟没认出来。
流年不利流年不利!他这一年来,真真与马命犯冲!先是被姜窈的那匹短腿马… 诶诶、不提也罢!
他嘴唇一抖,不由又吐了一口血,这回是因为气郁攻心。
从舟咬牙切齿地暗骂,好你个护主心切的死马!待哥哥与我相认,定要叫你知道我是你家二主子!
此时他双肘再撑不住,身体一软倒在范雎胸口
……
那马似乎听得见他的暗骂,大眼圆圆地瞪着他,还慢慢低下颈来,粗大的鼻孔离他越来越近…
他虽然背上如火烧般痛苦,但仅剩的面子不能懈掉,他正毫不示弱地欲瞪还一眼,却见那马闭了眼,很享受地舔了一口范雎的玉脸,鼻中喷出一股难闻的浊气、带着唾沫星子,却全喷在从舟脸上。
虞从舟的爱美之心、自恋之心,都被搞得碎了一地。还好此时姜窈奔来,心痛无比地抱起他,两眼泪汪汪地瞧着他。
报复的机会来了,从舟怎能放过。他不再强忍痛苦、眼神立刻纠结,“只有窈儿待我好……”
姜窈果然愈发心疼地抽泣。虞从舟几不可闻地邪笑一声,将脸埋进她怀里、愈发真实地痛苦喘息着。
范雎抵不过酸意,翻身站起,扯开他后背衣领,一撕到底,他整个背都□出来。
范雎仔细查看他的伤势,冰凉的手指抚过从舟青得发紫的伤处,顿了顿,终是深深叹了口气。
寒风吹过,从舟此时背上时冷时烫,难受得紧。但是他心里忽然暖烘烘的。他这一招英雄救兄,或许能让范雎留下。毕竟、他伤的那么重了…
却听范雎说,“好在他武将的体质,这伤应能扛得住。小令箭,这瓶创药待会儿与他敷上。”
从舟气恼地一回头,狠狠剜了他一眼,什么叫做我‘武将的体质扛得住’?真你祖宗的‘文臣的心’!坚硬难磕!
范雎对他的怒目视若无睹,扬身上马,带着剔透冰质的声音、缓缓说,
“昨日你以己为饵,诱我上钩,他日、或许也会有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