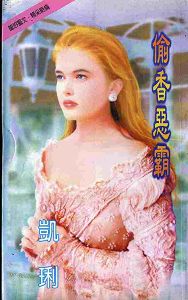迷谍香-第10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除非,至始至终、秦国真正的兵符一直在你手上!”秦王声音愈发冷戾,多年的信任、此刻只觉得是被一个幕后强敌始终玩弄于掌心。
终于还是有这一天… 嬴淮心中苦笑,漠然答道,“雎只是一介魏国布衣、怎么可能有秦国兵符?”
“‘雎’…?这当真是你的名字么?还是,你本名叫‘淮’,拆作名姓两边、只以苟且的‘且’字掩饰在中间?”
苟且的且……嬴淮心潮涩涩,没错、生于天宫又怎样、此生还不是只能苟且沦落于地下。
“……臣听不明白王上在说什么。”
“寡人是在问你,这么多年来,你可是隐姓埋名?你可是处心积虑?你可是、我先王之后?!”
☆、110指簪为符
整整一夜;嬴淮在地牢中受尽屈辱,但他只是紧紧咬住“范雎”这个飘零身世不肯松口。死士营的人下手毫不留情,针毡碾过,痛在皮肉、苦却全都压叠在心里。
此生志向尚未能燃尽高远、向来挚爱再不能围护左右…… 一丝一丝遗憾、从心间流落,似乎勾带出血的苦涩,潆在口中。
身心俱痛;但他愈加清楚、不管秦王是否真的能查明他的身世、都不会留他活口。因为这世间对王位具有威胁的任何一点可能、都不会被允许活下去。
秦王再顾惜他,亦不会冒这个险。
他昏昏沉沉的想着;狱卒推开门,秦王步进刑室。见他身上血色涟涟、秦王心中虽生了一丝不忍;但仍旧沉着脸逼问,
“范雎,真的兵符究竟是不是在你手上?!你到底把兵符藏在何处?!”
嬴淮虽然身无自由;但此时忍下浑身痛楚,神色清和平淡、一如青莲立于风中,
“臣不明白,王上为何竟会疑心臣手中有真兵符?难道、王上是在对臣说,王上手中的那枚、的确是仿造的假兵符?”
一语难答,秦王沉默。
嬴淮眉眼一垂,淡淡哂笑。笑得秦王心里发凉、不知他是何用意。
“范雎!”秦王语音刻意狠厉,却强不过嬴淮的气场、甚至也镇不住自己。
“王上,若是如此……此等天机不可泄露,不论雎今日说些什么、招供与否,王上都不可能留雎性命了。那又何必多问?”
他语声苍凉、秦王听着,戾怒的心里反而不自觉的起了相惜之情。
“臣与王上相识之初,王上曾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今既然王上怀疑臣,将臣赐死即可,省却一番费心猜疑。王上又何必缚住臣手脚,使臣受那些宵小欺辱?”
秦王深深吸了口气、强迫自己不能在此刻心软,猛地向他逼近几步道,
“范雎,如果你真的是公子淮、你蒙蔽寡人至今,休要以为寡人会轻易赐你一死。今日,你必须交出武王兵符,否则绝对生不如死!”
嬴淮闻言、凝视秦王,眼光中刻意流转一丝失望。但旋即玉唇一抿,默默摇了摇头,深邃的眸子里,眼神竟淡得犹如清晨白雾初霁。
他优雅一笑,反问秦王,“王上轮番对雎用刑,竟然只是为了一枚兵符?!”
‘只是’?这可是能率动秦国百万雄师的兵符!秦王双眉紧蹙、没有料到那在范雎口中竟然沾染着不屑之意。
“兵符真假又如何?范雎身世又如何?”嬴淮眼波潆动,似有魔力,一种出尘脱俗的淡然摄心摄魂,
“自秦庄公至秦武王,数百年皆持真兵符,但难道不是、始终偏居一隅,不得东出函谷关?而自从王上信臣之心、用臣之计,即使兵符旁落,亦多年来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群雄之中、唯秦胜局可握,皆因王上与雎君臣同心。之后,西方收蜀,南方平楚,扩疆千里,令世人敬畏。王与雎一场知交、究竟与兵符何干?!
“如今王上手中的兵符,即使真的是当年伪造,也早已以假胜真。雎一心为王上撇清外戚、固干削枝,奋力至今。若得王权至上,真假兵符又何须挂心?
“即使王上明日指簪为符,三军上下又有谁敢违君令?!只是雎不曾料想,时至今日,在王上眼中,雎之心、雎之谋,是真是假,竟还不如一方玉刻之物?”
……
秦王在空荡的大殿之上静立半宵、眉间不得一刻弛散。范雎的种种诘问始终萦绕在他脑海中。
听闻死士营仍然对范雎刑讯甚重,但范雎只是一口咬定、生来只是魏国流浪之人。
会不会、真的错了?如果范雎根本就不是嬴淮,他该如何面对?
范雎对他、秋泉山默然相救之恩,囚牢中远交近攻之策,甚至、为了与他的相知之信,不肯屈从于公子市的傀控、饮毒自尽之绝,全都历历在目。
他曾立誓要尊他为众臣之上、免他受党羽之争,但现在,范雎曾尽忠心、他却枉顾誓言?难怪当年范雎曾把免死诏还与他手上,君侧近臣、生死又岂在一诏之上。
范雎或许早已看透,只是他自己、误信了君王的定力?……如今、并无外人相逼、而亲自下旨对他严刑逼供的难道不正是自己么。
但或许,那一切恩情待重,都只是范雎为了复仇的伪装?
倘若,他真的是嬴淮,真的是王兄的嫡子,多年前他要入得朝堂、必要得君信任,他要弑君复仇、必要扫尽君侧亲信,那么,范雎从前那一番远交近攻、固干削枝之辞,便又有了一种全然不同、却又合乎情理的初衷。
此时殿隅暗影中有一人缓步走近,是死士营的主管王稽。他阴着眉目力劝道,
“王上绝不可心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放一个。”
那当年逃走的王副将也正是王稽寻来的,秦王明白他的意思,但是…
“但是雎……又何止一千!千军万马也抵不上他一人。”
王稽见秦王犹豫、立刻凑近他耳边道,
“但范雎毕竟有持真兵符之嫌,他年龄又相若,如果他当真是嬴淮,他便是武王的唯一子嗣、亦是惠文王的正脉嫡孙!即使他肯忘了王位、亦会有诸多朝臣会因此挑事、推他即位,那王上的君位堪忧啊!
“更不要说、当年武王之死,早有流言蜚语,意指王室兄弟残杀,即便王上心中明白,那些都是宣太后与公子市做下的嗜血勾当,但毕竟、当年是王上您即了位啊,群臣会怎么想,百姓会怎么想?那弑君篡位的大罪必定全都落在王上身上!”
秦王神色立僵、心中岌岌动容,他从前最信任的人,竟成了要谋他王位、取他性命的宿敌…
他年,他并不曾加害嬴淮父王,即位以来便总以为自己清白,但毕竟他坐着嬴淮应得之位、一坐便是二十多年,而今再守不住那自诩的清白,为了大位安危、连王兄仅存的子嗣也要暗中处死?
这染血的君位、这噬心的血缘… 究竟、该何去何从……
秦王忽然想到什么,一侧眸,问道,“那小令箭、是范雎之妻,可曾扣捕押下?”
王稽庆幸自己早已办妥,“王上放心,范雎入狱当天、微臣便已将她缉拿关押。这般牵连甚重之事,微臣岂敢大意。”
其实王稽早已忧心、范雎会为了当年他逼小令箭为死士之事寻他复仇,此时有此摒除隐忧、断绝后患的好机会,他怎会错过。
王稽引着秦王去了关押小令箭的地室。小令箭双手抱膝坐在一隅,见秦王身影、立刻跪行几步,爬到囚栅边,惶惶求问,“王上,范大哥究竟犯了什么事?为何……要囚禁他?”
秦王冷冷反问,“犯了什么事?你难道不知道?他分明从头到尾骗了寡人!你既然与他青梅竹马,对他的身世、你难道,丝毫不知?”
秦王紧紧盯着她的双眼,想要看看、听见‘身世’二字,这女子会有怎样的惊恐之态。
“身世?”小令箭眼中却只是满目疑惑,似乎毫不知情,“自从属下有记忆起,就跟着范大哥和老乞丐们飘零于魏国。老乞丐都说他是魏国无父无母的孤儿,我从未听说过别的,也从未有亲人来寻过他。”
“王上不可轻信。微臣已令人撬开当年旸山山谷中隐埋那人的童冢,冢中根本已无尸首!”
王稽轻轻一语,听得小令箭在旁浑身一冷,卑躬屈膝中听王稽又道,
“那人定然还活在这世上,当年那场杀戮,他已五岁、必有记忆。这范雎与小令箭差了八九岁,当年的事他或许连她也瞒了。”
秦王并不置言,仍是凝着小令箭问,“若他是孤儿,那他的名姓又从何而来?”
“是一个老乞丐随意给他取的。就像,小令箭的名字,是范大哥随意取的一样。”
王稽见小令箭答得似乎诚恳卑微的模样,立刻提醒道,“王上,问她没有用处。她做过死士,严刑亦撬不开她的口,何况只是询问。”
秦王忽然莞尔一笑,似乎心里已经有了计较,
“问她是没有用处,但是,范雎曾说、她是他铭心刻骨之爱……她的性命、或许有些用处。”
王稽怂眉一挑、立刻附和道,“甚是!若在范雎面前凌迟小令箭,倒不怕他不招。”
“不。寡人并不想屈打成招。寡人是要……反着来。”
秦王幽幽哼笑了一声,王稽越发猜不透。秦王对近侍耳语了几句,不一会儿,近侍已奉了一只木盒来,放在小令箭身边。
“小令箭,寡人要你现在便去见范雎,亲手把这‘云楚’之毒交给范雎,告诉他,就算只是怀疑、寡人也不敢留他在世,若他不肯服毒自尽,寡人便先杀了你。”
小令箭心思紊乱、难道秦王真的再不给嬴淮一丝机会?她叩首哭求道,“小令箭的命贱如草芥… 王上……”
秦王忽然打断她,“贱或贵,都在他心里。不过,若你敢先行自尽,寡人便当你二人做贼心虚,亦绝不会放过他”
……
离开地室,王稽随秦王回到大殿,不解问道,“王上,这是何意?”
秦王拈起一朵茶花,倏一用力、连根拔起,“既然范雎与她自幼两情相悦,倘若他当真只是魏国乞丐、没有复仇夺位之心,必定不想让这冤案连累所爱、应会愿意自尽,以换她一命。
“但假若、他就是嬴淮,那他这一生都陷在复仇重压之下、早已被仇念懵心,如他这般机关算尽、艰难走来,一个女人的生死必不能阻挡他的大志。”
秦王缓缓侧过头,将那行将蔫萎的茶花塞进王稽手中,道,
“寡人是说,若范雎肯为了一个女人自尽,那他必定不是嬴淮。”
☆、111燕脂如血
嬴淮陷于牢中;失却日夜之分、只见血光之色。身体益发虚弱,心中忧虑却又与日俱增。
他此时的心情仿佛夹在两重矛盾之间,四处尽是绝壁峭岩,层层嶙峋的压力向他逼来,不容他寻到一丝辗转的生机。
假若、他矢口不认,死士营定会布下天罗地网、节节查证。以秦国死士营的消息渠道、刺查深度;只怕很快连从舟的身世都会被牵连掀开。他们一双兄弟、皆对秦王王位有重重威胁,没有谁能逃得过。
但假若、他当真供认不讳、坦白身世;秦王自会诛他以绝后患、从此再不会去查其他人,这般虽可避免连累从舟;只是、他早已在众人面前称小令箭是他妻子,夫妻株连之罪又必会害死她。
挣扎为难、死死掐住他的呼吸、一分一刻渐令嬴淮心力憔悴。复仇之念已然放下,不料竟比复仇之初更加难断究竟该何去何从。此时才真的明白;原来比恨更似利刀、更能割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