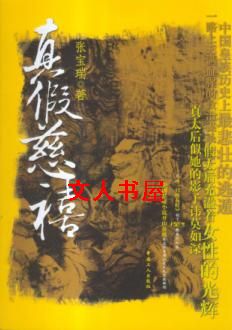真假亨特-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时,狡猾的蛇说:
“老铁手如果想去帮助小敏姆布伦约人,他可以放心地走,不需要担心我们会趁他不在的机会就采取不忠的行动。他的白人可以拿走我的战士的武器,在他回来之前,把我们当俘虏看待。”
大家各抒己见,我没有干预。
“假如我加紧赶路,是能及时赶上小敏姆布伦约人的。”
“要讨论的事情很多。如果太快,以后容易出现问题。我的兄弟最好是先去救人,他回来后,我们再讨论。”
前面讲话的那个人说:
“他可以留在这儿不动,因为小敏姆布伦约人走之前说过,他要去找韦勒尔,却没有说打算去和他战斗。他虽然很年轻,可看样子考虑问题很老练。他还有一匹极好的马。”
大家正众说纷坛的时候,听得一声枪响,只见西北方向有一骑马人,朝南奔跑。我们看到,他忽东忽西,变换着方向,但是一直向我们靠近。很明显,他是在逃脱一个人的追赶,那个人想把他驱赶到我们这儿来。
现在,我们看得清驱赶者了。他比第一个骑马的人矮小,骑的马快一些。原来是韦勒尔和小敏姆布伦约人。逃跑者不时向追赶者开枪,但都打不中。小孩也东打一枪,西打一枪,以阻挡韦勒尔,他的枪也没有击中。
我骑上马,朝两人跑去。韦勒尔有所察觉,尽力把马往西南方向赶。但是,两分钟以后,我不仅赶上了他,而且跑到了他前面,勒住他的马,把枪逼着他的脸。
“下马吧,韦勒尔船长,否则,我会用子弹把您射下来。”
他让我听到的是一阵怀着仇恨的笑,把马往旁边一拨,举起猎枪对准我。这个人在马背上可以瞄得很准。他的枪响了,但是我没有感到有子弹出膛。
他失算了;他转身的时候,看到的是小敏姆布伦的人,小敏姆布伦约人勒住了马,把枪对准了他。这样一来,他两面受敌,只有一条出路,不朝小敏姆布伦约人逼迫他去的方向跑,而朝我们的营地来。他看准了方向,催马快跑,以致我们听见他的马发出的呼啸声。我的同胞们没有武器,不能阻挡他。小敏姆布伦约人离他还有一段距离。我只有靠自己的力量迎击他了。我本来是可以给他一颗子弹,把他打下马的。但是,我想生擒他,又不让他受伤。于是,我就伸手去抓他。
韦勒尔的枪可以连击两次,第一枪是空弹虚发。他没有装弹,马上对我开第二枪。我是从后面追赶他的,不是正面进攻。在我靠近并抓住他之前,子弹肯定能从他的枪膛里射出。因此,我再次对他喊话:
“住手!否则我开枪了!”
他不管我的威胁,转身就射。他的枪管对准我的上身,子弹这次不是空的。我来了个楼里藏身,等子弹刚从我头上过去,我就直起身,向他猛扑。他来不及重新装弹,把猎枪一扔,从腰带里掏出手枪。我没有料到他还有一种武器,这时再伸去抓他,是最傻不过的。所以,我命令他:
“把枪放下,不然,我真的开枪了!”
他不听,而是等我再靠近一点,有把握的时候,又开了一枪。我的马在奔跑,不过我还是两腿夹着马镫,准备射击。为了瞄准,我把枪托靠紧身体以后,才扣扳机。韦勒尔一声尖叫,手枪跌落,手臂下垂。几秒钟后,我到了他身边,用枪托顶着他的背,身体稍稍弯曲,双手同时向他伸出。
“您下来吧!如果您不自己下来,我就把您扔下来!”
我抓住他,想把他摔下马。这时,他掏出第二枝手枪,放声大笑:
“没有那么快,老铁手。您没有制服我,而是我来制服您。”
他想扣扳机,但是不能,因为我左手猛击他的武器,右手由下而上,对着他的下巴就是一拳,打得他头往后仰。紧接着,我飞快抓住我的马和他的马的缰绳,使劲一勒,两匹马同时站住。我飞身下马,把他也拖下马来。他像一只口袋掉到地上,动弹不得,眼睛紧闭,嘴半张开,鲜血直流。
我在检查他的伤势之前,用腰带把他的双臂捆绑起来,把他身上的东西清点了一下,找到了一个信袋和一个用厚丝绸做的钱包,里面的金币闪闪发光。我把钱包收起,把表和其他物品留在他身上。
小敏姆布伦约人来了,把扔下的猎枪和两支手枪捡起来。现在,韦勒尔抬起头,睁大眼睛,恶狠狠地骂:
“你这家伙,放开我!否则,不会有好下场!”
“废话!”我回答,“我倒要看看,您可以用什么方法伤害我。站起来,跟我来!”
“不要碰我!您不放我,我就躺在这儿不动。”
“我可以很好地满足你这个要求。我只要把您的腿捆绑起来,让您躺着,折磨到您的活生生的肉体离开您的僵死的灵魂。不过,我还是想对您人道一点,尽管这违背您的意愿。从地上起来,否则我要来帮忙了。”
他还是躺着不动。可是,当小敏姆布伦约人用枪托捅他的肋骨的时候,他只得跳起来跟着我们走,嘴里狠狠地骂着。到广场以后,我们把他的腿捆绑起来,让他躺在地上。
尤马人在近处充当了这个过程的观众。对我躲开韦勒尔的子弹,他们保持沉默。但是,狡猾的蛇对小敏姆布伦约人说:
“我的年轻兄弟将成为一名能干的战士。我很高兴能够和他媾和,我将由他的敌人变成他的朋友。”
这样就开始了谈判。谈了两个多钟头,产生了一个使我满意的结果。把梅尔顿交给狡猾的蛇,尤迪特成为他的妻子。为此,我得到了我提出的所有的承诺。协议当然是通过抽和平烟斗签署的。谈判结束以后,我们又到了尤马人的营地,为了我的安全,每个在场的红色人都抽了一口和平烟斗。这样,我深信,我们协议的所有条款都会得到他们最严格的遵守。这时,我们才可能考虑其他问题。
“我的白色兄弟现在对我们马上要做的事情什么想法?”狡猾的蛇问,“阿帕奇人的首领和其他人到我们这儿来,还是我们到他们那儿去?”
“看样子是我们去拜访他。我先要与我的白色兄弟商量一下。”
商量之前,我检查了一下韦勒尔的信袋和钱包,发现里面有一万美元的纸币,还有将近五百美元的金币。然后,我召集男性同胞,家庭的父亲和其他独身者,就我的决定进行表决。
大家讨论的时候,我把尤迪特和她的父亲拉到旁边,问这位姑娘:
“我知道您在山岩上与首领谈话的内容。您对您父亲说过吗?”
“说过,”他代替她说,“我心爱的女儿给我讲述了她所感受的荣誉,将成为一个伟大红色民族的女首领。”
“您同意这件婚事?”
“为什么不,这对她,对我个人,都大有好处,因为我们将成为墨西哥和美国有威望的重要人物。”
“看来,您对于一个印第安人部落的政治意义,对于一个首领的市民地位,都还没有正确的看法。我有义务反对您。”
“您什么也不要说!”他打断我的话,“我是我的尤迪特的忠实父亲,只听从她,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将统治一个印第安人部落。我的女儿可以穿天鹅绒和丝绸衣服。您是不是认为,首领在用金子和宝石欺骗她?”
“不是。这儿有宝藏,老墨西哥人的后代默不作声地保护着这些宝藏。为什么首领不知道这样的秘密?他将恪守诺言。您必须保持正确的分寸。他是一个自然人,并不很了解宫廷里的事。他说一尺,总是只能拿到一寸。他也缺乏教育,而只有教育才能保证您女儿的安全。”
“教育?什么是教育?”他又打断我的话,“如果他掌握金子和宝石的秘密,怎么不能受到教育?难道新的丝绸衣服不是教育?难道拥有宫殿的人没有理智?学术讲座、高级中学、综合大学里面藏着什么?不就是几张坐人的木板凳和几只写字的墨水瓶吗?为什么要反对陈设在宫殿里的洛可可式和文艺复兴式家具?不,首领是有教养的,我作为岳父,对他的教养极为满意。”
“您要是这么想,我就不吭声了,只希望您别失望。您现在打算怎么办?我正要给您的同伴们提个建议,离开索诺拉,甚至离开墨西哥。”
“为什么不要他们留下?难道让我和尤迪特单独留在印第安人中间?”
“他们在尤马人中能做什么?要他们野化?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成为首领的妻子,每个男人都能成为其岳父的啊。他们已经认识到,德国工人在这儿得到的是什么。我将把他们带过边界,到美国去。首领是不会同意他们迁移的。”
“这也不能怪他们。他在这片土地上拥有金银,还有一个年轻美貌、富有魅力的妻子,和一个值得敬重的岳父,难道还要穿越边界,到一个找不到金子的地方去吗?”
“那么,您就留在尤马人这儿。据我所知,您的同伴们来的时候都是一无所有,只有海格立斯和您例外。我听说,您带过来了一大笔钱,真有其事吗?”
“当然是真的。”他急忙回答,“那是纯真金,保存在一个钱包裹面。这个钱包是我心爱的女儿尤迪特用丝绸做的。”
“有多少钱?”
“四百美元。为了这个,我才深入到可怕的地下。韦勒尔是个贼。现在,您把他抓住了。您将大发慈悲,向他要抢去的那笔财产。他使我在黑暗的矿井中过着悲惨的生活。”
“是不是这个钱包?”我问,同时从口袋里掏出它,递到他面前。
“正是它!”他欢呼雀跃,从我手中夺过钱包,“我马上数钱,看是不是被偷走了几块金币。”
“不要这么大声喊叫!韦勒尔还不知道我把它拿走了。不要让他这么早就知道这件事。”
他没有对我说一句感谢的话,就带着女儿走开了,到那边和她蹲下来数钱。我转身去找其他人,和他们简单谈了谈内容。他们认为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尽快离开这个地方。于是,我决定:
“我和温内图从这儿出发,去德克萨斯。那儿有大量的良田,气候温和。我带你们去,你们讨论一下,把决定告诉我!”
我离开了一会儿,让他们讨论我的建议。我回来的时候,他们指定的发言人对我说:
“您的建议很好,我们愿意跟随您,但是不可能。首先,我们还不能走,因为梅尔顿和韦勒尔有一个长时间的讼诉过程,我们无论如何是要当证人的。”
“没有必要。我把梅尔顿交给了尤马人。他们审判是不要证人的。至于韦勒尔我不知道拿他怎么办。我用子弹把他的上臂打碎了。在这个国度,这对于一个白人来说是危险的。此外,我从乌雷斯带来了一个警察和一名高级官员,他们在那儿等我们。只要你们为这两个人当了证人,就再不要出庭了。还有什么困难?”
“我们还要通过野蛮区。我们的妇女和孩子能经受得长途跋涉吗?”
“肯定的。尽管他们刚刚从矿井里被解救出来,情况并没有您想象的那么严重。这次行军的速度不会很快,大家不会忍受不了。我给你们从印第安人手里买一些马。此外,我还有好几辆车,装载着食品和用品,你们不会挨饿的。”
“这当然很好。可是我很想知道您对最主要的问题的看法,这就是:钱!”
“这不成问题。”
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这样平静地谈论这方面的事。我大概也像有钱人那样潇洒。所有的眼睛都惊讶地对着我,那个发言人更是难以置信地喊叫:
“不成问题?您也许不成问题,我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