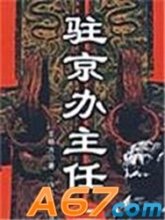怎么办-第4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根本不用看也全明白。
“韦罗奇卡,”过了一个星期他说话了,“你我的生活应验了古时的蒙昧传说:鞋匠总是没鞋穿,裁缝穿衣不合身。我们教别人按照我们的经济原则来生活,我们自己却不想按照这些原则来安排生活。一个大家庭不是比几个分散的小家庭过得省吗?我希望把这个规律应用到我们家庭来。如果我们跟别人伙着过马克思学说的有机联系。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主义的基,我们差不多能节约一半开销,跟我们伙着过的人也如是。那样,我光靠工厂的薪水生活就够用了,可以把令人民烦的可恶的家馆通通辞掉,我想要休息休息,搞搞科研,重抓专业。只要跟伙着过的人关系处好就行。你以为怎么样?”
韦拉·巴夫洛夫娜早就用充满猜疑和愤怒的目光死死盯着丈夫好久了,正如作理论性谈话那天基尔萨诺夫看他的目光一样。他说完话时,她的脸通红通红的。
“我请你停止这种不得体的谈话。”
“怎么不得体呢,韦罗奇卡?我只是说说节省钱的方法。像你我这样不太富裕的人对此可不能忽视。我的工作很繁重,其中的一部分还叫我厌恶。”
“你不该这么跟我讲话,”韦拉·巴夫洛夫娜站了起来,“我不许别人含含糊糊地跟我讲话。你想说什么就大胆直说吧!”
“我只想说,韦罗奇卡,考虑考虑我们的利益,对我们有好处……”
“还说!住嘴!谁给你管束我的权利呢?我会恨你的!”她很快地离开,进了自己的房间,锁上了房门。
这是他们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吵嘴。
韦拉·巴夫洛夫娜锁着房门,一直坐到了深夜,然后又来到丈夫房里。
“我亲爱的,我跟你说了好多过分厉害的话,你听了可别生气。你看,我正在斗争。你不但不支持我,反而帮助我的对立面,我希望,是的,我希望能挺得住。”
“原谅我,我的朋友,我开头太鲁莽了。不过我们不是和好了吗?我们谈一谈吧。”
“对啊,和好了,我亲爱的。但是可别跟我作对,我跟自己斗争已经相当不易了。”
“那是白费工夫,韦罗奇卡。你也花了工夫分析过自己的感情,你看,它比你当初预料的更为严重。你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呢?”
“不,我亲爱的,我愿意爱你。不愿,不愿使你难过。”
“我的朋友,你愿意我好。那么,你以为我会乐意或者需要看着你继续折磨自己吗?”
“不过,我亲爱的,你是太爱我了!”
“当然,韦罗奇卡,我很爱你,这还用说。但是我俩都懂得什么叫爱情。爱情不就是你所爱的人快乐你也快乐,他痛苦你也痛苦吗?你折磨自己就是折磨我啊。”
“不错,我亲爱的,但是假如我听任这种感情发展,你一定会感到痛苦,唉,我真不懂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情!我诅咒它!”
“怎么会产生和为什么产生,这无关紧要,反正是不可逆转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选择:要么是你痛苦,我也受你拖累而痛苦,要么是你不再痛苦,我也好过啦。”
“可是,我亲爱的,我不会再痛苦,那会过去的。你可以看到,那会过去的。”
“感谢你所作的努力。我敬重你这番努力,因为它表示你有毅力完成你觉得应该做的事情。不过你要知道,韦罗奇卡,只有你才觉得该做,我可不这么看。我作为旁观者,对你的处境比你看得更清楚。我知道这无济于事。如果力量够用,你就斗争吧。但是不要管我,别以为你会使我难过。你不是知道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吗,况且你也知道我对处理这件事的主张决不会动摇,而且它确实是正确的,这一切你本来都知道。难道你会欺骗我?难道你会不再尊重我?我可以进一步说:难道你对我的感情改变性质以后便会减弱?不是正好相反吗?由于你发现我对你没有敌意,这感情不是会变得更强烈吗?别怜惜我,我的命运丝毫用不着怜惜,因为你决不会受我拖累而被夺去幸福。但是说到此为止吧。这样的事再说下去要难过的,你听着就更加不好过了。只是你可要记住我刚刚说过的话,韦罗奇卡。原谅我,韦罗奇卡。回到你房里想一想,不过最好还是睡觉。别管我,顾你自己吧。只有顾你自己,你才不致于给我造成无谓的苦恼。”
第26节
过了两个星期,当洛普霍夫坐在他的工厂办公室的时候,韦拉·巴夫洛夫娜却在异常激动的心情中度过了整整一上午。她先是扑到床上,双手捂住脸,过了一刻钟霍地跳了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继而又倒人扶手椅中,坐下了。然后又迈着急促的步子,踉跄不稳地走动起来,接着重又扑到床上,重又下地走动。她几次三番走近写字台,可是站一会便跑开了。最后她坐下写了几句话,封上信封,过了半个小时,她却拿起那封信,撕碎烧毁了。她又慌乱地转来转去好半天,重新写了一封信,又把它撕碎烧毁了。她又乱转了一阵,重又写了一封,刚刚封上,还顾不得写地址,就急急慌慌地飞快地跑进丈夫房里,把信扔在桌子上面,跑回自己的房里,倒在扶手椅上,一动不动地坐着,双手捂住脸。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以后,门铃响了。这是他。她马上奔往书房去拿信,想要撕毁烧掉它。可是信在哪儿?信没有了,到底跑哪儿去了呢?她急忙在各种文件中翻找:信到底在哪儿?这时玛莎已经开了门,洛普霍夫在房门口看见韦拉·巴夫洛夫娜神情恍惚,脸色苍白,正打他的书房出来一闪身朝她自己屋里跑去。
他没有去追她,直接进了书房。他冷漠地、慢悠悠地察看了一下桌子和桌子近旁的地方。是的,他已有好几天都在盼望着类似的情况发生——一次谈话或一封信。现在信就在眼前,没写地址,可是盖着她的印章。当然,她也许来找过这封信,想把它销毁,也许是刚刚扔下。不,她找过:文件都给翻乱了。可是她怎么能找得到呢?她扔下信的时候那样慌乱不安,仿佛猛然甩掉一块烫手的煤块,那封信掠过整个桌面,掉到桌子后边的窗台上了。他几乎无需来读它,便知道其中的内容了。但他还是不能不读:
我亲爱的,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深地眷恋你。我就
是为你而死也心甘!啊,如果我的死能使你生活得更幸福,我
会含笑去死的!可是我没有他却活不下去。我伤透了你的
心,我亲爱的,我折磨坏了你,我的朋友,而我并不愿意这样。
我违反了自己的初衷。原谅我吧,原谅我。
洛普霍夫站在桌前,俯身瞧着椅子的扶手,大约有一刻钟或一刻钟以上。虽然这打击是预料到的,他还是感到痛苦。虽然他事先已经想好并且决定了在接到这种信件或听到这种内心呐喊以后他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他还是不能够一下子把思想集中起来。不过他最终还是把思想集中了起来。他走进厨房对玛莎说:
“玛莎,请等一等再开饭,一会我通知您,我不大舒服,必须在午饭以前吃药。您不要等我,自己先吃吧。不用着急,耽误不了,我过一会才能吃饭呢。到时候我通知您。”
他从厨房走到妻子屋里。她躺着,脸埋在枕头里,他进来时她全身猛然哆嗦了一下:
“你找到那信啦,读过啦!我的天,我真是疯了!我写的什么呀,这全是假话,我热昏头啦!”
“当然,我的朋友,对那些话不必当真,因为当时你过于激动。这类事情不能随随便便做决定。你我还来得及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平心静气地多考虑考虑,多谈它几次。现在我只想对你讲讲我的工作,我的朋友。我在工作中进行了不少改革,我很满意。你听着吗?”不用说,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在听,她只能说无论她是否在听,但她总还是听到了一些什么,可是她听到了什么呢,却顾不上搞清楚。不过她毕竟还是听到并且听清楚了一点:即他谈的是跟信件毫不相干的另一码事,她慢慢地开始倾听起来了,因为她很想把精神集中在什么事情上,而不再考虑那封信。虽然她听了好久还听不明白,但是丈夫的冷静而踌躇满志的嗓音毕竟还是使她平静了下来,随后她甚至能够听懂了。“你听一听吧,在我看来这都是至关重要的事。”丈夫问完“你在听吗?”然后就不间断地说下去,“是的,这些改革使我感到很愉快。”于是他细致入微地讲述着。这些事有四分之三她本来就知道,不,其实她通通都知道,可是没关系,让他讲吧,他这人真好!他什么都说:他对教家馆如何早就厌烦啦,为什么厌烦,在哪一家教课或者教哪些学生时他觉得厌烦,他对于办公室的工作怎么会并不厌烦(因为这个工作重要,对全厂的人都有影响),他怎样能在工厂做出了一些成绩:他培养了一批热心于扫盲的人员,教会了他们如何进行扫盲,并且迫使厂方付给这些教员酬金,他证明工人经过扫盲会减少对机器的损坏,使工作少受损失,因为经过扫盲旷工和酗酒的现象也可以减少。当然,扫盲的酬金微不足道。他又诱导工人改掉酗酒的毛病,为此经常出人于他们就餐的小饭馆。诸如此类的事他干得真不少。但主要的是他办事的干练机灵已被厂里公认了,他渐渐地把整个厂务统统抓到了自己手中,所以在讲话的结尾,也就是洛普霍夫的兴致所在,便是:他获得了副厂长的职位,至于厂长,那只有同事中间有声望、薪水高的人才能担任。而实际管事的却是洛普霍夫。那位同事只在这个条件下才肯接受厂长的职位,他说:“我不行,我哪成!”——“您挂个名就行,这个职务必须由一位大家尊敬的人士来担任,您什么都不用过问,由我来做好了。”——“如果这样,那还可以,我就权且接受这个职务。”其实洛普霍夫并不在乎权力,他看重的是能拿到三千五百卢布的薪水,这要比他原先教家馆、偶然接受的杂七杂八的文字工作、以及他在厂里的原职所得相加的全部收入几乎还要多一千卢布。现在他尽可把工厂以外的兼职统统辞掉,那可真棒极了。他讲了半个多小时,等他讲完的时候,韦拉·巴夫洛夫娜已经能够开口说话了,她说这确实挺好,她还整了整头发,就去吃饭了。
午饭后,玛莎拿到八十银戈比的车费,因为她一共得去四处地方为洛普霍夫送便条,条子上说:今晚有空,欢迎各位光临。没过多长时间,可怕的拉赫梅托夫来了,随后渐渐地聚集了一大群年轻人,开始了一次激烈的学术性的座谈,每个人的意见中种种矛盾的观点,几乎都遭到了所有其他人异常尖锐的揭露,有些不愿再接着进行高雅争辩的,就陪着韦拉·巴夫洛夫娜来打发时间,晚上的时间过了一半,她才明白过来玛莎外出的目的。他心肠真好!这一次韦拉·巴夫洛夫娜由衷地欢迎她的年轻朋友们,虽然她没有跟他们疯玩疯闹,而是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可她非常欢喜他们,连拉赫梅托夫她也想热烈地吻一吻。
客人直到深夜三点钟才散,散得这么晚再好不过了。韦拉·巴夫洛夫娜由于白天过于激动,已经疲惫不堪了,可是她刚刚睡下,丈夫就进来了。
“我的朋友韦罗奇卡,我刚才谈工厂的时候,忘了告诉你一件事,就是关于我的新职务的事,这事其实无关紧要,不值得专门提它,不过顺便说说罢了。只是我有个请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