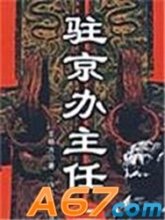怎么办-第4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怎样呢?没有什么新情况。在这期间他几乎每天晚上不是待在洛普霍夫家,就是护送韦拉·巴夫洛夫娜到什么地方去,他常常和她丈夫一起护送,单独护送的次数更多,也就仅此而已。这不仅对他已心满意足,就是对她也觉得尽够了。
现在韦拉·巴夫洛夫娜每天的日子是怎样过的呢?傍晚之前和过去一样。可是到了六点钟呢。过去她通常在这时独自去工场,或者独自待在房间里干活。而现在,如果她傍晚需要去工场,那么头天晚上她就通知基尔萨诺夫叫他来送她去。在往返的不长的路途中,他们总是要谈点什么必须加以拒斥。主张哲学的作用仅在于去“确定和澄清陈述,通常是谈工场,基尔萨诺夫是她在工场事务中最为得力的一个助手。她主管工场事务,而他也有许多事情可干:三十名女工询问和托办的事情加在一起难道还少吗?由他来处理这些事是再合适不过了。办事间歇他就和孩子们待在一起闲聊,有几个女工也参加了这种天南海北的闲谈。他们还谈起阿拉伯童话《一千零一夜》是多么有趣,其中不少篇他已经讲过了。又谈到印度人所尊崇的白象,就像我们这里的白猫很是招人喜爱的。伙伴中有一半人认为,白象、白猫、白马——俗不可耐,这是患了白化病的一群病态动物,从它们的眼睛就可看出,他们不像有色动物拥有健壮的体格;①另一半人却非说白猫好。“关于斯托夫人②的生平您还知道不知道更详细的情况?她的小说我们是听您讲过才知道的。”一个参加谈话的成年女工问。不,基尔萨诺夫暂时还不知道斯托夫人生平的更详细情况,但他会知道的,因为他自己对此也颇感兴趣。眼下他倒可以讲讲霍瓦德③,他差不多是跟斯托大人同样的人物。就这样,基尔萨诺夫时而进行讲解,时而跟伙伴们进行争论。伙伴中占半数的小孩始终抱成一团,而成年人却不断地有变动。韦拉·巴夫洛夫娜干完工作以后就同他一起回家喝茶,三个人喝完茶还要坐好半天。现在韦拉·巴大洛夫娜和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同坐的时间要比以往基尔萨诺夫不在时长得多。只要是他们三个人共度的晚上,准要安排一两个钟头的音乐节目: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弹钢琴,韦拉·巴夫洛夫娜唱歌,基尔萨诺夫坐在一旁静听;有时基尔萨诺夫弹钢琴,那么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就和妻子合唱。最近常有这种情况:韦拉·巴夫洛夫娜从工场急匆匆赶回家来,以便换装去歌剧院,最近他们经常去歌剧院,或者是三人一块去,或者是基尔萨诺夫单独陪同韦拉·巴夫洛夫娜去。除此之外,洛普霍夫家的客人比以前来得更为频繁了。从前,年轻人不算数——年轻人算什么客人呢?他们不过是小字辈——几乎只有梅察洛夫夫妇常来做客。现在洛普霍夫家又与两三个像这样可爱的家庭交往密切起来。梅察洛夫家和另外两个家庭安排每周轮流举行一次小型舞会,只约圈内人参加,每次都能凑足六对、甚至八对舞伴。缺了基尔萨诺夫,洛普霍夫几乎从不去歌剧院,也不去熟人家,可是基尔萨诺夫却常常单独陪伴韦拉·巴夫洛夫娜外出活动。洛普霍夫说,他宁愿穿着大衣待在家里的沙发上歇着。因此,只有半数的晚上他们三个人一块度过,不过这些晚上他们三人差不多总是一刻不分离地待在一起。的确,当洛普霍夫家中除了基尔萨诺夫没有外人时,长沙发常常会把洛普霍夫从放钢琴的客厅吸引过去——现在钢琴已从韦拉·巴夫洛夫娜的房里搬到了客厅——但是这对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来说仍然无济于事:过一刻钟,最多过半小时,基尔萨诺夫和韦拉·巴夫洛夫娜也离开钢琴,起身坐到他的沙发旁。而且韦拉·巴夫洛夫娜也不在沙发旁久坐,她很快就挪到沙发上斜靠在那里,即使两人坐在一张沙发上,丈夫坐着也还是挺松快,因为沙发很宽。其实也并非太松快,可是她用一只手搂着丈夫坐,所以他坐着也不感到挤——
①暗示作者对种族歧视的否定态度。
②斯托夫人(一八一二——一八九六),美国作家,反映黑人悲惨生活的小说《汤姆大伯的小屋》(一八五二)的作者。此书的俄译本出版于一八五八年。
③霍瓦德(一七二五—一七九0)英国著名慈善家,主张改善监狱中囚徒的生活。在俄国考察士兵生活时死于伤寒。
三个多月就这样过去了。
田园诗当今已不流行,而且我自己也根本不喜欢它,就是说,我个人不喜欢它,正像我不喜欢游逛,不喜欢芦笋一样。我不喜欢的东西可不少,一个人本来就不可能喜欢所有的菜肴和所有的娱乐方式。但是我知道,这些虽然不合我个人的口味,可都是上好之物,它合乎绝大多数人的口味,或者可能合乎绝大多数人的口味。他们可比像我这样的宁可下象棋而不爱游逛、宁肯吃大麻油拌酸白菜而不爱吃芦笋的人要多得多。我甚至知道,不愿分享我下象棋的乐趣和情愿不来分享我爱吃大麻油拌酸白菜的乐趣的那大多数人,他们的趣味决不低于我。因此我要说,愿世上能有更多的机会游逛,愿大麻油拌酸白菜从世上消灭干净,仅剩下的就作为希罕的珍馐供我这样极少数的怪人来享用吧!
我确实知道,对于那丝毫不比我差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幸福应当具有田园诗风味,于是我大声呼吁:让田园诗风味在生活中压倒其他一切的生活情趣吧。而极少数的怪人还达不到田园诗的境界呐,他们有着别种情趣。大多数人需要田园诗。说田园诗不流行、人们对它才毫无兴趣,这可不能作为反证:他们对它不感兴趣,只是像寓言中的狐狸不爱吃葡萄一样。他们觉得田园诗式的生活无法企及,因此才说出这样的话:“叫它别流行吧!”
不过,说田园诗式的生活无法企及,那才纯属无稽之谈呢: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它不仅是美好的,而且也是可以达到的。要营造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困难,不过不能够为了一个人或者为了十个人,而是为了所有的人。为五个人排演一场意大利歌剧是不可能办到的,为全彼得堡来排演,正如大家看到和听到的,却是完全可能的。为十个人印一部《尼·瓦·果戈理全集》(一八六一年莫斯科版)是不可能的事。为全体读者来印,谁都知道,却是可能的了,价钱也不会贵的。但是当还没有给全城演出的意大利歌剧时,也只能开个随便什么的音乐会来对付对付一些特别热心的歌迷们。在《死魂灵》第二部还没有为全体读者刊印出来的时候,只能由果戈理的少数特别热心的读者不惜力气分别为自己抄制个手抄本。手抄本和刊印的书不可同日而语,随便什么样的音乐会比起意大利的歌剧来更是差得远,不过有个手抄本和音乐会总比没有强。
第17节
如果某个局外人来与基尔萨诺夫商讨如何对待基尔萨诺夫在醒悟过来时已看清的自己的处境,又假定基尔萨诺夫与其他几位当事人毫无于系,他就会对来者说:“用逃避来补救为时已晚。我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但是对您来说,逃避或留下来是同样危险的,而对于您关心其安宁的那两个人来说,您逃避开恐怕比留下来更危险。”
自然,基尔萨诺夫只能对像他自己或者洛普霍夫这类性格坚强、诚实可靠的人说这些话。与其他人谈论如何对待这种处境问题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别人在这种境况下其行动必然是卑劣和鄙俗的:使女方的名声扫地,自毁声誉,再向自己的所有同伴们诉苦或吹牛,津津乐道于其具有的英雄好汉的美德或勾引女性的魅力。无论洛普霍夫还是基尔萨诺夫,都不爱跟这种人来谈论高尚的人该怎样行动的问题。可是如果基尔萨诺夫对一个跟自己有相同原则的人说,现在逃避恐怕比留下更糟,那么他就是对的了。这里包含的意思是:“我知道你留下时将怎样自处:绝对不流露自己的感情,因为只有这样,你即使留下来也不会变成坏蛋。你的任务是尽可能不去破坏生活已经好起来了的女方的平静。要使这份平静不受破坏,看来已经做不到了。跟她目前的身份不协调的感情恐怕——说什么‘恐怕’,干脆说,是‘毋庸置疑’——已经在她心中萌生,不过她还没有觉察而已。如果完全没有来自你这方面的挑逗,这种感情会不会很快向她自己显露出来,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你一疏远,准会刺激它显露出来。所以,你疏远的结果只能是使你希望避免的那件事来得更快。
然而基尔萨诺夫不是作为一个局外人,却是作为一个当局者来考虑这件事的。他觉得疏远比留下更为难,而驱使他留下的是感情,那么,留下不就是意味着向感情屈服,受感情的左右而迷惑了吗?他有什么权利竟能如此绝对自信,相信自己不会在言谈或眼神中流露内心的情感而挑逗对方呢?因此疏远更为妥当。当事情涉及到自己时,人就很难看出他的理智被矫情的诱惑左右到了何等程度,所以正直的人告诫说:抵制住诱惑,你才能有较多的机会去完成高尚的行动。这是从理论语言译成的日常口语。而基尔萨诺夫信奉的理论,却认为类似“高尚”这样冠冕堂皇的字眼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如用自己的述语来表达:“任何人都是利己主义者,我也是。现在要问:什么对我更有利,是疏远还是留下?如果疏远,我只要抑制个人内心的情感即可。如果留下,我却要冒着损害自己人格的风险,因为一句不得体的话,或者痴迷的一瞥都会泄露天机的。个人的情感是可以抑制住的,过些时候我的平静就能恢复了,我又会对自己的生活心满意足。要是我有一次行动矫情背理,那我就永远于心不安,也无法对自己满意,我将毁掉我的全部生活。我的处境是这样;我爱喝酒,而我面前正摆着一杯美酒,不过我怀疑这酒有毒。我又无法证实我的怀疑。我应该喝下这杯美酒还是免受它诱惑,倒掉它呢?我不能把我的决定叫做高尚的决定,甚至也称不上正当的决定,这些字眼过于铿锵作响。我只能称之为合算的、明智的决定:我倒掉这杯美酒。虽然我剥夺了自己的一份小小的乐趣,给自己造成了一点不愉快,但是我却保证了自己的健康,也就是保证我来日方长,可以大量地饮用那些我确实地知道没有毒的酒。我的行动不算蠢,这也就是我所得到的全部褒奖。”
第18节
那么用什么方法疏远呢?如果使用老法子,假装受委屈,表现自己性格中庸俗的一面,借此来疏远,这已经不行了;两次都用同一套招术就骗不了人了。第二个同样的故事只能拆穿第一个故事的用心,表明他不仅是新故事的主人公,而且是老故事的主人公。总之,快刀斩乱麻的任何做法都是不相宜的。虽然这样疏远比较省事,却过于张扬,会引起注意的,也就是说,那在眼下是庸俗的、卑鄙的(照基尔萨诺夫的利己主义理论,便是愚蠢、不合算)。因此只剩下一个最费事、最折磨人的方法:慢慢地、不露声色地悄悄地避开,使人看不出他在疏远。这件事有点棘手,极为复杂:人家在瞪大眼睛注视你,你却要逃离开他们的视线,而又不让他们看见你的动作。但是别无出路,必须这么做。可是照基尔萨诺夫的理论,这并不痛苦,甚至还挺愉快,因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