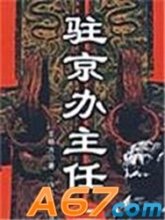怎么办-第3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倒也说得对。看来没我,你们就要有不轨行为了。那您就指定课程吧。”
“比方俄国史,简明世界史。”
“好极了,这我去讲,还把我算作专家,太妙了。身兼二职:教授和保护伞。”
娜塔莉妮·安德列夫娜、洛普霍夫、两三个大学生,韦拉·巴夫洛夫娜本人也都是他们所戏谑自称的“教授”。
除了上课,她们还安排了娱乐。她们举办晚会,进行郊游,一开始次数不多,后来钱多了,娱乐活动就更经常了。她们订了剧院中的包厢。第三年的冬天,她们在意大利歌剧院①里长期包了十个边座——
①一八五O至一八六O年间,每个戏剧节(从秋季到次年初夏)意大利歌剧在彼得堡的米海洛夫斯克剧院(即今天的小歌剧院一八三三年创办)上演。
韦拉·巴夫洛夫娜有多快活,多幸福。同时她遇到了很多的麻烦,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当然她也有痛苦。
工场里一名优秀女工的不幸遭遇不仅对于她,而且对于整个团体都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萨申卡·普里贝特科娃是韦拉·巴夫洛夫娜亲自挑选的三名裁缝之一。她长得不错,性情温和,她有个在官府供职的未婚夫,一个善良的好青年。有一次,天相当晚了,她在街上走,一位先生钉上了她,她加快脚步,他紧跟她,一下子抓住她的手。她猛地一冲,挣脱开了。但是她在挣脱时,手碰了他的胸口一下,竟把这位道貌岸然的先生的怀表打落在人行道上,发出当啷的声响。这道貌岸然的先生理直气壮地扭住普里贝特科娃,喊了起来:“小偷!岗警!”两名岗警跑了过来,把普里贝特科娃送进了拘留所。工场里的人有三天都不知道她的情况;谁也想不出她会到哪儿去了。第四天,一个好心肠的勤务兵给韦拉·巴夫洛夫娜带来了普里贝特科娃写的一张字条。于是洛普霍夫便立刻去奔走斡旋。人们对他说了许多粗话,他也加倍地回敬了他们,然后就去找谢尔日。这时谢尔日和朱丽正在远方参加一个盛大的野餐会,第二天才返回来。谢尔日回来两小时后,警察分局长就向普里贝特科娃道了歉,又乘车去找她的夫婚夫道歉,但是他没有碰到未婚夫。原来未婚夫在头天晚上就到拘留所找普里贝特科娃去了,并从关押她的岗警处了解了那花花公子的名字,已去找他要求决斗了。花花公子还不知他要提出决斗,以戏谑自嘲的口吻认了罪,道了歉;而听到决斗要求后,却哈哈大笑起来。这位在官府供职的公务员说道:“这样的话,你可不能拒绝决斗。”立即打了他一个耳光,花花公子抓起一根棍子,公务员就推了他胸口一把,花花公子跌倒了,仆人闻声赶来,老爷已命归西天。他在重重倒地的时候,额头撞在楼花桌子脚突出的尖棱上。公务员下了监牢,一场官司开始了,难以预料这场官司何时能结束。后来怎么样了?后来也没有什么。不过从那以后,人们都不忍看普里贝特科娃了。
工场里还发生过几件事,虽不是这种刑事案件,却也叫人不痛快。事情平平常常,姑娘们为之长久动容流泪,年轻人和上了年纪的男子却当作是一时的解闷消遣。韦拉·巴夫洛夫娜知道,在今天的观念和情势下这些事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人们对女工怎样关怀,也无论女工自己怎样多加小心,都是永远不可能不出事的。这就像古人在学会预防天花之前,一定要生天花一样。现在谁再生天花,那就该怪他自己了,尤其该怪罪他的亲人们;而以前并非如此,谁都不该怪,除了可恶的流行病或可恶的城市和乡村,也许还有那种得了天花却去接触别人、在复原之前不去防疫站隔离的人,才是该怪罪的。现在发生这些事也一样,总有一天人们能避免生天花,避免的方法已经掌握,不过还是不愿采用它,就像从前人们很久很久都不愿意采用防治天花的方法一样。韦拉·巴夫洛夫娜知道,这可恶的流行病必然会在城市和乡村蔓延,不断地把人的生命夺走,就连小心翼翼看护着的双手也挽留不住。但是如果你只知道“你的不幸不怪我,也不怪你自己,我的朋友”,那么这不也还是得不到什么慰藉吗。这每一件平常的事毕竟给韦拉·巴夫洛夫娜带来了许多痛苦和更多得多的麻烦:有时她需要先探明原委好进行帮助,更经常的是无需追究,只要进行帮助就行:安慰安慰,振作她们的精神,找回她们的自尊,开导她们:‘别再哭了,只要止住哭,就会知道,真是没有什么可哭的。”
不过还是快乐多,快乐多得多!因为除了痛苦就都是快乐了,而痛苦只是个别的和少有的事:如今过了半年以后,你只是在为一个女工痛苦,同时却为所有其他的人而感到快慰,再过两三个星期就又可以为这个女工而感到快慰了。事业的日常的全部进程都充满着光明和欢乐,使得韦拉·巴夫洛夫娜总是兴致勃勃的。而如果在进程中有时受到了痛苦的严重干扰,那么定会有特别的喜事来加以补偿的,而喜事还是比痛苦要多得多,比方说,把某个女工的年幼的弟弟或妹妹安置妥善了,第三年有两名女工通过了家庭教师资格的考试,这对于她们是多么幸运的事,还有过几件类似的喜事。而能引起整个工场的欢腾,使韦拉·巴夫洛夫娜感到快乐的最常见的原因是举办婚礼。婚礼办得相当多,并且都很圆满,喜气洋洋的,婚礼前后多次举办晚会,新娘收到工场的女伴送来的各式各样带给人惊喜的礼品,还从储备金中提出钱来给新娘办嫁妆。不过这又给韦拉·巴夫洛夫娜增添了多少麻烦啊,她自然是忙得不可开交了!只是有一件事工场的人起初觉得韦拉·巴夫洛夫娜不尽情理:第一个新娘请她做女方主婚人,没请动;第二个新娘又来请,还是没请动。而常做女方主婚人的是梅察洛娃或她的母亲——那也是个很好的人。韦拉·巴夫洛夫娜却从未做过主婚人,她只作为一个朋友,给新娘穿装打扮,伴送她上教堂。头一回,人们以为她不答应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其实不然。韦拉·巴夫洛夫娜乐意有这邀请,但是却不接受。第二回,大家才明白这完全是出于谦虚,韦拉·巴夫洛夫娜不愿正式做新娘的保护人。况且一般来说,她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免施加任何的影响,竭力把别人推向前台,叫别人出头露面,她成功地做到了这点,以致于许多到工场来订活的太太在三名剪裁师中认不出她来。韦拉·巴夫洛夫娜在向人家说明这整套制度都是由女工自己建立的,而且始终受到她们的支持时,深深感到,这才是她从工场中体验到的最大的乐事。她竭力用这些说明来使自己也相信那经常在她心里索绕着的念头:工场缺了她也能运转,而且其他类似这样的工场自生自长也是有可能的。甚至根本无需裁缝以外的任何领导,凭着裁缝本身的思想和才能就行,为什么不行呢?这该多好!比什么都好!这便是韦拉·巴夫洛夫娜最珍爱的一个梦想。
第05节
自从工场建立以来,这样过了将近三年;如果从韦拉·巴夫洛夫娜出嫁的时候算起,那就超过三年了。这些年过得平静而又活跃,充满着祥和、欢乐,一切都那么顺遂如意。
韦拉·巴夫洛夫娜醒来以后,还久久地赖在床上。她喜欢懒懒地躺一躺,有点像打盹又不是打盹,而是在思量需要做什么。有时她就这样躺着,既不打盹,也不思量。不,她是在思量:“早晨赖在床上真舒坦,又温暖又软和!”她这么懒懒地躺着,直到她的丈夫,也就是她那“亲爱的”在“中立房间”——不,应该说在“中立房间”之一,现在他们已有两个“中立房间”,因为这已经是她出嫁后的第四年——里说道:“韦罗奇卡,醒了吗?”——“嗯,亲爱的。”这就是说丈夫可以动手烧茶(早茶由他来烧),韦拉·巴夫洛夫娜——不,她在自己房里就不叫韦拉·巴夫洛夫娜了,而叫韦罗奇卡——要开始穿衣服啦。她穿了多长时间!不,她穿衣服倒快,一会儿就完,可是她洗浴的时间长,她喜欢洗浴,之后她又梳了半天头,不,其实她梳头的时间并不长,一会儿就梳好了,但是她久久地摆弄头发,因为她喜欢自己的头发。不过有时她也花工夫进行一项真正的化妆——穿鞋:她有些优质的鞋子。她衣装很朴素,却爱穿考究的鞋子——这是她的一大嗜好。
随后她出来喝茶,拥抱丈夫:“睡得怎么样,亲爱的?”她一边喝茶,一边跟他议论种种大事和琐事。可是韦拉·巴夫洛夫娜——不,得叫韦罗奇卡:喝早茶时她也还是韦罗奇卡——与其说是喝茶,不如说是吃奶油,喝茶只不过是吃奶油的借口,一碗茶里一大半都是奶油,吃奶油也是她的一大嗜好。彼得堡难得有好奶油,韦罗奇卡却找到了真正优质的纯奶油。她梦想着自己有一头奶牛。那有什么,如果事业还照原先那样地顺利,再过一年就能办到。这时十点钟了。亲爱的要去教课或上班:他在一个工厂主的事务所供职。韦拉·巴夫洛夫娜——现在她已经完全是韦拉·巴夫洛夫娜,直到第二天早上为止——都在忙活家务。她倒是有一名女仆,是个稚嫩的小姑娘,事事都需要指点才成,等她刚教会,又得调教新女仆来熟悉规矩了:女仆在韦拉·巴夫洛夫娜家都待不长,总得嫁人,隔个半年或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你看吧,韦拉·巴夫洛夫娜又在给自己缝什么披肩或袖口,准备当女方的主婚人了。这时候她再也不能拒绝,“您怎么能拒绝呢,韦拉·巴夫洛夫娜?您样样事都亲自给我安排好了,除了您再也没合适的人啦。”的确,她为家务操了许多心。然后她要出去教课,她的课时相当多,每周十来个小时,课时再多负担就太重了,而且也没工夫。上课前必须到工场待上一段时间,下课回来还得去看看。然后就跟“亲爱的”一块吃午饭。午饭时,常有客人来:一个,最多两个,再多可不成。即使有两个客人吃饭,已经需要多少地张罗张罗了,得添个菜才够吃。如果韦拉·巴夫洛夫娜回家时累了,午饭就更为简单。饭前她待在自己的房里休息,做成什么样子她不管,就照她当初安排好的那样做吧。要是她回家来还不累,厨房里就该忙碌起来了,她会给午饭添点什么饼于之类的——多半是就着奶油吃的,即可以成为吃奶油的借口的东西。午饭时韦拉·巴夫洛夫娜又是讲,又是问,可是她讲的总比问的多。怎么能不讲讲呢?单就工场来说,该报告的新闻就有多少啊。吃完午饭,她还陪亲爱的坐上十五分钟左右,直到相互说“再见”,就各自回房了。韦拉·巴夫洛夫娜又倒在自己的小床上,看看书,懒懒地那么一躺,她时不时地还睡一觉,甚至经常睡,十天当中得有五天要睡,一睡就是一个到一个半小时。这是一种习惯,看来简直是一种恶习,但韦拉·巴夫洛夫娜饭后如能睡着的话,总是要睡的。她甚至乐意睡着,她对这个恶习的养成既不害臊,也不后悔。等她小睡或者懒懒地躺上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以后,她才起床穿衣,再去工场,在那儿一直待到喝晚茶的时候。如果晚上没有客人,喝茶时她就再给亲爱的讲讲,在‘冲立房间”待半小时左右。然后说声“再见,亲爱的”,吻别后到次日早茶时再见面。现在韦拉·巴夫洛夫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