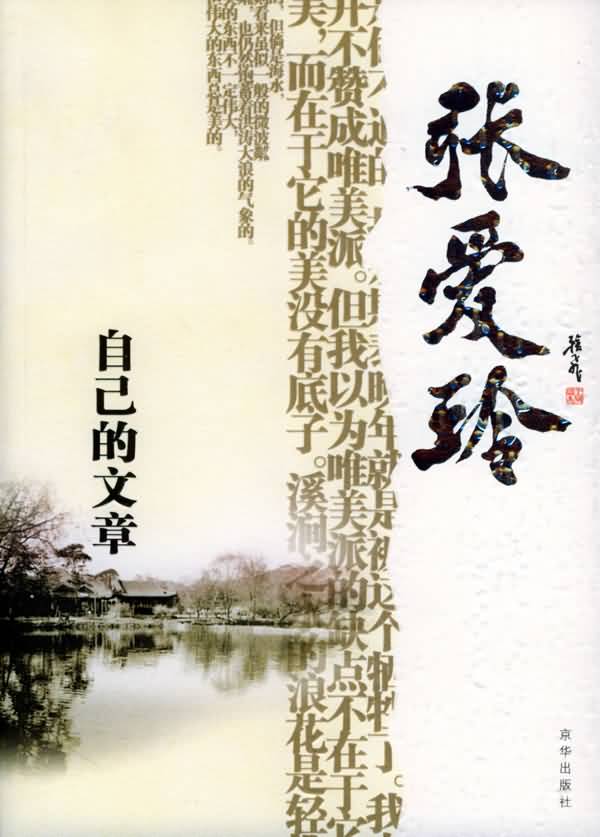方方文集-第5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指气使地行走在大街上,前后雇了两个保镖的日子里,早年的站长业已作古,他患
的是鼻癌,而书记则瘫倒在床,每日被儿媳妇喝来斥去,眼巴巴地讨一口饭水度日,
比吊死还令人觉得凄惨。他是骑自行车摔跤而中风的。卢小波为自己没有报复的机
会而叹息不止。
卢小波在那天夜晚开始了后来几乎成了一种习惯的沉思。他想这事怎么会走到
这样一步?他想究竟是他自己错了还是别人错了?他想倘若是他自己错了他又有什
么可以抱怨?而如果错在别人,那么他又有什么办法来对付他们?一时间,他想得
双泪长流,他觉得自己何其渺小,又何其软弱无助。
那时的我正做着团支部的一个委员。我觉得如此对待卢小波显然很不公平。虽
然世上公平的事少得可怜,但这么明摆着地欺负人也未免过分。我对卢小波说不如
跟大维谈,让大维通过青年人的组织帮青年说几句话。卢小波一脸的不信任,他说
大维这个狗娘养的会帮我说话?他是他们的狗。他不咬我两口我倒感谢他了。我说
不妨试试。
卢小波那天便专门去拜访了大维。卢小波属沉默少言之人,俗话里有“不叫的
狗才咬人”一语,其意乃是不叫的狗比叫狗多一份心眼。卢小波显然也还是有心眼
的人,他居然知道大维擅奕,最喜围棋,便去友谊商店买了副云子,携带着上了大
维的家。
大维见云子自然眉开眼笑,爱不释手。及至卢小波提及正事,言需他大维帮忙
叫屈之时,大维却如烫手般将云子放了下来。大维说要得这副云子还不那么容易呀。
卢小波说我并不想要你帮我争取一个司机名额,我只想请你帮我说明我是怎么进的
拘留所,打架时我不仅没动手而且是准备扯劝的。大维作思考状,一只手又不由自
主搭在装着云子的草藤盒子上。好一会儿,大维方说:“好吧,我去试试。”
卢小波说大维的答话很聪明,那态度使他不知道说把这副云子送给他还是拿回
去。既是试试,就有可能什么都不干,送他一副云子不值。如果不送,他恐怕连试
都不试。卢小波犹豫几秒,还是放下了云子回家了。
卢小波再次去找大维时,大维正用他送的那副云子与入对奕。没等卢小波开口
说,大维便将他拉到外面。大维说晚上我来找你,这下棋的老兄是公司团委的,我
准备他下得高兴时跟他谈你的事。卢小波心里涌出几分感动。他说那你晚上来我这
吃饭?大维说好吧。
卢小波到餐馆端了几个菜,又买了些酒,红、白、啤三种都买了。不论大维喝
哪种,他都有对付的。
天擦黑时,大维来了,坐下即喝酒,白的。不等卢小波劝,便呼啦啦喝下三杯。
卢小波殷勤为之挟菜,且问怎么样?
大维长长地叹息着,嘴里塞进几块肉,方嚅嚅不清地说:“我先提的是你入团
的事,我知道你迫切想入团。可是,那老兄说不行呀。如果,没记档案,包在我身
上不成问题,可惜,入了档,我这边就没办法了。”
卢小波来了气,说:“我现在也不想要入团了,只要平这个冤。”
大维说:“你还敢提这事,你自己签了字,划了押,现在又来推翻,那么,追
问你一句,你为什么要蒙骗专政机关?让真正的坏人得不到改造的机会?故意给公
安机关多弄出个冤案,你是什么目的?什么动机?凭这,不光拘你,说不定还判上
几年,你想,这能开口么?”
卢小波两眼发直,他脑子里嗡嗡嗡地乱成一团糟。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呆
呆地望着大维喝酒吃肉,望着他佯做同情地边叹息边揩油沥沥的嘴,又望着他点着
了一根烟,无奈地摇摇头扬长而去。卢小波守着那桌残羹剩饭呆坐到半夜。后来。
他隔着窗子看到了一颗流星倏地滑落,他想又一个人死了,这个人便是我。很多年
之后,我告诉卢小波,大维其实什么也没对公司团委那老兄说,因为大维赢了那老
兄的棋,两人有些不太愉快。那时的卢小波只是冷冷一笑说:“说不说都没什么意
义。只是可惜了我那副好棋。”
卢小波在站里突然之间就换了形象,以致于初始时人们纷纷交头接耳说卢小波
的神经是不是有了点毛病。有一天站里所有的自行车胎全部消了气,而站长的车连
气门芯都被扔了。一时间站里骂声连天,都说干这事的是哪个王八羔子。在一片喧
嚣声中,卢小波大模大样站出来说:“哥儿们,别骂,是我干的。”骂人的人都怔
了怔,有个女孩问为什么这样?卢小波说要叫全站人重新认识我。所有听到卢小波
如此说的人都吃了一惊,便从那天起,人们知道原先那个沉默少言的卢小波再也不
会出现了。
大维迅速组织团支部委员开会,制订“帮救”措施,即帮助卢小波,挽救卢小
波。会上列举的卢小波的错误写了好几张纸,给人一种卢小波变化时间虽短,却已
恶贯满盈之感。比方干活偷懒,投机取巧;比方在公共茶桶里偷偷倒洗脚水;又比
方给书记的女儿打电话说书记出了车祸已送殡仪馆,而给书记打电话说他女儿被人
暗杀尸体已入冰库;还有拼命纠缠卫生员小茹,对她挑尽下流话说。(不过这事总
没第三者作证,只是小茹一个人向领导哭诉的,而这领导恰恰是她的表舅站长大人,
故而很多人认为是小茹伙同站长一起陷害卢小波。)至于卢小波在开会时故意吵闹,
跟领导唱反调,有偷办公室墨水和剪刀之嫌,等等等等。大维罗列了好几大张,然
后痛心疾首地说:“我们必须得把卢小波拉过来,不能看着他一天天滑下去而变成
人民的敌人。”
卢小波的如此之状,也极令我反感。虽然一度我曾同情过他,且帮他出主意洗
白自己,可他后来见到我也一口的油腔滑调。有一次甚至尖叫着把烟灰弹到我的脸
上,当时许多人大笑不止,令我愤怒异常。好在没多久,我便上了大学,离开了装
卸站,永远可以不见到那个卢小波。
大学二年级时,有一天我乘船过江,在轮渡上遇到了卢小波。他若不喊我,我
差不多根本没认出他来。他戴了副墨镜,嘴角叼了一支烟,一脸的痞子气。我刚上
船时,没坐定就看到几个男女青年在船尾打闹着调情,类似的场面我们平日也常能
见到,这些人被我们称作“油子哥哥”和“油子姐姐”。整个城市中,他们无处不
在,所以我颇有见多不惊的派头。孰料我刚坐下,他们中一个“油子哥哥”朝我走
来。他摘下墨镜,痞着脸说:“小姐,不认识了?我吓了一跳,以为遭到流氓骚扰,
正欲躲避,忽又觉得来者面熟,定了定神,方惊叫道:“是你,卢小波?!”
便是在那一次的相遇中,我知道卢小波已经被开除了。我问他可是以干木匠活
儿为生,他说那不是太累了?他说他隔三岔五地打打麻将,赢了钱就又能过几天。
有一天赌到半夜,他赢了六百块,结果被公安局抓赌抓住了,钱被没收了不说,还
劳他又蹲了三个月拘留所。卢小波说这些话时很轻松很从容,也很诙谐。他说:
“我这是二进宫了。”他的脸上再也没有那一天警察将手铐戴到他手上时的那份惊
恐了。我说你变得好厉害呀,他说你不也变了?原来是个拉板车的,现在派头好大,
我笑了笑,觉得他说的是。
船靠岸时,卢小波的几个狐朋狗友对他打着唿哨,其中之一笑喊道:“嗨,是
你的老相好?”卢小波朝他笑笑又望着我说:“你心里只管把我们当一帮流氓你就
不会计较了。”我没作声,脸上显然也不悦。
几乎快跟卢小波分手,卢小波忽而说:“你还记得金苟不?他被毙了。”
我大惊,问:“为什么?”
卢小波说:“他拿了驾驶执照后,没多久便跑长途。路上有些乡下妇女想搭便
车,他总是很友好地让她们上来,然后找个静处把她们奸了。他干了好几十回。有
一回叫人撞上,逮住了。一审讯,金苟便屁滚尿流地交待出来了许多,这小子想着
坦白可以宽大,结果,给毙了。也可怜,我代他受过,他老婆还是没跟他,只好走
这条路,早知如此,当初岂不是送他去公安局,他不致于死,我也不致于……”
我说:“真的,人有时真是把握不住自己,稍微的一个闪失,没准就错上十万
八千里,谁也预测不了自己的明天会是怎么个样子,却只会望着昨天叹息,看着今
天发愁。”
卢小波说:“你真会说。到底是大学生。”
我说:“卢小波,你打算这么过一辈子?”
卢小波:“有什么不好?总归比金苟强多了吧?”
说完这话,他便摆摆手,走向他那群朝着他挤眉弄眼且做些下流手式的狐朋狗
友。我呆望着他的背影,想着过去的一些事,心道是不是每一个有着卢小波这样经
历的人都会有如卢小波这样的现状?
后来我便写了那篇《羊脂球》。我只想说一个人由好变坏往往身不由己,是社
会和环境所迫,然后还想问,面临着同样的社会和环境是不是每个人都会由好变坏?
如果不是(显然不是),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分野?是不是人自己?人的本
性在人的命运中究竟占了几分主导地位?一个人的堕落,是外界的一只手和自己的
一只手同时拽下去的,是不是只有他们联手才会有力量将人战得一败涂地?当然,
我那小说没这样直白地去说,但其疑惑却是尽在其中。
卢小波对我那篇小说很不以为然。他甚至不屑,甚至觉得我这类人读多了书令
人好笑。那之后,我好久没得到卢小波的消息。
卢小波在很多年后一个刮大风下大雨的夜晚给我打了电话之后,我实在有一股
按捺不住的好奇心。我想他未必靠赌博发了财?或者出现了别的什么奇迹?一星期
后,我忍不住给卢小波打了个电话,然后我们约好了在长江大酒店碰头。
好多人都说“长江大酒店”的窗口像碉堡的枪眼,果然也是。但是里面却极令
人感到优雅舒适。见到卢小波,我说你现在是享受另一种人生了?卢小波说是的:
卢小波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虽然仍是瘦削黝黑的,却不知怎么给人一种老练
精明之感,卢小波说我那天忽然想起你说过的话,你说谁也预测不了自己的明天会
是什么样子,却只会望着昨天叹息,看着今天发愁。所以心一动,就给你挂了电话。
我说:“你这儿好象出现了奇迹,你发财了?”
卢小波说:“可以说是吧。你记得我老爸吧,国民党少将。”
我说:“噢,海外来人了?”
卢小波说:“是,我老爸的副手。我老爸以前说那家伙杀过不少人。1950年要
镇压他,他从乡下跑出来,在我爸这儿藏了几天,然后借了点钱出逃了。现在是个
大老板,回来投资办企业。”
我说:“他来报恩?”
卢小波说:“可不,我老爸死了,可我还在呀。他让我代理他管管事。一个月
你猜多少工资?三千块!可惜我老爸死了,要不他还要买栋楼送给他.”
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