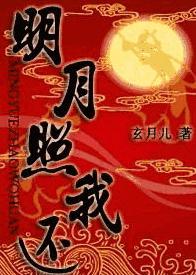疯颠与文明-第3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响。他们把汤放在疯人身边,命令他在当夜喝掉,否则就会受到残酷的待遇。他们退出后,疯人陷入在眼前的惩罚和来世的惩罚之间做出选择的极其痛苦的困境。经过这几个小时的思想斗争,前一种选择占了上风,他决定进食。”
疯人院作为一个司法机构是完全独立的,不承认其他权威。它直接判决,不许上诉。它拥有自己的惩罚手段,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以使用。旧式的禁闭一般来说不属于正常的司法形式,但是它模仿对罪犯的惩罚,使用同样的监狱、同样的地牢、同样残酷的体罚。而在皮内尔的疯人院中,司法完全自成一体,并不借用其他司法机构的镇压方式。或者说,它使用的是18世纪逐渐为人所知的医疗方法,但是,它是把它们当作惩罚手段来使用。把医学变成司法,把治疗变成镇压——这种转换在皮内尔的“慈善”和“解放”事业中并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吊诡。在古典时期的医学中,由于医生对神经系统性质的各种古怪认识,浸洗和淋浴被当作灵丹妙药,其目的是使机体解除疲劳恢复元气,使枯萎的纤维得以放松。诚然,他们还认为,冷水淋浴除了令人愉快的效果外,还有骤然不快的感觉所造成的心理效应,即打断病人的思路,改变情绪的性质。但是,这些认识依然属于医学思辨范畴。而在皮内尔那里,淋浴法则明显地成为一种司法手段,淋浴是疯人院中的常设治安法庭所惯用的惩罚手段:“它被视为一种压制手段。它常常能够使对之敏感的疯人服从体力劳动的一般律令,能够制服拒绝进食的顽症,并能制服被某种想入非非的古怪念头所支配的精神病人。”
总之,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使疯人认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天网恢恢的审判世界;他必须懂得,自己受到监视、审判和谴责;越轨和惩罚之间的联系必须是显而易见的,罪名必须受到公认。“我们可以利用洗澡的机会,用一个龙头突然向病人头上喷射冷水,提醒病人认识自己的越轨或疏忽。这样常常能用一种突如其来的强烈印象使他仓皇失措或驱散原来的偏执想法。如果那种想法仍顽固不化,就重复进行冷水淋浴。但是一定要避免使用强硬的语气和刺激语言,否则会引起反抗;要使疯人懂得,我们是为了他而不得已使用这种激烈措施;有时我们可以开个玩笑,但不要过火。”这种十分明显的惩罚必要时可经常反复使用,以此使病人认识到自己的过失。这一切都应为了最终使司法过程变为病人的内心活动,使病人产生悔恨。只有产生了这种结果,法官才能同意停止惩罚,因为他们可以断定,这种惩罚会在病人的良心中继续进行。有一位躁狂症患者有撕扯衣服和乱摔手中东西的习惯。对她进行了多次淋浴,并给她穿上一件紧身衣。她终于显得“深感羞辱而神情沮丧”。但是,院长担心这种羞愧可能是暂时的和表面的。“为了使她有一种恐惧感,院长使用一种冷静而坚定的态度对她说话,并宣布,以后她将受到最严厉的对待。”预期的效果旋即产生:“她痛哭流涕近两个小时,一再表示悔悟。”这种过程反复了两次;过失受到惩罚,过失者低头认罪。
然而,也有一些疯人不为所动,抵制这种道德教化。这些人被安置在疯人院的禁区,形成一批新的被禁闭者。对他们甚至谈不上用司法手段。当人们谈到皮内尔及其解放活动时,往往忽略了这第二次幽闭。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皮内尔反对将疯人院改革的好处提供给那些“宗教狂人,他们认为自己受到神灵的启示,竭力招揽信从者,他们以服从上帝而不服从世人为借口挑动其他疯人闹事,并以此为乐”。但是,禁闭和牢房也同样适用于“那些不能服从一般的工作律令的人,那些用邪恶手段折磨其他被收容者和不断挑动其他人争斗并以此为乐的人”,以及那些“在疯癫发作时有不可抑制的偷窃病的”女人。宗教狂热导致的不服从,拒不工作和偷窃,是对抗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基本价值观的三种重大罪行,即使是疯癫所致也不能宽有。它们应受到最彻底的禁闭,受到最严厉的排斥,因为它们都表现为对道德和社会一律化的抗拒,而这种一律化正是皮内尔的疯人院的存在理由。
过去,非理性被置于审判之外,从而被武断地弓版给理性的权威。现在,它则受到审判)但不仅仅在它进入疯人院时为了识别、分类和使它从此变得清白而对它进行审判。它已经陷于一种无休止的审判中。审判永远跟随着它,制裁它,宣布它的过失,要求它体面地改过自新,甚至驱逐那些可能危害社会秩序的人。疯癫逃脱了那种武断的处置,其结果却是进入了一种无休止的审判。疯人院为这种审判配置了警察、法官和刑吏。在这种审判中,根据疯人院所要求的生活美德,任何生活中的过失都变成了社会罪行,应受到监视、谴责和惩罚。这种审判的唯一后果是,病人在内心永远不断地悔悟。被皮内尔“释放”的疯人以及在他之后受到现代禁闭的疯人,永远被置于受审的地位。如果说他们已不再被视为罪犯或与罪犯相联系,他们仍每时每刻受到谴责。他们受到指控,却从未见到指控的正文,因为他们在疯人院的全部生活就构成了这种指控的正文。在实证主义时代,皮内尔创立的并引以为荣的疯人院不是观察、诊断和治疗的自由领域,而是一个司法领域,在那里,疯人受到指控、审判和谴责,除非这种审判达到了一定的心理深度,即造成了悔悟,否则疯人永远不会被释放出去。即使疯癫在疯人院外是清白无辜的,但在疯人院中将受到惩罚。在以后一段时间里,至少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疯癫一直被禁闭在一个道德世界之中。
除了缄默、镜像认识、无休止的审判外,我们还应提到疯人院特有的第四种结构。这种结构是在18世纪末确立的,即对医务人员的神化。在上述结构中,这种结构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不仅确立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新联系,’而且也确立了精神错乱与医学思想的新联系,并且最终决定了整个现代疯癫体验。在疯人院的前三种结构中,我们发现它们与禁闭的结构相同,只是发生了位移和形变。但是,由于医务人员的地位发生变化,禁闭的最深层意义被废除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疾病就有可能出现了。
尽管图克和皮内尔的思想和价值观差异很大,但是在转变医务人员的地位这一点上他们的工作却是一致的。我们在前面看到,医生在禁闭过程中不起任何作用。而现在,他成为疯人院中最重要的角色。他掌握着病人的入院权。图克的休养院明文规定:“在批准病人入院时,委员会一般应要求申请人提交由一名医生签署的诊断书。……诊断书还应说明,病人是否还患有精神病之外的其他疾病。最好还应附有其他报告,说明病人精神失常已有多长时间,是否用过或用过何种医疗手段。”自18世纪末起,医生诊断书几乎成为禁闭疯人的必要文件。疯人院内,医生已具有主导地位,因为他把疯人院变成一个医疗空间。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医生的介入并不是因为他本人具有医疗技术——这需要有一套客观知识来证明。医务人员在疯人院中享有权威,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聪明人。如果说疯人院需要医务专业人员,也是当作司法和道德的保证,而不是需要科学。一个廉正而谨慎的人,只要具有在疯人院工作多年的经验,也能胜任工作。医疗工作仅仅是疯人院的庞大道德工作中的一部分,认清这一点就能保证对精神病人的治疗:“给躁狂症患者提供在确保他和其他人安全的条件下的各种自由,根据他越轨行为的危险程度来压制他,……搜集各种有助于医生的治疗的事实,仔细研究病人的行为和情绪变化,相应地使用温和或强硬的态度、协商劝慰的词句或威严命令的口气,难道这一切不应是管理任何疯人院,不论是公立还是私立的疯人院的神圣准则吗?”据图克说,休养院的第一位医生是因为他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而被推荐任命的。这位医生刚进人休养院时,毫无精神病方面的专门知识,但是,“他以满腔热忱走马上任,因为他的技术发挥关系到许多同胞的切身利益”。他根据自己的常识和前人提供的经验,试用了各种医疗方法。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这并不是因为疗效很糟,也不是因为治愈率太低:“医疗手段与康复过程并不是密切相关的,这使他不能不对它们产生怀疑,认为医疗手段可能并非是康复的原因,而只是陪衬。”他发现利用当时已知的医疗方法几乎毫无作用。由于怀有博爱之心,他决定不使用任何引起病人强烈不快的药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位医生在休养院中无足轻重。由于他定期看望病人,由于他在休养院中对全体职工行使权威,因此“这位医生……对病人思想的影响有时会大于其他护理人员”。
人们认为,图克和皮内尔使疯人院开始接受医学知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引进科学,而是进一种人格。这种人格力量只是借用了科学的面具,至多是用科学来为自己辩护。就其性质而言,这种人格力量属于道德和社会范畴。其基础是疯人的未成年地位,疯人肉体的疯癫,而非其头脑的疯癫。如果说这种医务人员能使疯癫陷于孤立,其原因并不是他了解疯癫,而是他控制了疯癫。实证主义所认定的那种客观形象只不过是这种统治的另一面。“赢得病人的信任,使他们产生尊敬和服从的情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目标。而这只能是良好的教育、高雅的风度、庄重的语调和敏锐的洞察力所产生的效果。愚昧无知、没有原则,尽管可以用一种专横来维持,但只能引起恐惧,而且总是激发不信任感。看护已经获得支配疯人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挥和管束他们的行动。他应该具有坚定的性格,偶尔施展一下他的强制力量。他应该尽量不去威吓,而一旦做出威胁就要兑现,如果遇到不服从,立即予以惩罚。”医生之所以能够在疯人院行使绝对权威,是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父亲和法官,他就代表着家庭和法律。他的医疗实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过是对秩序、权威和惩罚的古老仪式的一个补充。因此,皮内尔十分清楚,无须现代医疗方法,只要医生使这些古老的形象发挥作用,就能医治疯人。
皮内尔援引了一个17岁少女的病例。这个少女是在父母的“极端溺爱”下长大的。她患了一种“轻浮的语妄症,其病因无法确定”。在医院里,她受到极其有礼貌的对待,但是她却总是摆出一种“高傲”的样子,这在疯人院中是无法容忍的。她在谈到“自己的父母时总是出言不逊”。疯人院决定对她实行严厉管教。“为了驯服这个桀骜不驯的人,看护利用浸泡的手段,表明自己对某些胆敢对父母大逆不道的人的强硬态度。他警告这个少女,因为她抗拒治疗,并且顽固不化地掩饰自己的病因,今后她将受到各种理所当然的严厉对待。由于这次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和这些威胁,这个少女受到“深深的触动,……最后她承认了错误,并坦白说,她丧失理智是因一段无法实现的痴情所致,她还说出了所迷恋的人的名字”。在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