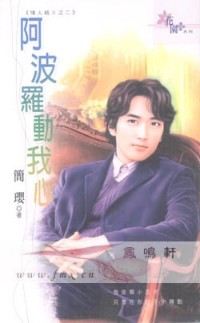���ʲ�-��1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ű����������ҵ�һͰ���ͣ��������̫���˶��µģ�ʷ������˹�����ũ���ǹ��һЩ�������ͣ����ϻ𣬰����dz����Ῠ�ϳ�������
�����Ż��ˣ����ˡ����ƽ��������������˴�ɽ�²�������Ͷ����ǹ��������ͷ����^���������������̴���̫���˵Ķ�Ƥ�������Dz��ڽ���̤����ׯ�⣺�����˸������Ǻ������Сɽ�������˵�Ӫ����Χû����^�����£�ֻһ�γ���ȫ���ٻ�����̫���˱�����ڳǽ��¡���Ϊ������˲�Ը���ţ����AӶ������������
�����ˡ����ǿ������еIJ��������������ͬʱ���Ҳ�����ˣ������ɰͷ�˹���������Ŭ�����ˣ���II����Ծ�����ֺ�ľ�ԣ�^���Ӵܵ���̫���ˣ���������Ȯ��Ұ�á����˵�ת������ִ���ٵĻ�ͷ�����������������˷����߳�ԡ�ء�
����ֻ��²ʼ��վ������ǰ�������и����ˣ����Ǹղ���ս��������������ɡ���Ǹ����������Ķ���˵����
��ʲô��������ִ��������˹����˵����Ŷ��������ɱ�ˣ������ֱ��ؽ���˵һ�䡣
�ǰ����������˴�������γ�һ��ذ������������ͷ������������һ����ͷ�ĵ��˲��Ȅ���֮�䣬��һ�磬���������裬������Ư����һ�����������ͣ�˫Ŀ���ӡ����ش�ǽ�ڵķ�϶�����˽���������ʬ���˵��ڵأ���Ѫ��Ȫˮ�������Ȫ����������������������ɫϸɳ�������˵ذ��������š�ִ��ä�������ֽ�����̯Ѫ���У�����Ħ��ϥ�ǣ���Ҳ��һ����ҩ��
ҹĻ�����ˣ����������^���ڵ̿��ǡ���ɽ�֣�Ѱ������������һЩ�в���
�����Ժ������˸��������һ��С���ĸߴ�����ʱʷ��ڮ��˹�Ķ���0���������С·����^ֻҪ�ö�ʮ�s���ڣ������湥������������ٵذ���������ɽ�¡�����̫����Ŀ�ɿڹ������������߹�����ũ�ڶ���ĵ�����ϳ���Ŭ�����˵Ŀ������ɹ���˹���������¾�������һ�����ƣ�����ũȴ�������⡣
���ǻ������ֲֿ����ӻ���̫������^�������ϸ������ҹ���������·��ÿ��һ�̾���ȥ���ˣ��ü��ض���Ϊ�Ѿ������ˡ�������ǵ����˺�����W^��ᵣ���̫���ɴ�����������ǽ��˻�ȥ��
��ũ��ƣ���ߣ���������^^����������۵ģ�����ʧ����Щս��һ���������Į�ɏ��ֶ�ҩ��������Լ��������������������Լ�Ҫ������ʮ�ּܡ���
��̫��û�о������ͷ�����������ʧ����ʮ����Ű���ʮ���������գ�һ����ǧ���ٶ�ʮ����л���գ�ʮ��ͷս��ʮ��������Ժ���飬��������������ǧ�������㹻�����µ����ӣ��������غ�ȫ����ս��е���ɹ���˹�϶��Ѿ��������ǣ�����֮�����¿�ʼ��ŷ�����ز��������Ѵ�ͻ�������쵽����˹^���Ǹߴ����Կ�����Ұ��һ���Ƴ���������գ����Ǹ����ǵı�����ȼ�ա�
ֻ��һ��������������̫����������Һ�ڲ��ú�������������������ҲͶƱ�ɾ����˼����ٻع�������������
���ʲ����������Ժ�������������������Ϊ^��������ĽŲ������ŵ�����������ž��ѹ�������ÿ�����˸�����������ի����އ�ȿ�Ϊִ�����������Ѿ��۵��ˡ�ɳ�����������������ߣ���i���롣��
���ߡ�����
��
ÿҹ�غ��ڰ�˹��ķ��������۲����ಢ�úŽDZ��������仯�ı����ˣ�һ���峿��������������ֻ������ƵĶ��������ſ������ij���ӹ����档
����һ�������㽰�Ĵ����ٵ���һƥ����̫���������ˣ��������ִ�����һ����������ץ����ţ�������̫��������������������
�Ҽһ������߳���������Ҷ������ű��˵Ļ������ִ�ţ���������վ�����ˡ�������ϳ��˹������������㽰ս����
ս�����������͵������˻����۶�����б���ֱ������������Φ���ŵùĹĵģ�һ����˶���ޱȵĴ��S�н�����Ĵ�ˮ������������Ƕ��˲�ʱ¶��ˮ�棬����Ŝ�ij���·���һƥͷ����������ɵĿ�������˫�㣬�·��ں���ԭҰ�ϳ۳ҡ�
����ᵽǸ��������Ѿ�ƽϢ���������䣬ֻ����������վ��һλû��ñ�ӵ��ˣ����������ִ�������������������Ϲ������ڷ�������ף�����ϵ�ź�ɫ�����ף�¶�������첲�����ϴ������ż��������飬Ũ�ܵĺ�ɫ���ʹ�����ǰ��
�ⅼս���Ⱦ��ڽ���ҡ����������ŷ�����ǰ������Ⱥ�ڷ����̵��̸�ʯ��һ��������ߣ�ͬʱ�����к���
�������¾��������㡣̫������۾���������ǰɣ�������Щؔ������������Ҫ���㣡��ɵ��İ����Ͷ�������
��û�лش��ƺ��ķ��κ�ս���ĺ���ʹ����ȫ�����ˡ�����ս��ʻ��ͨ�����ǵ��ݼ�����ʱ����������̧��ͷ�������Ÿ첲��������˹��ķ���������������������������������ξ��������������ˮ���Ƿ���һ������������㽬ս���������������������ڷ����̹ս�����ѹ�籩������ս���ڸ�����������ľƬ����Ƥ���̸����ƿ���ײ������ϵ��ľ���ϵĴ�ͷ���������ǵĴ�ֻ��Ⱥ���ܹ������м���������ˮ�����������Ѿ�ʻ��ͷ�������������ӵ�ˮ��ǰ�档ˮ������ս��ʻ��������Ŷ��������ˡ�
����ͬ������ȫ�ֿ��ġ����ʹ�ڵ���ʱ���봩�����¸�ǽ֮���һ��ͨ����ͨ������һֱͨ��������ǰ�档���ǡ���Ƭˮ�Ĺ㳡����ΧһȦȫ����ͷ��������������ڱδ�ֻ��ÿ������ǰ���������������ӣ���ͷ���а����ȵĽǡ����������γ���һȦ�������ϵ����Ȼ���ˮ�档�ھ��������С����6���Ż��ִ���ٵĹ�ۡ��
ˮ���峺�����Կ���ˮ�������˰�ɰ�������е������������������������������ʱ���ϳ���������ָ�ӹ���һЩ���㽰^����
��Щս��ֻʣ���˴�Լ���弸�ң���������ӵ����ĵ��ϣ���Щ�����ţ���Щֱ���ţ���β�߸��̣��������������Ͼ���Щ�ƽ��װ�κ����ص�����ͼ������Щ���ͷ������β���»����û�˳���r��ɷ�Ѿ����˸첲����ţȱ�����ǣ�����������Щս�������ᶼ�Ȱ�����룬������������ʴ��ܣ���ȫ��������ɣ��������Ȼɢ����������ս����Ϣ������һЩ�˲е��ϱ����Լ�����˧�طꡣ���Ǻ���ڶ���˵�����������⣡��Ҳ��������ˡ���
���˺���ִ����˭Ҳ�����˺���ͳ˧����ֻҪû��֤��˵��������������Ӧ����Ϊ��ʼ�ջ��š�������Ԫ��Ժ�Ϳ��Ա����ί��һ�����ˡ����ڹ�����������Ҳ�ǰ���ϰ����������
ִ�����߹�һ�����һ�˵����ڡ�ÿ��һ����������һЩ��Ϥ�Ķ������׃١��Ҿߣ��ȵȣ�ʹ���е��Ծ�����������ǰ����һ����¯������Լ��ڳ���ǰ����������Ӷ���
������µ���ҡ���ϣ�����ɲ��������ص���̫������������һ�У���������һ�У��������ļ�����չ�ԣ�������Ż���ա��������š��������ꡢ������ũ���������������ﱴ�������ɻ�ɽ�������˹���بD��������սһֱ��Ү�����ҵ����ӣ����Ƿ���������ʧȥ�������ﵺ�����ţ����·��ּ�������Щ�������֣������ɵ�ɽ���ϵ����˺���Ⱥ����������������������������ؽ�һ������̫�������ļƻ������Ļ��䣬ʹ���DZ��ܺ����������������Ӻ�����졣һ�ֽ��ǵ�����ʹ���������ܣ���Ȼ��������������е���Ҫ���ֵı��ӡ�
����������ͳ˧������߲㣬�ӹ����Լ��첲�ϵ�һֻ�𱴿���ȡ��һֻͷ��װ�ж��ڵ�Ĩ�������һ����Բ��С����ķ��š�
ǽ��Ƕ��һЩ��ɫ��СԲ��Ƭ��������������͵Ĺ��ߡ�����һ����ͬ����С��ԲƬ�м䣬����������ǻҴ�����Ĺǻ���һ���Ķ���ÿ�����ﶼ����һ���ɫ�ġ�����ȥ�������ص�Բʯ��ֻ��һЩ������͵��˹�����Щ����������ĸ�ʯ����������������������dz�����ա����棻���ǵ���ɫ��ζ�ź�ҹ�����ǵ��ܶȴ����������������������������صĴ���������������Ϣ�����ա���ɳ��������Щ�����Բʯ����һ���ɫ�����Ǵ��Ǻ�����ŷ��ﴵ���ġ�������������ָͷһ��һ������һ�飬Ȼ����һ���ۻ�ɫ����ɴ��ס����������ȥ����ֱ��ֻ��َ���ڵ��¡�
����������ں�ɫ��СԲƬ�ϣ���ľ��СIII�����С�ģ�������Ķ����ڰ�����ԲƬ�ﹴ������������������ü����˺�����ʮ��ƽ�ͣ�����̫��������δ���Ĵ��������ڵ������ؿռ��д�ž�����������������ͷ���������й�����ĸ������塢�����ͳƺ����Ա���õذ��ձ���������ڸ��ŵIJ���ľ������������������������ģ�ͬʱ����������һ��Σ�����˸���̡�����^��ҕ��������ӳ����ˡ�������վ��������̩Ȼ�������������������ǿ־嶼���ܱ�����ҡ�����е��ؿڷ��ƣ��������Ǹ�������̫��ȫ�ǵ�����¥������
��̫�������������γ�һ�����ݵij��������ߣ���Щ�A�ݶ���������������ݡ�һ�ԴԵ��ظ���������ҫ�ŵƻ�IJ����A�����۵ף������ij�ǽ����������������ľ۱���ľ��Ե��������������Щ�ۿڣ���Щ�㳡��ͥԺ���ڲ�����Щ�ֵ����ɵ�ͼ�Σ��ͼ�С��С���·�����·���ϵ����ǡ����������������ϰ�ũ������ô���ŴӰ����ص������Ļ���������������ע��ңԶ����ߣ�һ˫�ն��ĸ첲���������ķ�����ȥ��
ͨ�����ǵ��ݼ���վ�����ˡ�����㳡������������������ִ���ٳ������Ĵ���ƽ̨�϶������������ˡ���Щ���ϳ��������������¾�����������ȥ��Ϊ�����ô�������������Ķ�������С�
����������¥�¿���������һ�ɵ�������Ҫ������˹���ǡ��汴�����ǡ�ϣ�����ɡ��Ȱ��Լ�����ˡ����Ƕ���������ǩ����Լ���������������Ԫ���ǵ�̰�ߡ���Ӷ������ȥ��ȥ�����������ǵ�Ҫ��˹�ı��������µı����������Ῠ����Ԯ�ͷ���������˭Ҳ���Ҹ����������йص���Щ�¼���������������������ҹ����Ħ��������Ԫ�ϻ������ټ���
���Ǹ��ߣ���������������������������赲������ӲҪ������������Խ��Խ�����ǹ�������������˴��˽�����
ֻ��һ��������̫�����˽���������������������y����ס���£�������ͣ���ͷ���Ź��ſ������ɫ���ۡ����ߵ�ִ������ǰ�����˻���עҕ��һ���������������Ȼ����һ����һ���֣�ū���Ƕ����˳�ȥ���������������˸����ƣ�����С�����ߣ��Sץס���ĸ�َ���������˸�Ƨ���ķ����
�Ǻ����˵��ڵأ������Ľš����͵ؽ�����������������������������ˣ����f���գ���
���DZߣ�����^���ѵ����ۡ������ӿ�����ס������͵ķ�ɫ����ΡΡ����̬������������ȫ����ʧ�ˡ�ԭ������һ��׳������ͷ�ӣ�Ƥ���·𱻷�ɳ�ͺ�������Ⱦ�����غ�ɫ��һ�ذ����Դ������𣬾���ijЩ����Ĺ�ë�������������Ϸ���Ŀ��ָ�����ڵ��ϵ��Ƕ�αװ˵��
�����öԣ����ϰ��գ��ܶԣ���Ȼ���������չ�·�Ҫ��������